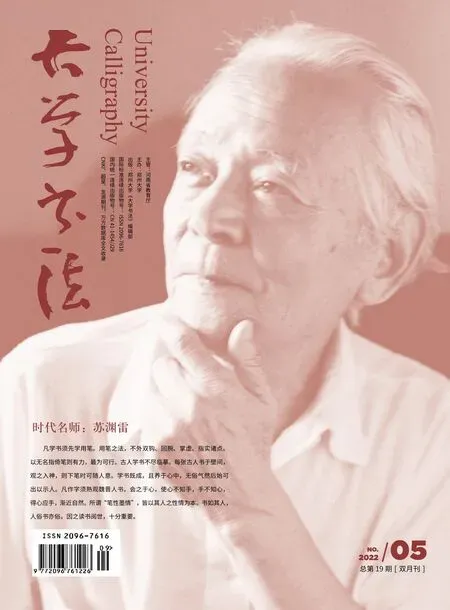清代湖南造像記楷書探析
⊙ 翟鑫 喬麗桃
造像記是宗教信眾在造作神像時,為表達美好祈愿而書寫在金石或絲麻織品、紙張等介質上的文字。早在我國魏晉南北朝時期,以金石為載體的造像記便已大量出現。清代的湖南尤其是廣大鄉村地區,佛道盛行,伴隨著造像活動的風靡,大量書寫在紙質上的造像記應運而生。中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通過田野考察,現已收集長江流域宋以后各類造像記4000余卷,涉及佛教、道教、民間宗教等多種宗教類別。本文擬以其中的清代湖南地區佛、道教造像記為研究對象和論述依據。這些造像記在年代上跨越了整個清朝時期,在地域上涵蓋了湘中、湘西、湘南等廣大地區。當前,學界對清代湖南造像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討其載體、內容,挖掘其背后所蘊含的宗教史、社會史、文化史等信息[1],尚未涉及其中的書法藝術。盡管這些造像記存在一些俗字、別字甚至錯字,但從書法創作的角度來看,它們真實集中地反映了流行于清代底層社會的書法風貌和書寫水平,為我們研究清代民間書法藝術提供了重要的一手實物資料。
一、清代湖南造像記的書寫格式與內容
清代湖南造像記多在神像開光時使用,之后便被隱藏于神像的背龕之中。造像記用毛筆書寫,載體多為紙張,書寫者多是活躍于底層社會的宗教人士,如處士、道士、師公等,或是至少受過基礎書法教育的民間寫手。
這些造像記有著較為固定的書寫格式,一般采用從右至左的豎寫形式。全文多以“今據”起首,中間為正文,表述造像者個人信息及愿望訴求等信息,最后為落款,包括書寫時間及書寫者姓名。除此之外,有些造像記在落款前后還會繪制一些符箓,應是用以役神扼鬼、驅邪降魔。造像記內容繁簡不一,多者上百字,少則三四十字,但基本會囊括造像的時間、地點、原因、造像者、造像對象、愿望訴求以及其他一些相關內容。如《蕭鎮南造像記》:
今據,大清國湖南寶慶府邵縣西路洪仁四都,地名江家村青山陡山二回,廟王城隍祠下土地各分居住,求吉保泰。下民信士蕭鎮南,室人劉氏,長男再生,次男松生,女蘇英,合家發心裝塑地主掌枟蕭法旺金容圣象。取畢,二月十五日上座。乞保:家下人口清泰,六畜平安,男增定百福,女納并千祥,凡在光中,全叨神庇佑。光緒八年開光安位,處士顏權堂。
從落款的書寫人姓名來看,這些造像記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因書寫者身份及教育背景的差異,它們呈現出不同的書體樣式和藝術風格,總體來看,主要有楷書、行書和草書。其中,楷書數量最多,占到總數的80%以上,其次為行書,草書僅有極少文字。本文試就其中的楷書進行分析。
二、清代湖南造像記楷書形態
清代湖南造像記楷書風格多樣、形態繁復,有的規整端莊,有的清麗雋秀,有的本真樸拙,有的隨意率性,展現出豐富的藝術特征和審美價值。
(一)規整端莊的楷書
這類造像記的書寫遵循一定的法度,筆畫清晰,結體端正,布局規整勻稱,但因書寫者不同,呈現出不同的氣質和風貌。
《孫士彬造像記》共計529字,書于清光緒二十五(1899)年四月。字體為清代流行的“館閣體”。用墨濃重厚實,運筆一絲不茍,點畫飽滿;結體平穩端正,間架勻稱;整體看起來烏黑方正,勻厚豐腴,有一種程式化的傾向。在章法上,該造像記采用了“縱有行,橫無列”的布局風格,給原本拘謹刻板的文字增添了一絲生氣。《羅朝秀造像記》全文共計228字,書于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三月。文字筆畫規矩圓潤,字體端莊方正、寬綽肥厚,字距與行距皆布局疏朗,整體給人一種儒雅、虛和的氣象。書者運筆流暢自然,點畫之間筆斷意連,如“二”“三”“六”等字的長橫多露鋒順勢起筆,收筆頓按,形成一條左低右高的弧線,使整個字端穩又顯靈動。

清 楷書 蔣長基造像記 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藏

清 楷書 楊錫運造像記 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藏
(二)清麗雋秀的楷書
這類造像記一般用勁瘦小楷書寫,其文字不似前述楷書那么規整端嚴,而是自然流暢、富有靈氣,整體看起來清秀雋美,給人一種清新脫俗的美感。
《蔣長基造像記》全文共240字,據“湖南衡州府”這一行政稱呼可知,其書寫年代至少應在清康熙以后。字體端莊清秀、細骨豐肌。筆畫多露鋒起筆,短橫干凈利落,長橫多形成一個向上的圓弧,如“王”“無”“安”字,整個字顯得生動活潑;豎畫多寫成懸針豎,如“不”“干”等字,運筆灑脫而不失法度。寬綽的章法布局,使整篇造像記看起來俊逸自然。雖為民間所書,也不失藝術美感。《楊錫運造像記》全文共13行,126字,其中第10行為符箓。前9行字體纖瘦秀氣,字形方中偏長,結體緊密連貫。輕而快的運筆使線條看起來纖細而富有生氣,尤其豎畫,多順勢露鋒收筆,懸針而立,如“新”“沖”“什”等字。
(三)本真樸拙的楷書
這類楷書數量最多,與名家書法相比,其無論在筆法、結體還是章法布局上,都有著很高的自由度,缺乏統一的規范和基調。
《譚肖氏造像記》全文共計159字,書于清光緒十四年(1888)五月。通篇文字雖缺乏書法謹嚴的法度,但總體來看,筆畫大氣流暢,字勢方廣開張。“凡”“光”“氏”“民”等字的最后一筆,在收筆時大角度上挑,給人一種率意自然的氣韻;“各”“爰”“辰”等字捺畫粗重,筆力雄健,“大”“人”等字撇捺開張,呈現出書者率真無拘、爽朗曠達的氣魄與風格。《彭澤翠造像記》線條簡潔明快,橫畫頓按起筆,形成一個“蠶頭”,且長橫多呈左低右高態勢,筆意活潑而有生氣;撇捺開張,筆致灑脫流暢,偶有連筆映帶現象,如第4行“一月”二字,“一”字末尾順帶而下,自然通暢如行云流水。《卿肖氏造像記》共計136字。全篇筆墨濃重,線條粗黑,但粗細不均,不夠圓潤。全文通體露鋒起筆,筆意稍顯生澀,結體扭捏歪斜,偏旁部首的組合缺乏統一的法度,如“官”字寶蓋過于寬大,“居”字下半部分則明顯拘謹。樸拙的筆法,粗糙的字體,盡顯淳樸率真,感覺不到一絲矯揉造作。

清 楷書 譚肖氏造像記 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藏

清 楷書 彭澤翠造像記 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藏
(四)隨意粗率的楷書
隨意粗率的楷書不拘泥于法度,這類造像記從運筆到字形結構都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字跡不工甚至潦草,個性十足。有的字出現了連筆和減省,有行楷意蘊。
《陳能和造像記》書于清嘉慶十年(1805)三月,全文共38行217字,第37行下部為一符箓。全文用筆粗細不均,字跡潦草,橫豎撇捺行筆隨意,信手寫來。“阝”“辶”“廣”等偏旁部首簡化連帶,“士”“吉”“大”等字橫畫修長奔放,“仝”字撇畫開張,捺筆彎曲。在結體上,各字不拘定法,字勢欹側,富有動感。但因連帶減筆所引起的大小輕重等結體變化也使得個別字看起來缺乏疏密之致與協調之美,如“下”字頭重腳輕,“祠”字左弱右強。《王順發造像記》書于清光緒三十年八月,因紙張脫層導致文字殘缺,全文現存38字。全篇筆墨濃重,書者運筆疾馳,揮灑率意,筆畫工草相間,線條粗細長短的對比起伏比較強烈。如“順”“發”“緒”等字連筆明顯,縱意瀟灑中隱現著樸拙的呼應,而“初”字則結體歪斜,姿態稍顯不穩。
三、清代湖南造像記楷書成因
清廷入主中原以后,為籠絡漢民,鞏固統治地位,在文化上延續明制,繼續推崇程朱理學。作為學校文化教育的一個重要方面,清代書法教育也深受程朱理學思想的影響。朱熹將書法風格與人的品格修養相聯系,認為書法要體現書寫者雍容中正的涵養和胸襟。他主張:“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潦草。”[2]朱熹這一端正謹嚴的理學書法思想深刻左右了整個清代書法教育的審美定位。
以清中期國子監為例,其所開設的書體課程中,明確強調書寫要規整。清道光四年(1824)《欽定國子監則例》卷三十四規定:“凡內外班肄業生,學習書體,每日數百字,皆令臨摹晉唐名帖,助教等隨時指示,毋得潦草、錯落及倩人代書。”[3]國子監為清代最高教育機構,其書法教育模式作為典范,必然為其他官學及民間私學的書法教育所效法,這一點在民間書院書法教育所遵循的《程董二先生學則》中就有所體現。該學則第十二條規定:“寫字必楷敬,勿草,勿欹傾。”[4]清末,書院改制學堂,朝廷依然將端莊、法度嚴謹的楷書作為習字標準。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欽定小學堂章程》規定,學生第一年習“今體楷書”,第三年“兼習行書”,高等小學堂第二年習“楷書、行書,兼習小篆”[5]; 光緒二十九年(1903)《奏定中學堂章程》規定,一、二、三、四年級“相間習楷書行書”“兼習小篆”[6]。
此外,被學校教育奉為圭臬的科舉制度也對清代書法教育的基本理念和方法產生重要影響。清代繼續實行科舉取士,出于選拔人才的需要,與科舉有關的各級各類考試均對考生的文字書寫提出嚴格要求,考卷上書法的優劣直接決定著能否高中以及高中的名次。正如晚清進士傅增湘對當時殿試錄取的描述:“縱有天人三策之文,而不嫻《字學舉隅》之法,則決難入選。”[7]于是“父詔師勉,以楷法為元燈。偶有研求實對者,咸相嗤笑。相師成風,牢不可破”[8]。
由前述可以看出,由于理學正統觀念的影響以及科舉制度的引導,清代的書法教育崇尚“端莊”,在具體的書法教育實踐中,始終以楷書作為學生的習字藍本,同時輔以行書和小篆,至于隸書、草書等其他書體,則不在書法課程的常規訓練內容之列。這種書法教育模式對當時人們的審美觀念、書寫風尚以及書法風貌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莊重、端穩的審美觀念逐漸深入人心,楷書成為社會通行的標準字體,士人書法創作出現正體化傾向。在功利性和實用性的價值導向下,人們在日常實用書寫中對書體的選擇也表現出兩大傾向:一是蘊含官方正統思想的楷書大行其道;二是由楷書發展而來,在筆畫上連帶減省的行書因書寫快捷而又不影響識別的優點,也被人們,尤其是底層民眾所普遍使用。
四、清代湖南造像記楷書價值
清代湖南造像記楷書是清代書法教育以及科舉制度影響下的產物,作為來自底層百姓的民間墨跡,它具有重要的藝術價值和學術價值。
首先,它豐富了中國書法的多樣面貌,展現了生活于社會底層的人們在“無意識”狀態下所創作出的最原生的書法風貌。書法藝術的創造,既需要藝術技巧的護持,同時也少不了個性的自由發揮。清代湖南造像記楷書展現了底層百姓的本真個性,是自由率真與法度技巧相互融合的結果,顯現出旺盛的生命力。雖然這些作品有稚拙粗率之弊,但從藝術史的角度審視,它在主流書壇之外開辟了新的境界,給書法傳統注入了一股難得的新韻。
其次,透過清代湖南造像記楷書,我們可以一窺俗書與官書的互動與融攝。一種新字體,其發生、形成和成熟,都在俗書之中完成,并逐漸被官方所接納進而成為官書。[9]楷書發展到清代,已形成標準的“館閣體”,其作為被規范、美化后的官書,已顯現出刻板、拘束的弊端,最初的靈動與活力也已黯然失色。清代湖南造像記所展現的民間楷書,可被視為楷書在清代民間的存續樣本,它們大多還依然保留著楷書的率意自然,這對于我們了解清代“館閣體”的初始來源形態以及楷書在民間的發展演變態勢都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清代湖南造像記的搜集、整理與研究工作仍在進行。造像記文字作為清代庶民墨跡或“非自覺書法”的一個縮影,值得我們進一步挖掘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