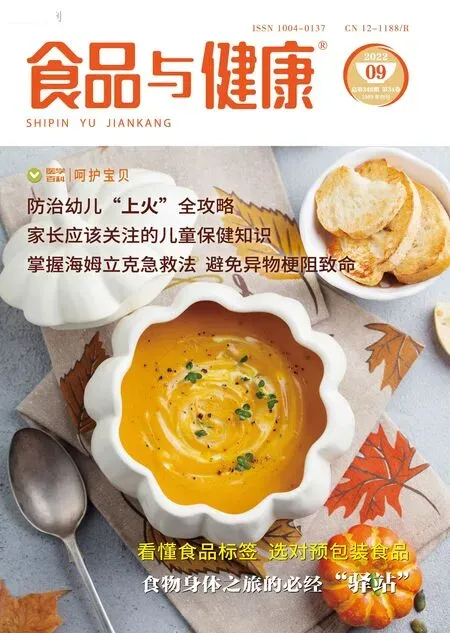每一株植物都有故事
■王 曉
我對夏天的感情有些復雜。小時候很愛夏天,下河游泳、釣草蝦、摘瓜果都是樂事。宋代楊萬里《夏夜追涼》寫夏天:“夜熱依然午熱同,開門小立月明中。竹深樹密蟲鳴處,時有微涼不是風。”詩人千年前的感受,與我童年的夏天何其相似。工作后,也許是因為俗事纏身,一到夏天我便感覺燥熱難忍。
重新喜歡夏天,源自打理樓下的小花園。一塊廢棄的空地,經過我一番收拾,花草們一一安家。沒有什么比一顆種子發芽,一朵花盛開,一個果子成熟更讓我欣喜的了,我重新體會到了幼時對夏天的那種親切感。于是,書可不讀,文可不寫,酒可不喝,友可不約,我只愿與這方小園相處,以養心安神。
園子里每一株植物都有故事,我與它們同呼吸、共成長。看似雜亂的園子,其實是經過我精心規劃的,一片菊花,一片端午花(學名蜀葵),一片繡球,一片向日葵,還有間隔種的藍目菊、朝天椒等等,都是明艷的,像我現在的穿衣風格。看紀錄片,河南人用荊芥佐面,吃得那個香!我看得好饞,于是網購了種子栽種在園子里。我特別喜歡荊芥那獨特的清香,像位別致的女子。
萱草是中國的母親花。我小時候便種它,將其種在自家后門口。夏天,媽媽會摘下幾朵橙黃色的萱草花、兩片薄荷葉子,放入雞蛋湯,成就一碗獨屬夏天的味道。人到中年,我與母親幾乎每天通一次電話。母女相隔二三百里,不是說見就能見的。種下萱草花,像天天能看見我的母親。
小園子里疏松的沙土更適合種植根莖類植物。去年我隨意插了幾棵山芋藤,并沒有精心侍弄,秋天卻挖出一兜子紅心山芋。這可把家里參與過勞動的兩個上幼兒園的小朋友樂壞了。今年,我把發芽的土豆隨手淺淺地插到土里,也沒怎么管。前日澆水,發現園里的土豆已經破土而出。它們白生生、圓溜溜,可愛極了。過幾天,我家小娃娃們便可以挖土豆了。小花園就是他們最方便的自然課堂。
一天中,我有太多的時間在這里度過。松土、開溝、提水、灌溉,收拾花園的勞動量可真不小。小園子如果不是靠路邊太近,中午我都想搬張床在這兒午睡。有樹蔭更好,無樹蔭就日光浴,不舟車勞頓,不翻山越嶺,不拋家,不遠行,這里就是我的詩與遠方。我可以在這里用自己的經歷、感受書寫小園子里植物們獨一無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