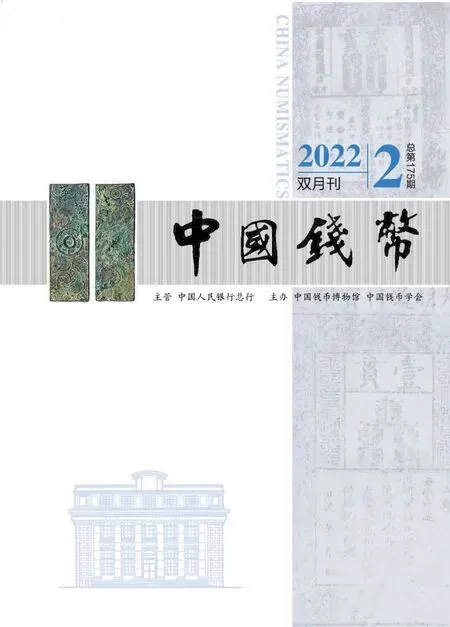豫泉官銀錢局與清末民初河南幣制變革*
楊 濤 (安陽師范學(xué)院)
清末民初河南地方政府與軍閥為調(diào)劑金融,彌補(bǔ)財(cái)政,解決通貨不足,創(chuàng)辦豫泉官銀錢局(以下簡稱豫泉局)。豫泉局與諸多省區(qū)官銀錢號(hào)一樣,具有早期地方銀行性質(zhì),兼具地方財(cái)政機(jī)關(guān)與省庫職能。豫泉局對(duì)近代河南財(cái)政、金融,尤其幣制方面影響極大。
但是豫泉局的研究成果十分薄弱,主要為史料輯錄性質(zhì)的著作。如周葆鑒著《中華銀行史》、郭榮生著《中國省地方銀行概況》、姜宏業(yè)主編《中國地方銀行史》、邵文杰主纂《河南省志》第46 卷“金融志”等,偏重豫泉局與河南省銀行沿革,清廷與北京政府監(jiān)管措施方面史料,內(nèi)容十分簡略。張家驥著《中華幣制史》、黃亨俊著《清代官銀錢號(hào)發(fā)行史》、戴建兵著《中國紙幣》,僅收錄豫泉局發(fā)行、流通紙幣情況。至于豫泉局對(duì)近代河南幣制影響,僅見吳籌中、黃亨俊著《河南豫泉官銀錢局及其發(fā)行的鈔票》、孫豪著《近代豫泉官銀錢局探微》、王新峰著《清末至1923 年的河南豫泉官銀錢局》等3 篇文章。本文側(cè)重豫泉局對(duì)貨幣流通、兌現(xiàn)的影響,分析地方政府對(duì)豫泉局的影響,體現(xiàn)近代幣改的復(fù)雜過程與必然趨勢(shì)。
豫泉局設(shè)立原因,與河南更早設(shè)立的豫立官錢局類似。依光緒二十四年(1896)五月河?xùn)|河道總督任道镕、河南巡撫劉樹堂奏稱,往年豫省每兩銀合制錢一千五、六百文,本年僅易一千二百余文。河工經(jīng)費(fèi)事事以銀換錢結(jié)算,“幾暗耗錢二十余萬串矣”。價(jià)昂導(dǎo)致“各料必不能多”,影響黃河伏汛歲修大計(jì)。應(yīng)急之策,二人提出:一者,籌款兩萬兩,于本年六月二日在開封設(shè)立豫泉局,推行鈔票,搭用制錢,以保障制錢“轉(zhuǎn)輸不竭”。一者,另籌銀兩萬兩,在湖北附鑄銀元,由豫泉局發(fā)給各典當(dāng)行鋪推廣使用。“亦可輔制錢之不足。”這兩個(gè)彌補(bǔ)制錢不足的措施,第一個(gè)設(shè)官錢局,是咸同成法;第二個(gè)附鑄銀元,是張之洞、李鴻章甲午戰(zhàn)爭前后在湖北、廣東推行的新法。但囿于民間不習(xí)使用,加之無力籌集鑄本以及運(yùn)輸不便,河南始終無自鑄銀元。
一 對(duì)制錢、銀兩流通、兌換影響
(一)對(duì)制錢流通、兌換影響
豫泉局只設(shè)官錢局時(shí)期(1896-1904),主要業(yè)務(wù)是發(fā)行鈔票來彌補(bǔ)制錢不足。因民間日常生產(chǎn)、生活,“仍以現(xiàn)錢為重”,1898 年河南重新開鑄制錢,解交豫泉局分發(fā)搭用。但只開鑄十爐,便因銅料不足,被迫停工。河南當(dāng)局逐漸意識(shí)到,恢復(fù)制錢不合時(shí)宜。1902 年,清廷詔令籌議通商惠工,整理幣制、財(cái)政之法。河南地方官員提出,不應(yīng)恢復(fù)錢兩并用制度,應(yīng)確立本位制,廢兩改元,發(fā)行統(tǒng)一國幣即標(biāo)準(zhǔn)銀元。這一主張被撫院采納。之后河南地方政府幣改思路、實(shí)踐,調(diào)整為鑄造銅元,與豫泉局發(fā)行錢票互為兌換,以便流通。
清末河南境內(nèi)已顯現(xiàn)出銅元代替制錢趨勢(shì),民初更為彰顯。“市面上幾不見制錢之活動(dòng),惟僻遠(yuǎn)城邑或存其勢(shì)力。”1917 年豫泉局計(jì)劃大規(guī)模收買制錢,镕化為銅元材料,雖因議會(huì)反對(duì)而不果,但影響制錢逐漸淘汰出流通市場。開封等地市面上制錢日益見少,原因與各地類似:社會(huì)不穩(wěn)定使得商民將制錢窖藏;奸商與日本人勾結(jié),組織公司收買,镕化、販運(yùn),以圖重利。
以滑縣為例,隨著制錢制度崩壞,豫泉局設(shè)立后,民間不再崇用青錢、當(dāng)十大錢等。至民初,“銀元、銅元盛行于世,兼有紙幣(豫泉局紙幣)通行,世人樂其取攜之便。向之紋銀、銅錢漸行消滅。”此可說明,1904 年后,制錢在河南貨幣流通市場的地位被銀元、銅元、紙幣攘奪。但不可否認(rèn),至北洋政府滅亡,在偏遠(yuǎn)地區(qū),制錢仍和普通民眾日常生產(chǎn)、生活關(guān)聯(lián),“長時(shí)段”影響這些地區(qū)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緩慢變革。
(二)對(duì)銀兩流通、兌換影響
豫泉局對(duì)河南銀兩影響,一是其準(zhǔn)備金、護(hù)本銀兩,與發(fā)行銀兩票數(shù)量之比;一是其放款銀兩額度;一是其代理省金庫對(duì)使用銀兩的規(guī)定。
豫泉局設(shè)立時(shí)領(lǐng)成本銀九萬兩,護(hù)本銀一萬兩。1904 年設(shè)官銀號(hào)后,成本銀增至十一萬兩,護(hù)本銀未變,主要業(yè)務(wù)轉(zhuǎn)為兌發(fā)制錢、銀兩票及放款。其放款業(yè)務(wù),因分支多,擴(kuò)張過快,數(shù)量達(dá)七十萬八千余兩(可收回者僅二十余萬兩),出現(xiàn)嚴(yán)重虧損。1912 年5月清理時(shí),負(fù)債八十萬四千兩,而該局存款折合不過七萬二千余兩。民國以后分新舊案整理,存放款統(tǒng)以銀元而不再以銀兩計(jì)算。
豫泉局因放款造成銀根吃緊,于是發(fā)行銀兩票加以應(yīng)對(duì)。1905 年豫泉局發(fā)行60 萬兩,是其準(zhǔn)備金5 倍多;1911 年達(dá)到170 多萬兩,是準(zhǔn)備金15 倍多;即便經(jīng)1912 至1914 年間整頓,1914 年仍有1458420 兩。這種不考慮準(zhǔn)備情況的濫發(fā),不僅影響銀兩票的信用,對(duì)銀兩流通、兌換也極為不利,加劇了河南貨幣市場銀兩缺乏問題。
民初《國幣條例》頒行,廢兩改元成為幣制改革的方向。地方當(dāng)局頒布《各縣局解繳庫款手續(xù)辦法規(guī)則》,規(guī)定豫泉局代理省金庫,各縣局解款來省,徑赴該局隨到隨收。這些因素決定豫泉局必然一改清末舊制,完糧納稅禁收銀兩、錢票,統(tǒng)以銀元結(jié)算。兼之汴秤、湘秤、庫秤、行秤等稱量標(biāo)準(zhǔn)的不便,“五、六年來省垣用銀者已屬鮮見,惟邊遠(yuǎn)各縣行用尚多。”
1916 年第一次停兌風(fēng)波后,河南廣大地區(qū)流通的金屬貨幣以銀元、銅元、制錢為“三大宗”,銀兩淡出歷史舞臺(tái)。至20 世紀(jì)20 年代初,周口、漯河等地,受“五四運(yùn)動(dòng)”影響,國幣(即袁頭幣)流行最多。其次為日本龍洋,清末湖北、天津造銀元。當(dāng)十、當(dāng)二十、當(dāng)五十銅元通用,制錢在漯河局部流通,銀兩已在這些地方退出流通市場。
二 對(duì)銅元鑄造、流通、兌換影響
(一)清末至第一次停兌風(fēng)波前情況
河南開鑄銅元始于1904 年。背景為京漢鐵路通車在即,湖北制錢乘勢(shì)大量輸入。因河南制錢缺乏,“往而不復(fù),鄂省錢價(jià)日貴。”故河南巡撫陳夔龍?jiān)诤V總督端方建議下,仿照湖北、山東開鑄當(dāng)十銅元,“以救錢荒而拓利源”。并規(guī)定銅元完糧納稅、市場交易一律通用,與豫泉局官錢票并行不悖。如此,“票本益充,制錢無日絀之虞,市價(jià)有常平之望,于國計(jì)民生均有裨益。”這也是豫泉局轉(zhuǎn)變經(jīng)營思路,將錢票與制錢、銅元同時(shí)掛鉤。
依考察銅幣大臣陳璧1907 年所奏,河南銅元局共設(shè)49 爐,屬“機(jī)廠無多”者。至1906 年底,共鑄當(dāng)十銅元235145880 枚,行銷207031493 枚(撥陸軍學(xué)堂一千萬枚),實(shí)存13514387 枚。市價(jià)120 枚合銀一兩,“較各省錢價(jià)為高,民間極為信用,因出數(shù)無多,各屬尚難遍及。”后清廷裁撤十二省銅元鑄造機(jī)器845 具,河南僅裁6 具,數(shù)量最少,銅元局至民初依然保留。這一方面得益于河南銅元數(shù)量未至泛濫,另一方面得益于豫泉局發(fā)行錢票審慎,支持銅元信用。豫泉局發(fā)行錢票以1905 年為標(biāo)準(zhǔn)值(100),約計(jì)11 萬串。因清廷出臺(tái)《通用銀錢票章程》《厘定兌換紙幣則例》,限制發(fā)行,至1911 年豫泉局錢票發(fā)行量為30 余萬串,比值為270.27。民初推行幣制改革,整理各省濫紙幣,豫泉局至1914 年發(fā)行量降為231300 串,比值為210.27。為穩(wěn)定境內(nèi)銅元流通,豫泉局提調(diào)王宰善1909 年曾向河南巡撫張人駿提出:“我國但知行用銅元,而不詳究其性質(zhì)與功用,無一定之價(jià)格,無一定之限制,宜乎?”指出銅元應(yīng)為劃一銀元輔幣,應(yīng)確定二者比價(jià),限制其鑄量。
民初河南流通銅元主要為改版的當(dāng)十銅元及1908 年鑄當(dāng)一銅元,1918 年以前大額銅元尚未出現(xiàn),各類銅元信用良好。1916 年,因洪憲帝制發(fā)動(dòng),銅元需用迫切,經(jīng)河南商會(huì)提議,省政府與豫泉局下令開放門戶,省外銅元一律通用。于是在第一次停兌風(fēng)波發(fā)生前,銅元“致呈供不應(yīng)需之象。”為穩(wěn)定本省自鑄銅元價(jià)格及流通,豫泉局與地方政府除開始限制外省銅元輸入,又強(qiáng)制規(guī)定本省銅元十足行使,外省僅作七、八折。
這一時(shí)期,豫泉局能保持河南境內(nèi)銅元較為穩(wěn)定的流通與兌換,得益于清廷與袁世凱政府的監(jiān)管措施,特別是袁世凱統(tǒng)治時(shí)期,為推行《國幣條例》,對(duì)銅元鑄造、流通也予以嚴(yán)格的監(jiān)管措施。
(二)第一次停兌風(fēng)波后的情況
第一次停兌風(fēng)波后,情況大變。其一,因停兌波及豫泉局,為應(yīng)對(duì),1918 年河南一改袁世凱統(tǒng)治時(shí)期的中央禁令,復(fù)設(shè)爐開鑄。1919 年后又鼓鑄當(dāng)二十文、當(dāng)五十文銅元。主政河南的軍閥趙倜還與豫泉局總辦景仲生、中交二行行長、財(cái)政廳長商議,決定中央未允許河南開鑄前,委托天津造幣廠代鑄當(dāng)二十銅元,并從湖北購進(jìn)銅元。1920 年直皖戰(zhàn)爭爆發(fā),雖然當(dāng)二十銅元完糧納稅仍可通用,但市面當(dāng)十銅元明顯減少。社會(huì)上關(guān)于官方收買當(dāng)十銅元,改鑄大額銅元之說盛行,嚴(yán)重影響銅元信用。
其二,地方政府與豫泉局出臺(tái)地方保護(hù)性質(zhì)政策。一是出臺(tái)《河南省禁止銅元入境章程》,規(guī)定軍政機(jī)關(guān)、商人除持特別護(hù)照外,嚴(yán)禁“私運(yùn)”銅元出境,或來河南購買銅斤。對(duì)走私五千枚以上,不及兩萬枚者將超過數(shù)扣留。超過兩萬枚且系牟利者,原人扣留,逾額充公。二是河南當(dāng)局為保護(hù)鑄造銅元利益,保障豫泉局兌現(xiàn),屢次與北洋政府財(cái)政部交涉,反對(duì)復(fù)設(shè)平市官錢局河南分局,發(fā)行銅元票。1918 年8 月河南省長趙倜,以“豫泉舊幣現(xiàn)尚補(bǔ)救未遑”為由,反對(duì)“再增一發(fā)票機(jī)關(guān)”,甚至講洪憲帝制時(shí)期,平市官錢局銅元票不能兌現(xiàn),信用毫無,法理上已喪失部屬金融機(jī)關(guān)資格。盡管北京政府不顧地方反對(duì),復(fù)設(shè)該局,但豫泉局呈請(qǐng)地方政府,平市官錢局收買、流通銅元票應(yīng)暫緩,待其整理完畢后,“再為推行”。三是豫泉局還大量收集制錢,限制外流,備鑄大額銅元,并嚴(yán)禁兌換銅元。
停兌危機(jī)后,河南地方當(dāng)局以盡快恢復(fù)豫泉局兌現(xiàn)、保障本省銅元價(jià)格穩(wěn)定為主旨,政策上有極大轉(zhuǎn)變。一是飲鴆止渴,收集制錢與小額銅元,鑄發(fā)大額銅元,加劇金融紊亂和豫泉局經(jīng)營危機(jī)。二是用政府禁令,政策干預(yù)手段,影響境內(nèi)銅元流通、發(fā)行和豫泉局兌現(xiàn)。此舉非但沒有給豫泉局營業(yè)帶來好的影響,還進(jìn)一步激化了與中央的矛盾。趙倜治豫時(shí),改鑄當(dāng)二十銅元,添鑄當(dāng)五十銅元,趙倜獲利十分之二、三。趙倜去后,銅元局一度每日鑄造十五萬枚,“所有每日鼓鑄之利益,仍歸督軍”,以供軍政所需。豫泉局此時(shí)使命就是在銅元局鑄大額銅元后,亦步亦趨,發(fā)行各種銅元票,附和地方當(dāng)政者利益訴求。其對(duì)幣制統(tǒng)一、現(xiàn)代化的影響也談不上積極。
三 對(duì)銀元流通、兌現(xiàn)影響
光緒末年,開封、鄭州等地已行用銀元,民初豫泉局流通、兌現(xiàn)的外來銀元共以下幾種:湖北銀元、北洋銀元、大清銀幣、袁頭幣及輔幣。1914 年頒布的《國幣條例》,確立七錢二分重、一元幣值銀元為國幣,并確立了銀本位制、十進(jìn)位輔幣制度,這是中國幣制現(xiàn)代化重要一步。因此銀元在河南流通、兌現(xiàn)情況,以及豫泉局在其中所起作用,可作為考量河南幣制現(xiàn)代化水平的重要標(biāo)準(zhǔn)。
如何穩(wěn)定銀元充足流通、完全兌現(xiàn)是影響豫泉局營業(yè)的關(guān)鍵,為此河南當(dāng)局出臺(tái)相關(guān)政策。第一,在各省崇用銀元大背景下,為鞏固銀元在貨幣市場地位,1918 年河南省議會(huì)議決:“糧漕皆以銀元計(jì)算繳納”。這一決議,導(dǎo)致此后“銀元之行用始見普及”。如湖北銀元由過去每元換制錢九百文,至1919 年已漲至一千五余文。第二,省政府出臺(tái)《河南省限制銀元出境章程》,明確規(guī)定凡入豫省商民,攜帶銀元每人以五百元為限。運(yùn)輸過境,應(yīng)持省長、督軍或財(cái)政廳護(hù)照,載明用途、數(shù)目及起止點(diǎn)。超過五百元,不及兩千元者將超過數(shù)扣留。超過兩千元且系牟利,原人扣留,逾額充公。
但以上均非治本之策。工商業(yè)疲敝造成金融僵滯,現(xiàn)金缺乏;民風(fēng)、習(xí)俗保守導(dǎo)致銀元不能廣為流通;財(cái)政枯竭使當(dāng)局濫發(fā)豫泉局銀元票吸收現(xiàn)金,用于軍政開支,導(dǎo)致豫泉局銀根不穩(wěn)。加之停兌風(fēng)波發(fā)生,銀元流通、兌現(xiàn)在河南極為困難。第一次停兌風(fēng)波后,豫省現(xiàn)金不足變?yōu)橹饕狈ΜF(xiàn)洋。當(dāng)時(shí),“開封等地一般商民來省買貨者,均購現(xiàn)洋出省。而省城各商號(hào)交易亦皆以現(xiàn)洋為定價(jià),所以現(xiàn)洋即日見增長。”但豫泉局卻在資本不固情形下,“收買現(xiàn)洋湊集政費(fèi)”,使得銀價(jià)高昂,進(jìn)一步加劇現(xiàn)洋空虛,紙幣低折。輿論批評(píng)河南當(dāng)局與豫泉局此舉,為“近來之卑劣理財(cái)政策”。更甚者當(dāng)局為穩(wěn)定豫泉局銀元票,竟強(qiáng)制分發(fā)各縣流通。輿論質(zhì)問此舉:“果為調(diào)劑金融之政策乎?抑為吸收現(xiàn)款之手段乎?吾民雖愚,當(dāng)亦不待思索而知其用意之所在矣。”
四 豫泉局紙幣流通、兌現(xiàn)情況及對(duì)幣制統(tǒng)一、現(xiàn)代化影響
豫泉局至1923 年停業(yè),發(fā)行紙幣計(jì)有制錢票、銅元票、銀兩票、銀元票、銀角票。這些紙幣多未經(jīng)中央許可,全視河南省需要而異。“準(zhǔn)備之有無,及成效之若干,亦復(fù)各自為制。故票之兌現(xiàn)與否,亦不一致,信用之良否,市價(jià)之高下亦復(fù)互異。”依靠豫泉局發(fā)行紙幣來流通金融,這是近代河南金融史、經(jīng)濟(jì)史一個(gè)重要特點(diǎn),這一特點(diǎn)暴露出近代河南幣制的落后。
豫泉局發(fā)行紙幣情況,分時(shí)段說明如下:
第一時(shí)期,1896-1915 年洪憲帝制揭幕前。依據(jù)1915 年11 月北京政府財(cái)政部報(bào)告,豫泉局發(fā)行銀兩票為1457620 兩,市面流通470760 兩;發(fā)行銀元票110600 元,市面流通66744 元;發(fā)行制錢票231381 串,市面流通171194 串。而豫泉局的實(shí)有資本為12 萬兩。這一時(shí)期又可分三階段。
第一階段1896-1904 年,豫泉局只發(fā)行錢票,流通額93 萬串以上,在市場上,排擠錢莊、票號(hào),獨(dú)占鰲頭。
第二階段即1904-1912 年,豫泉局增設(shè)官銀號(hào),擴(kuò)張分支機(jī)構(gòu),紙幣發(fā)行業(yè)務(wù)急劇擴(kuò)張。除發(fā)行錢票外,“并出銀洋鈔票。銀票一兩起,百兩止;洋票一元起,百元止。”銀兩、銀元票逐日增多,造成準(zhǔn)備金與發(fā)行額、流通額與發(fā)行額、存放款巨差,豫泉局出現(xiàn)虧損。銀兩票比重,發(fā)行速度也大于、快于銀元票。這說明地方當(dāng)局與豫泉局幣改觀念的滯后。這一時(shí)期清廷推廣劃一紙幣。同時(shí)為籌劃幣改,成立國家銀行,度支部尚書載澤明確要求:“各省銀行及官錢局亟宜留心整頓,以期一律奉行。”為防止官銀錢號(hào)濫發(fā)紙幣而倒閉,引發(fā)金融恐慌,要求各省調(diào)查資本,規(guī)定發(fā)行不得逾資本半數(shù)。清廷整頓措施具有一定遏制作用。與粵、湘、鄂、東三省等省區(qū)官銀錢號(hào)紙幣泛濫成災(zāi)相比,豫泉局至民國建立仍能保持信用,基本兌現(xiàn),價(jià)格未低至八折以下乃至四五折,已屬難能可貴。
第三階段,1912 年至1915 年底洪憲帝制前。袁世凱政府對(duì)整理濫發(fā)紙幣問題高度重視,明確表示:“若使各省紙幣仍舊任意發(fā)行,則金融愈滯,產(chǎn)業(yè)愈凋,國家歲入又將安仰?”要求各省民政長、財(cái)政司嚴(yán)飭所屬官銀錢行號(hào)恪守章程,不得增發(fā)。此間北洋政府出臺(tái)一系列政策,如發(fā)行特權(quán)收歸中交二行;頒布《整理各省官發(fā)紙幣法案》《取締紙幣條例》、收回紙幣辦法五條;頒布《各省官銀錢行號(hào)監(jiān)理官章程》等。經(jīng)整理,廣東、湖北、湖南、直隸、山東、山西、福建、安徽、陜西、浙江紙幣濫發(fā)無度情況明顯改善。豫泉局紙幣發(fā)行、流通也趨于正軌,信用為較好時(shí)期。豫泉局整頓、清理實(shí)效可以下表對(duì)比說明。

說明:紙幣增減以1905年為標(biāo)準(zhǔn)值(100),其比值計(jì)算均按實(shí)數(shù),如60多萬兩即按60萬兩核算,53000余元按53000元核算,余者類推。另1915年4月豫泉局還有“以收回四十萬兩之銀票,改為三十萬元銀元票之請(qǐng)”。
對(duì)比三個(gè)時(shí)期發(fā)行情況,最高峰為1911 年。經(jīng)1912-1914 年整頓,銀元票不變外,制錢與銀兩票均下跌。北洋政府有意將豫泉局紙幣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為以銀元票為主,配合國幣推行,反對(duì)與傳統(tǒng)幣制相關(guān)的銀兩、制錢票增發(fā)和流通。
第二時(shí)期,1915 年末至1922 年直奉戰(zhàn)爭爆發(fā),趙倜離豫前。這一時(shí)期,豫泉局成為趙倜行軍糧臺(tái)、軍政開支賬房,又經(jīng)歷兩次停兌風(fēng)波沖擊,經(jīng)歷直皖、直奉戰(zhàn)爭,營業(yè)大受影響,紙幣信用一落千丈。
1916 年后豫泉局的紙幣除制錢票、銀元票、銀兩票外,又有銅元票、銀角票。停兌風(fēng)波后,除制錢票、銅元票尚未“失去表面之價(jià)額者”外,其余“價(jià)額與表面所載不符”。一邊現(xiàn)金價(jià)值飛漲、物價(jià)騰貴,一邊銀兩、銀元票價(jià)格低折至九折、八折,官方征收丁銀禁收豫泉局紙幣。
這一時(shí)期又可分兩個(gè)階段。第一個(gè)階段1915 至1921 年第二次停兌風(fēng)波前。第一次停兌風(fēng)波發(fā)生后,河南當(dāng)局鑒于中交二行停兌,銀兩、銀元匱乏,由豫泉局發(fā)行十元、五元、一元三種銀元票共60 萬元救濟(jì)市面。規(guī)定價(jià)格與現(xiàn)洋一致,但不許兌現(xiàn)洋,只可兌銅元。一時(shí)頗為社會(huì)所歡迎,但未幾換算價(jià)格低落,與不兌現(xiàn)之中、交鈔票無甚軒輊,進(jìn)一步加劇市面恐慌。1918 年9 月后,豫泉局勉強(qiáng)兌現(xiàn)。豫泉局于1915 年開始發(fā)行二百枚、一百枚、五十枚、二十枚、十枚銅元票,但不久就受平市官錢局濫發(fā)銅元票沖擊。停兌風(fēng)波后,二局銅元票均停兌。“豫泉局之票僅抵九折,惟省垣及杞縣、通許等三、五縣可以行使。”其他各地市面幾乎不見銅元票。制錢票也好不到哪里,“與銅元票概停兌現(xiàn)”。至1920年2 月,豫泉局紙幣在洛陽由于“各商公議不收紙幣”,大跌至七五折。銀元與制錢票比價(jià),增高至一元合一千七百文以上。各地商民生產(chǎn)、生活大受影響。
即使如此,趙倜與河南當(dāng)局仍飲鴆止渴,繼續(xù)濫發(fā)。至1920 年底,豫泉局發(fā)行銀元票4380000 兩,為1914 年3 倍多,制錢票492940 串,為1914 年2.13 倍,銀角票5455000 元,為1914 年48.32 倍。此外尚有銅元票合1502400 串。1920 年彭既安等河南士紳致電總統(tǒng)徐世昌、總理靳云鵬,控訴趙倜操縱豫泉局紙幣行市,從中牟利,不準(zhǔn)豫泉局紙幣兌現(xiàn)。“計(jì)其私蓄,至數(shù)千萬,民脂民膏,盡入一人之私囊。”
第二個(gè)階段至1922 年直奉戰(zhàn)爭前。趙倜行將垮臺(tái),強(qiáng)迫流通豫泉局鈔票,苦苦支撐。因金融危機(jī)和戰(zhàn)爭影響,豫泉局兌現(xiàn)、流通紙幣更為困難。1921 年11 月第二次停兌風(fēng)波波及豫泉局,該月19 日河南軍民長官布告中交二行與豫泉局停兌兩個(gè)月。“自此風(fēng)潮發(fā)生后,中、交行及官錢局鈔票,在市面上遂大受影響。”11 月22 日后,豫泉局與中交二行鈔票有限制兌現(xiàn),豫泉局每日兌現(xiàn)僅五百元。每人不過五元,且抽簽取號(hào)兌現(xiàn)。此舉進(jìn)一步引發(fā)社會(huì)恐慌與不滿。“此次停兌,中、交兩行事前并無同意,全系官錢局一方面之主張,以致牽動(dòng)全局。因官錢局近日實(shí)不名一文,不得不停止兌現(xiàn)。”這是豫泉局在廣大民眾中大失信用的一個(gè)標(biāo)志性事件。
但趙倜與河南當(dāng)局仍強(qiáng)令每縣攤派使用豫泉局紙幣,方法為票面加蓋一紅戳,鄭縣印“鄭”字,許昌印“許”字,委派專員到各處換取現(xiàn)洋;此類鈔票只準(zhǔn)在該縣流通,逾境無效。這種辦法進(jìn)一步造成豫泉局紙幣信用下跌,流通、兌現(xiàn)更為不便。此外豫泉局流通當(dāng)五十、當(dāng)百等大額銅元票價(jià)值落至六七折,在市面上受到商民抵制,各行業(yè)被迫相率改用銅元交易。輿論評(píng)價(jià):“而豫泉局鈔票之信用,益行墮落矣!此次流通豫鈔辦法,仍歸前年故智,而較前略為活動(dòng),究亦不外于勒派、硬索之一途耳。”
第三個(gè)時(shí)期由直奉戰(zhàn)爭至豫泉局改組。豫泉局由于吳佩孚等橫征暴斂、需索無度,其紙幣發(fā)行更為泛濫、信用徹底崩潰。
據(jù)河南省銀行監(jiān)理官耿文華1924 年7 月報(bào)告,截至1924 年3 月31 日,豫泉局流通紙幣總量達(dá)19959812 元。河南省銀行成立后,豫泉局三種銀元票仍繼續(xù)流通,至1926年發(fā)行總計(jì)1200 余萬元。因河南財(cái)政廳通令各征收機(jī)關(guān),收解時(shí)改用現(xiàn)洋,于是豫泉局銀元票大跌,每元僅合二角一、二分。1926 年市面流通四種豫泉局銅元票共1800 余萬吊,但至1926 年每一吊銅元票,只值銅元七百二、三十文,“且稍有破爛,即當(dāng)廢紙?jiān)啤!痹ト旨垘诺慕Y(jié)局如廢紙一堆,被扔進(jìn)了歷史的垃圾堆里。
五 結(jié)語
(一)豫泉局影響封閉的地方貨幣圈形成
豫泉局設(shè)立雖早于湖北、直隸、廣東、東三省、江蘇等地官銀錢號(hào),但就形成的貨幣圈范圍來講,與后者無法相比。豫泉局流通無豫省自鑄銀元,銅元及紙幣局限于河南,省外幾乎無影響力。1904 年豫泉局總辦胡翔林為擴(kuò)張業(yè)務(wù),于北京、天津、上海、漢口、渦陽設(shè)立分局,除少量放款外,主要業(yè)務(wù)為紙幣匯兌。由于業(yè)務(wù)擴(kuò)張過快,資本有限,帶來嚴(yán)重虧損。故1912 年至1921 年間,豫泉局業(yè)務(wù)收縮于省內(nèi),以開封、鄭州、洛陽為中心。省外雖在滬、漢、津設(shè)立分支,但只有兌現(xiàn)業(yè)務(wù),極為慘淡,不久即停業(yè)。豫泉局在近代國內(nèi)貨幣市場影響力較弱,受制于河南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較低。
豫泉局造成河南貨幣圈封閉,還體現(xiàn)在它受地方政府、軍閥政治、經(jīng)濟(jì)利益訴求影響,與中央所設(shè)中交二行、平市官錢局相互抵制,這在軍閥割據(jù)出現(xiàn)后更為嚴(yán)重。在1912-1916 年間,遵照《取締紙幣條例》《各省銀行辦法大綱》,豫泉局只代理中交二行銀元票。1916 年后豫泉局自主發(fā)行銀元票,自然與中交二行產(chǎn)生競爭。豫泉局與中交二行在兩次停兌風(fēng)波中休戚與共,且同為國家金融機(jī)構(gòu),同負(fù)有維持河南地方經(jīng)濟(jì)穩(wěn)定發(fā)展職責(zé)。中央與河南地方政府本應(yīng)采取一致措施來應(yīng)對(duì),但雙方各站在地方、中央立場上,屢有齟齬和矛盾。如第一次停兌風(fēng)波發(fā)生后,河南省長田文烈一方面以財(cái)政困難為由拒絕歸還中行河南分行墊款,將該行30 多萬存款盡數(shù)提取,使該行搖搖欲墜,另一面卻讓豫泉局代理省庫,加劇該行危機(jī)。中行總裁王克敏向大總統(tǒng)馮國璋控訴,田氏此舉是對(duì)中行任意摧殘,“金融之機(jī)關(guān)已壞,財(cái)政之整理無從。誤國害民,雖死莫瞑。”至于豫泉局與平市官錢局的矛盾,前文已述,雙方爭執(zhí)從1918 年延續(xù)到1920 年。這是央地關(guān)系在金融領(lǐng)域的體現(xiàn),是幣制劃一性與地方性的體現(xiàn)。
(二)豫泉局使得河南幣改滯后、被動(dòng)
清咸同朝因推行大錢、鈔票制度,銀錢制度受到極大破壞。之后張之洞、袁世凱等地方督撫設(shè)立地方金融機(jī)構(gòu),試鑄銀元、銅元,發(fā)行紙幣兌換券,在大清銀行設(shè)立前,從局部到整體,實(shí)則引導(dǎo)近代幣制嬗變。這一方向就是以劃一銀元、銅元代替銀兩,制錢,促進(jìn)紙幣兌換券這一信用貨幣急遽推廣。反觀河南當(dāng)局設(shè)立豫泉局初衷,“自以鼓鑄為至計(jì),使制錢充盈,價(jià)值自平。”1904 年前仍以恢復(fù)制錢制度為根本。1904 年后受各地試鑄銀元、銅元沖擊,加之京漢鐵路通車直接影響,河南幣制才被迫調(diào)整。辛亥革命前,豫泉局通過發(fā)行、流通鈔票,兌換銅元作為維持地方幣制的主要辦法。由于河南無自鑄銀元,發(fā)行銀元票,兌收銀元是其另一辦法。
《國幣條例》頒布前后,豫泉局發(fā)行紙幣,流通銀元、銅元較為穩(wěn)定。但之后軍閥割據(jù)與混戰(zhàn),中央政權(quán)癱瘓,給金屬貨幣與紙幣統(tǒng)一帶來惡劣影響,河南幣制地方化特征凸出。豫泉局作為地方政府,趙倜、吳佩孚等軍閥控制河南金融、財(cái)政的工具,常常違背準(zhǔn)備制度,濫發(fā)銀元兌換券,吸收現(xiàn)洋,以供其所需。豫泉局紙幣更毋庸說有資格保持信用,作為有償債務(wù)貨幣了。1921 年第二次停兌風(fēng)波中,河南就發(fā)生各地錢商抵制豫泉局鈔票情況。1922 年錢業(yè)各商拒絕當(dāng)局與商會(huì)勸導(dǎo),張貼兌現(xiàn)、行用豫泉局紙幣的告示。
第一次停兌風(fēng)波后,“征收丁銀禁收錢票之說”在官方得到默許。故民間擔(dān)憂豫泉局紙幣官方若拒用,“不知將來金融之救濟(jì)當(dāng)用何策?”這一擔(dān)心在1922 年變?yōu)楝F(xiàn)實(shí),豫泉局鈔票“納賦購車票等事”被拒收。“故該票一至民手,即如同廢紙,是以此種巨款,即無形歸于人民負(fù)擔(dān)。”
發(fā)行紙幣兌換券是豫泉局后期主要業(yè)務(wù),也是將其置于萬劫不復(fù)的原因。紙幣在近代泛濫或畸形發(fā)展,一為工商業(yè)發(fā)展驅(qū)動(dòng),方便流通、兌換;一為地方經(jīng)濟(jì)疲敝,財(cái)政困難,現(xiàn)金匱乏。河南無疑后一因素更多。紙幣成功發(fā)行取決于政治穩(wěn)定,取決于政府、金融機(jī)構(gòu)、社會(huì)大眾之間確立信用、契約關(guān)系。但這兩個(gè)條件,豫泉局紙幣均不具備,故其不具有信用貨幣全部職能,只能充當(dāng)?shù)胤疆?dāng)政者的理財(cái)工具,替代金屬貨幣的兌換券而已。
由于河南在流通市場上無競爭力,現(xiàn)金匱乏。地方軍閥又不斷通過豫泉局吸收現(xiàn)金,將財(cái)政、金融手段雜糅,滿足其軍政開支所需,進(jìn)一步加劇現(xiàn)金荒。這使得豫泉局紙幣在河南貨幣流通市場上必然起到突出作用,造成紙幣流通、發(fā)行“過熱”“早熟”現(xiàn)象。
近代類似河南,最初因通貨不足、財(cái)政困難、金融滯礙,自設(shè)地方金融機(jī)構(gòu)的省區(qū)還有很多。這些地方金融機(jī)構(gòu)先后掌控在地方督撫、軍閥手中。其維持金融、財(cái)政的手段大都類似,以發(fā)行兌換券為主要手段,以保障與銀元、銅元的兌換為主要目標(biāo)。這些兌換券與銀元、銅元大都是地方貨幣,省區(qū)之間,省區(qū)與中央之間互相沖突,抵制。但就是在這一極端方式下,銀錢制度逐漸瓦解,改用統(tǒng)一國幣(銀元)逐漸被認(rèn)同。在此基礎(chǔ)上,為推廣使用銀本位的全國統(tǒng)一紙幣,從金屬貨幣時(shí)代進(jìn)入到信用貨幣時(shí)代,慢慢奠定了基礎(chǔ)。
[1] 《宮門鈔》,《申報(bào)》,1896 年9 月2 日。
[2][54]《河南巡撫劉樹堂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卷宗號(hào)04-01-35-1374-032。
[3] 《河南巡撫劉樹堂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折》第九十二輯,中華書局,1996 年,第99 頁。
[4] 《光緒二十八年綜合資料:錢幣(二)》,河南省檔案館藏河南巡撫衙門檔案,卷宗號(hào)Q1-1-235。
[5][11][12][19][20][28][29][35][42][52]《河南幣制與匯兌事業(yè)》,《申報(bào)》,1919 年9 月18 日。
[6][22][47]《河南金融之現(xiàn)狀》,《申報(bào)》,1921 年4 月8 日。
[7] 河南省滑縣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huì):《重修滑縣志》(上冊(cè)),1986 年,第593 頁。
[8] 賈士毅:《民國財(cái)政史》,商務(wù)印書館,1917 年,第115-116 頁。
[9][17][40]周葆鑒:《中華銀行史》,商務(wù)印書館,1923 年,第17 頁。
[10] 《河南省財(cái)政廳擬定各縣局解繳庫款手續(xù)辦法規(guī)則》,河南省財(cái)政廳:《河南財(cái)政廳章則輯覽》,1922 年,第158 頁。
[13][51]上海商業(yè)儲(chǔ)蓄銀行國內(nèi)匯兌處編:《國內(nèi)商業(yè)匯兌要覽》,商業(yè)儲(chǔ)蓄銀行,1925 年,第417-426 頁。
[14] 《河南巡撫陳奏豫省銀賤錢荒現(xiàn)經(jīng)設(shè)局開鑄銅元以資補(bǔ)救折》,《東方雜志(第一卷)》,1904 年第十一期。
[15] 《考察銅幣大臣陳璧折——考察各省銅元鑄造情形》,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金融史料組編:《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一輯(清政府統(tǒng)治時(shí)期),中華書局,1964 年,第875、882-884 頁。
[16] 張新三:《中國機(jī)制銅元簡史》,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huì)議河南省委員會(huì)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huì)編:《河南文史資料選輯(第11 輯)》,1984 年,第182 頁。
[18] 《河南官銀號(hào)提調(diào)王令宰善稟撫院劃一幣制謹(jǐn)陳管見文(附錄)》,甘厚慈:《北洋公牘類纂續(xù)編》,臺(tái)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第708-709 頁。
[21] 《開封:會(huì)議救濟(jì)銅元辦法》,《申報(bào)》,1917 年2 月21 日。
[23] 《河南省禁止銅元入境章程》,河南省財(cái)政廳:《河南財(cái)政廳章則輯覽》,1922 年,第147-148 頁。
[24] 《河南省長趙倜咨財(cái)政部文——反對(duì)平市官錢局在豫設(shè)局發(fā)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金融史料組編:《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一輯(1912-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548-549 頁。
[25] 《中國銀行總管理處致財(cái)政部函》,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金融史料組編:《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一輯(1912-1927),第550 頁。
[26] 《金融恐慌之因果》,《申報(bào)》,1917 年4 月3 日。
[27] 《豫人所受易督影響》,《申報(bào)》,1922 年11 月11 日。
[30] 《河南省限制銀元出境章程》,河南省財(cái)政廳:《河南財(cái)政廳章則輯覽》,第149-150 頁。
[31] 《現(xiàn)洋陡漲之原因》,《新中州報(bào)》,1918 年1 月15 日。
[32] 《豫泉局吸收現(xiàn)款》,《新中州報(bào)》,1919 年1 月15 日。
[33] 《幣制節(jié)略》,財(cái)政部錢幣司編:《幣制匯編》第一編,1919 年,第70-71 頁。
[34] 《財(cái)政部檢查征收機(jī)關(guān)委員會(huì)抄送有關(guān)河南豫泉官銀錢局沿革及現(xiàn)狀并準(zhǔn)備金暨發(fā)行紙幣數(shù)目清單付》,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金融)》,第740-741 頁。
[36] 《各省理財(cái)匯志》,《東方雜志(第一卷)》,1904 年第十期。
[37] 《幣制大臣改良圜法之手續(xù)》,《申報(bào)》,1911 年9 月12 日。
[38] 《大總統(tǒng)令》,《政府公報(bào)》,1913 年11 月8 日第544 號(hào)。
[39] 參見楊濤:《民初北京政府整理濫幣問題研究》,《安徽史學(xué)》,2012 年第6 期。
[41] 《收現(xiàn)》,《新中州報(bào)》,1918 年1 月17 日。
[43] 《洛陽近聞一束》,《順天時(shí)報(bào)》,1920 年3 月4 日。
[44] 《各省官銀行發(fā)行紙幣數(shù)目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金融二),第199 頁。
[45] 《河南公民彭既安等陳控豫督兼省長趙倜劣跡給大總統(tǒng)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軍事三,第728 頁。
[46] 《河南有限制兌現(xiàn)觀》,《申報(bào)》,1921 年11 月29 日。
[48] 《豫當(dāng)局將強(qiáng)迫流通豫泉鈔(開封特約通信)》,《晨報(bào)》,1922 年3 月5 日。
[49] 參考:《豫泉官銀錢局截至民國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票幣流通一覽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金融二),第743 頁。本表作適當(dāng)修改。
[50] 子明:《備省濫鈔禍民觀》,《銀行周報(bào)》,1926 年第10 卷第20 號(hào)。
[53] 《王克敏與田文烈》,《申報(bào)》,1917 年10 月30 日。
[55] 《河南有限制兌現(xiàn)觀》,《申報(bào)》,1921 年11 月29 日。
[56] 《豫兩行停兌之金融》,《申報(bào)》,1921 年11 月25 日。
[57] 《開封通信》,《京報(bào)》,1922 年1 月10 日。
[58] 《豫省財(cái)政金融之黑幕 增加正稅外又加附稅 豫泉鈔票只出不準(zhǔn)入》,《晨報(bào)》,1922 年4 月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