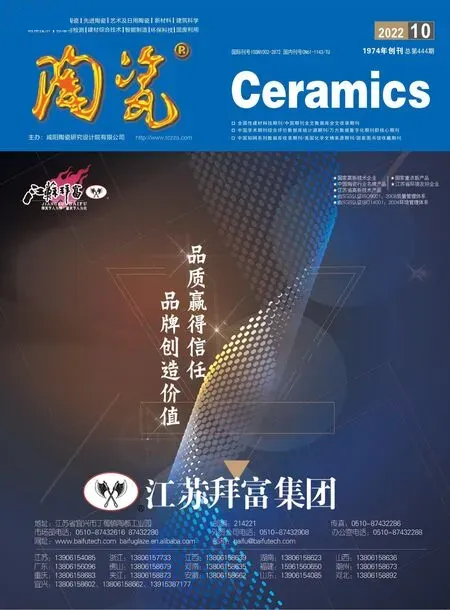喀什民間土陶釉料的生產工藝與技術體系研究*
朱慶禮 田 軍
(喀什大學 新疆 喀什 844008)
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喀什民間土陶,具有悠久的生產歷史,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優秀代表。喀什地處塔里木盆地西緣,獨特的地理、氣候、礦產分布等,使民間土陶在釉料制備方面立足本地自然資源,有獨特的地域特色,其釉料對土陶色彩的最后呈現有關鍵性作用。
關于喀什土陶的制釉技術,國內公開發表的各類文獻中,有兩種表述:①認為是源于關中和中原地區的鉛釉技術,沿古代絲綢之路傳播至塔里木盆地地區,在當地生產后一直不間斷地保留下來;②認為是源自西亞的錫釉技術,隨著小麥的種植和面食的傳播路徑,傳入古西域地區。筆者試從喀什民間土陶的釉料生產工藝出發,對比鉛釉和錫釉技術體系及釉彩特征,對喀什民間土陶的釉彩技術進行研究,以期厘清技術認識上的誤區。
1 中國的多彩鉛釉體系及釉彩特征
鉛釉工藝出現于西漢時期的關中地區,至東漢時期在黃河流域和整個中國北方地區燒制出黃色、綠色的單色釉陶器。唐代時在國都長安和東都洛陽用來制作日用陶器、建筑用陶,也大量用于明器的燒造,出現了世界陶瓷工藝史上著名的多種釉色的唐三彩陶器。歷經宋、遼、元、明、清各代,發展出了磚瓦和其他建筑構件等不同系列陶器品種。
低溫鉛釉陶器是我國陶瓷制造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品類,以唐三彩為例(見圖1),它是用陜西和河南當地的白色粘土制作胎坯,塑造成形、干燥后,先入窯以1 000~1 100℃的溫度燒出素坯,然后在燒過的素坯上施以配制好的各種低溫釉料,二次入窯以850~950℃的溫度用氧化氣氛燒制而成。這種低溫釉料是以氧化銅、氧化鐵、氧化鈷等作為著色劑,以鉛的氧化物作為助熔劑,配以石英制作而成的透明釉。釉的制備在古代稱為炒鉛,先將作為制作色料的母體原料的鉛礦石或鉛塊,放在鐵鍋中用文火加熱,慢慢翻炒成為黃色的粉末狀,過籮篩細后用清水漂洗,去除沉渣后就可用以配釉。氧化鉛(Pb O)的熔點為886℃,可以有效降低釉料的熔融溫度,增加釉料的流動性,在燒成時各類金屬著色劑熔于鉛釉中并往下流淌四處擴散,各種顏色相互浸潤,以燒制時的狀態從上到下產生由淡到濃的層次變化,釉面光亮度高,釉層清澈透明,表面平整光滑,猶如彩云般變幻飄渺,顯得五彩繽紛、光彩奪目。三彩陶器以其輝煌絢麗、雍容華貴的風韻,成為中國古典文化的一個象征,在陶瓷史上久負盛名。

圖1 唐代三彩雙龍柄壺
2 錫釉體系及其釉彩特征
錫釉陶器大約在公元9世紀出現于中東地區的兩河流域,并于10世紀后相繼傳入埃及以及阿拉伯人治下的西班牙南部。錫釉技術于13世紀傳入意大利,在文藝復興時期開放自由的人文藝術氛圍中,以法恩扎為中心開始形成重要的陶瓷產區,其生產的錫釉陶“馬約里卡”在15~16世紀得到空前繁榮發展,并迅速傳遍歐洲。
與氧化鉛在釉中作為助熔劑不同,氧化錫在釉中是起到乳濁劑的作用。二氧化錫(Sn O2),別名氧化錫,白色無定形粉末,熔點為1 127℃。制備錫釉時,一般是將錫與鉛混合生成二者的氧化物,混合在基釉(如堿硅酸鹽)中,加熱冷卻后生成氧化錫重結晶,即不透明的白色錫釉。胎坯素燒后,表面浸掛釉液,二次入窯以1 000~1 200℃的溫度在氧化氣氛中燒制而成。因氧化錫不熔于釉,以懸浮態存在于玻璃體中,形成非常高的折射率,增加了釉的不透明度,起到遮光劑的作用,形成不透明的白色釉面,非常適合進一步用繪畫來裝飾,所以,常用含有各種金屬氧化物作為著色劑的顏料在表面繪制圖畫,形成很強烈的彩繪裝飾風格,如圖2所示。

圖2 意大利錫釉陶盤
3 喀什土陶釉料生產工藝與釉彩特征
3.1 制釉工藝
制釉工藝對產品的最終效果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是喀什民間土陶整體工藝中最具隱蔽性的技藝,各作坊對制釉工藝均采取嚴格的保密態度,視為“絕技”互不外傳,故每家釉色在總體風格一致下又有細微差別。通過課題組的調查,可以判定喀什土陶是鉛釉技術,采用傳統的“炒鉛”工藝制作(見圖3)。土陶藝人先將鉛塊、從戈壁灘上采集的天然長石和石英石等按比例配好,放在鐵鍋中用文火加熱翻炒,使原料逐漸變成粉狀,冷卻后用細目篩過籮,再用清水進行漂洗,將沉渣去除后,即成為基礎釉。使用時,根據釉彩顏色的要求在基礎釉里面加入鐵、鈷、銅等起發色作用的金屬氧化物作為色料。各種金屬氧化物在低溫燒制時呈色不同,如銅氧化物呈綠色;鐵氧化物呈黃褐色和棕紅色;鈷氧化物生成藍色。至于具體的呈色效果,則在各作坊藝人心中有一份配方賬本,而外莫能知。
3.2 釉彩裝飾
喀什土陶除模制法成形的有一定規制外,傳統的輪制法成形產品常為一次成形,一般不做修坯加工,坯體表面往往留有藝人的手工痕跡,同一器型就有著細微的差別。土陶藝人在拉坯過程中,常會在瓶壺的口沿下方拉出一圈薄泥片,再用手或其他工具上下跳動將泥片擠出造型,也常有用身邊隨便的什么工具在濕坯表面直接劃花,依形布勢,講究一氣呵成,無拘無束。待坯體干燥后,只需將多余的泥刺用手輕輕拂去即可,天然成趣,人性與泥性渾然一體。
干燥后的坯體上,也可以用較鋒利的金屬工具進行刻花,傳統上以植物、幾何圖案為主,絕少出現動物、人物、風景等現實主義題材的繪畫。近年來,隨著在政府的組織下不斷赴內地陶瓷產區進行參觀交流,土陶藝人吸取他處之長,對陶器的劃花越來越少,刻花工藝逐漸加強,工藝技術越來越精致,圖案也越加繁復,現實主義的題材在作品中也越來越多的出現。
土陶藝人經常將化妝土彩繪裝飾和釉彩裝飾結合起來,使產品產生一種不同于其他地方的裝飾風格。喀什土陶的化妝土制作有兩種方法:①采集喀什當地含有一定金屬氧化物的天然礦物質,磨粉后加水調制即可直接使用;②土陶藝人有意識的將粘土原料中較為淺色的部分篩撿出來,用制釉的金屬氧化物加入進去做發色劑。經常是家中的女性或老年成員,在制作好的坯料上,用化妝土直接描畫,圖案有巴旦木紋、石榴紋、卷草紋、葡萄紋等,各家沒有固定范式,全憑口傳心授和自由想象,甚至是由主人的心情決定,顯得天然成趣、靈動絕妙。
用化妝土裝飾好的土陶,再在表面施以釉彩。土陶藝人在施釉時經常會有意先用一種釉料繪制花紋圖案,再通體施另外一種釉料,或者干脆幾種釉料混合施釉,燒制后陶器表面各種色料混合交融,顯得猶如艾德萊斯絲綢般異彩紛呈,別有一番民族審美情趣,如圖4所示。

圖4 喀什土陶的釉彩
3.3 釉彩特征
喀什民間土陶采用素坯直接上釉,入窯以約835℃的溫度在氧化氣氛中一次燒制而成,也有少部分作坊采用二次復燒的方法燒制質量和藝術要求較高的產品。陶器的低溫鉛釉具有粘度較小、熔融性比較強的特點,造成釉面流動性較大,金屬氧化物熔于釉中向四面尤其是低處流動,造成色料絲絲如發的絮狀質感,釉表面光滑平整,釉層呈清澈的透明狀,光澤度很好。因燒成溫度的原因,坯體不夠致密,釉層與坯體的結合不夠緊密,易產生釉層剝落現象,釉面硬度較低,易產生劃痕。
4 鉛錫之辨
4.1 制釉工藝
從制釉工藝上來講,喀什土陶可以明確地判定為鉛釉技術體系。原因有3:①從筆者田野考察采集的各作坊釉料樣本分析,氧化鉛成分都在40%以上;②筆者現場觀摩的民間土陶藝人制備釉料的過程中,明顯可見為黃色粉末狀,這符合氧化鉛黃色結晶狀粉末的理化性質;③基于傳統工藝在歷史傳承中的穩定性特征,陶器的生產是物質層面的,技術的傳承則是精神層面在歷史上的見證,在前現代的中國社會,技術的產生往往需要在漫長的生產過程中總結提煉,這種總結提煉的背后是巨大的時間成本,人們不會輕易改變一種能夠有效促進生產發展的技術體系。在田野考察中筆者也發現,民間藝人對相關手藝有很強的保守和保密心理,害怕技術外傳導致自身利益的受損,各土陶作坊也確實有“傳內不傳外”、“傳媳不傳女”的授業傳統。
4.2 釉彩特征
從釉面光澤度上來講,喀什土陶釉面反射率很高,觀之有光亮如鏡的美感,符合中國傳統鉛釉的釉面特征。從釉層上分析,喀什土陶玻璃質清澈透明,光彩照人,透過釉層肉眼可見胎底,與錫釉不透明的白色釉底迥異。從釉的熔融性上分析,明顯可見各種色料在低溫釉料中相互浸潤,形成五彩斑斕的色彩效果,與三彩陶一脈相承。
4.3 絲綢之路的傳播
原產自中國的陶瓷,一直是絲綢之路上的暢銷品,產量大,出口量多,深受絲路沿線各地人們的喜愛。由于唐三彩高超的制作技術和動人心魄的藝術品質,早在唐代就隨著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流傳至世界各地,如東亞的日本、朝鮮半島,南亞的印度、巴基斯坦,中西亞的伊朗、伊拉克、阿富汗,非洲的埃及等地,古代遺址中都出土了唐三彩。作為古絲綢之路南道和北道重要交匯點的喀什,在接待從長安和洛陽沿著絲綢之路而來的客商和物產的同時,接受流傳過來的三彩陶制作技術,依托當地物產就地生產,是非常合理可信的。
事實上,近年來在喀什周圍的古代遺址考古發掘中,不斷有唐代中原風格的陶器出土,這是作為絲路重鎮的喀什受到唐代陶瓷文化直接影響的重要證據。唐中期安史之亂后,隨著中國北方地區連年戰火,影響了東西方的陸上貿易,絲綢之路逐漸走向低谷,人流和物流逐漸減少。東面被塔克拉瑪干沙漠包圍,北、西、南被天山、蔥嶺、昆侖山阻隔的喀什,也逐漸失去了與外界進行大規模交流的機會。但來自中原的三彩燒制技術,在喀什周圍一直沒有間斷地生產著,這也是喀什鉛釉陶器,裝飾華麗色彩斑斕,較多地保留有三彩陶器遺風的原因。
5 結語
最早發表的有關喀什土陶是錫釉技術的文獻,目前已不可考證,但綜合筆者以上論述,應不是基于技術研究的結論,而是出于陶瓷技術之外的其他原因。后期研究者在使用文獻時并未加以考證而是直接采信,導致目前在有關喀什土陶研究中的鉛釉和錫釉技術體系認識上的混亂。
綜合本文的以上論證,可以判定喀什民間土陶在釉料生產工藝上采用的是鉛釉技術體系,與源自關中和中原地區的鉛釉技術一脈相承,是中國低溫鉛釉陶大家族中的重要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