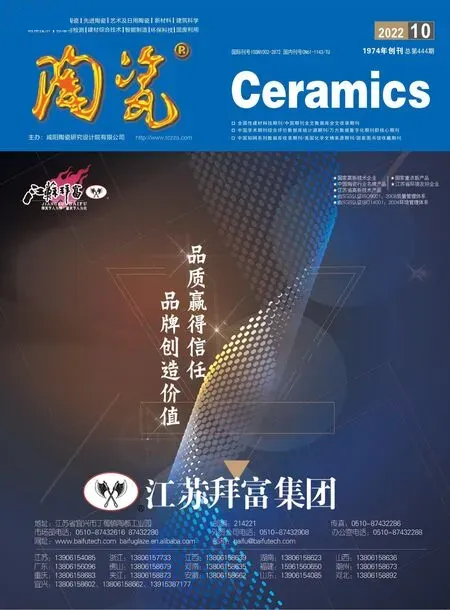民初新粉彩桃花美女瓷繪的藝術表現手法*
黃瑩瑩
(景德鎮陶瓷大學研究生院 江西 景德鎮 333400)
“桃花美女”一詞首先會讓人想到崔護的《題都城南莊》:“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1]首次將“桃花”與美貌女子聯系起來表達一種美好的情事和感傷無奈之心緒,而將“桃花”與女性相結合應用最為突出的要屬清代,清代孔尚任的戲曲《桃花扇》以“桃花”為劇名,表現一場凄美的愛情故事,曹雪芹《紅樓夢》中“黛玉葬花”一篇中黛玉憐桃花飄落,將它葬于花冢。不僅文學領域,清末畫壇也出現了一批表現“桃花美女”的仕女畫家,如改琦、費丹旭,所繪仕女人物嬌柔纖弱,身材窈窕,代表作如改琦《紅樓夢圖詠》,費丹旭《紅樓夢人物圖》。錢慧安,吳友如等人是海上畫派的大家,而他們的繪畫風格也都有繼承和借鑒過改琦、費丹旭等人的繪畫之風,并對他們的繪畫藝術風格的形成產生重要影響。與此同時,另一種藝術形式也深受其影響,如晚清的淺絳彩瓷繪中的仕女畫人物形象,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完全承襲了“改費”之風[2],使瓷繪仕女畫呈現一派媚態柔弱的女性形象。其中就出現一種“桃花美女”瓷繪類型,清末(1840~1911年)淺絳彩瓷仕女畫以桃花與美女相結合,反映仕女清閑舒適的生活畫面的紋飾,這種紋飾被稱為“桃花美女”[3]。所繪仕女皆弱柳扶風,人物多著明代仕女服裝,衣帶飄逸,長裙拖地不露足,仕女或坐石倚欄,撲蝶拈花、讀書教子,背景多為深閨庭院,院內多描繪假山石、柵欄、桃樹一株或數株,周圍用芳草點綴,畫面淺淡的淺絳彩技法為主,輔之用粉彩來表現桃花。
民初(1912年~1929年)新粉彩完全取代淺絳彩成為瓷繪技法主流之后,“桃花美女”瓷畫的色彩更加濃重亮麗,“新粉彩在傳統粉彩和淺絳彩的基礎上發展而來,施彩方式是先是在潔白的瓷坯上勾畫裝飾紋飾的輪廓,在輪廓內用‘玻璃白’打底,再通過填色工藝中的洗染、油染、點染等不同工藝手法,用彩料在上面作畫”[4]。這種繪畫方式,目的是使繪畫顏色呈現出濃淡漸變之感,有柔和的過渡顏色。圖1為益友齋1916年作仕女戲兔紋雙耳長頸瓶,身穿高立領窄袖上衣,藍色馬面裙的女子站立于假山石前,腳邊兩只白兔,山石后繪桃花芭蕉。圖2為1921年“利生工廠”作桃花美女圖葉形瓷飾片,圖中女子立于桃花園中,身穿露腕上衣,七分長褲,天足,短發,手拿一束桃花,美女形象突破傳統仕女嬌弱的體態和長袖飄舉的服飾,穿上了民國新潮的時裝,人物形象清新亮麗,自信優雅。

圖1 仕女戲兔紋雙耳長頸瓶

圖2 桃花美女圖葉形瓷飾片
民初新粉彩桃花美女瓷繪是中西方藝術手法相互交融的產物,立足于傳統陶瓷繪畫的藝術根基,突破傳統彩繪技法,而創造性地使用民國新粉彩瓷繪技法,在形象的整體勾勒上使用中國畫筆墨技巧,以及“六法”的指導,遵循著詩書畫印一體的文人畫風格。與西方繪畫的融合上,在瓷繪中有意識地運用透視規律進行構圖,色彩的處理上可以看到類似西方水彩畫風格一樣的色彩濃麗,顏色過渡柔和,通透細膩的人物表現手法。這些表現手法的相互作用共同促進了民初新粉彩桃花美女瓷繪藝術的形成。
1 運用民國新粉彩瓷繪技法
清末景德鎮出現了釉上彩新品種——淺絳彩,淺絳彩色彩不鮮亮,易于脫落導致被新粉彩所取代,新粉彩的材料起初來自進口,色彩濃麗,柔美明快,使畫面形象更加明艷奪目,符合民國時期新興市民階層的審美。“珠山八友”最活躍的重要時期,大約在20 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5]。從對民初新粉彩桃花美女瓷繪的作品的彩繪技法上分析,能夠直觀看到對新粉彩工藝的運用,傳統粉彩顏色過渡色使用較少,色彩較為呆板。新粉彩用“玻璃白”打底,再用不同的洗染手法,使每一種顏色都有過渡色,有濃淡變化。《景德鎮瓷業史》記錄道:“此外有洋彩,系外國傳來之飾瓷方法,為時約在清光緒之際(非乾隆時之洋彩),其顏色鮮艷,繪畫手續比較簡單,現在景德鎮很盛行,此種顏料先多由德國輸入,近來全為日本貨。”[6]由此可知,新粉彩由海外傳入,清末由于通商口岸的開放,景德鎮瓷畫家得以獲悉國外先進的原料,從而摒棄了色彩易脫落,不夠鮮亮的淺絳彩瓷,新粉彩在民初之后大放異彩。
2 繼承中國畫技法和文人畫風格
民初新粉彩桃花美女瓷繪繼承運用中國畫中以工筆兼寫意刻畫人物的手法進行桃花美女瓷繪的繪制,中國畫風格也可以在民初新粉彩桃花美女瓷繪的題款中找到證明,桃花美女瓷繪中常見到如“仿六如主人之書”、“仿六如之法”、“仿云林居士之意”等字樣的題款,“六如主人”即明代畫家唐寅,字伯虎,號六如主人。可以看到桃花美女瓷繪對于中國畫技法的承繼和風格的借鑒。針對中國古人寬衣大袍的服飾,古代畫家在對人物衣紋褶皺進行表現的線描技法上總結出“十八描”,民初新粉彩桃花美女瓷繪中人物形象以線造型的特點顯而易見,改良前的相對寬大的服裝輪廓與衣褶的轉折多用粗筆勾勒,體現民初新粉彩桃花美女瓷繪創作前期的半襲舊制服飾風格中留存的形象板滯之感,而改良后的“文明新裝”,用線相對較細,簡約流暢,體現出衣著自由后的人物形象的輕松自如及休閑之感,特別是人物的垂絲劉海,細絲分明可數。
“珠山八友”對民國陶瓷文人畫風格具有重要影響,作為一個重要的團體對景德鎮其他群體的創作也會帶來影響,景德鎮的新粉彩桃花美女瓷繪家在從事桃花美女瓷畫之前從事過淺絳彩瓷畫的創作,在轉型期受到其他主要團體的創作影響,沿用了淺絳彩文人畫的技法,強調瓷畫中詩書畫印的結合[7]。桃花美女瓷繪每一件作品都有配詩文,有直接采用古詩來形容,也有根據畫面自行創作,但大多數詩文重復率較高,配詩偏向程式化,如“玉人如花月,美色正清華”、“汗濕紅妝花帶露,云堆綠髻柳拖煙”、“國色何須脂粉加,天然素質靜無暇”等。因此,民初新粉彩桃花美女瓷繪也是“舊瓶裝新酒”的一種瓷繪品種,保持中國畫形式符合民國時期部分文人的審美,另辟新題材則符合新興市民階層的審美需要,從陽春白雪走向雅俗共賞是民初新粉彩桃花美女瓷繪的一種新追求。
3 吸收西畫透視規律構圖
“透視”一詞屬西方繪畫理論專用名詞,在西方一般指焦點透視,即觀者站在一個視點觀看事物時,事物產生近大遠小的視覺現象,并將視點集中消失于視平線的一點。清代鄒一桂在《小山畫譜》記載關于西洋畫的技法和評論:“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繪畫于陰陽遠近,不差錙黍,所畫人物屋樹,皆有日影,其所用顏色與筆,與中華絕異,布影由闊而狹,以三角量之,畫宮室與墻壁,令人幾欲走進……。”[8]西洋畫依照透視法理性作畫,追求景物的立體感,人物形象的逼真,以再現現實為目的。中國古代繪畫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到的“高遠”、“平遠”、“深遠”的繪畫理論也屬于透視理論的之中,只是視角不同,帶來的視覺感受亦不同。中國繪畫視覺處理常用透視即人們常說的散點透視,是一種多視角觀看景物的方式,也就是眼睛觀看所到景物,就是描繪的焦點,這種方式可以描繪更加寬闊的視野。民初新粉彩桃花美女瓷繪是對于家居生活場景,這種獨特的視角的一種描繪,并以特定的角度、一定的距離遠近,在某一確定好的視覺焦點上進行描繪,這種方式就可以使畫面看起來有一種近大遠小的透視感覺[7]。但細細分析可以發現這種透視感覺是在整體上來呈現的,人物的安排遵循的是社會尊卑。如圖3洪步余繪《藤下聚美圖深腹蓋罐》,近處的人物偏小而且處于視覺的下方,而遠處圍墻之內的人物卻明顯較大。圖4為洪步余1920年繪《堂前話語圖撣瓶》,近處的女子和孩童較小,而位于桌角對面的女子卻顯高大,顯示出女主人的尊貴之態。圖5為1924年祥興春繪《雙美游玩圖倭瓜罐》,從畫面直接可以看到人物身后的屋內一墻角,在西方透視理論中稱為成角透視,屬于兩點透視的范疇,這種透視的特點是左右兩側面延伸消失于左右兩側的一點,體現圖畫面的三度空間感。不太規范的透視法畫法,一方面由于瓷器非平面紙質易于表現,另一方面瓷繪家承襲了傳統中國畫散點透視的方法,而非全盤接納西式畫法,藝術上的“西為中用”也是民國初期景德鎮瓷業發展的重要革新方式。

圖3 藤下聚美圖深腹蓋罐

圖4 堂前話語圖撣瓶

圖5 雙美游玩圖倭瓜罐
4 結語
從藝術表現手法上看,民初新粉彩桃花美女瓷繪以中國傳統繪畫技法為基礎,吸收西洋繪畫規律為創作所用,是中西融合的藝術表現手法,然而從外部的形式還可以窺見更深的敘事內容。首先,景德鎮瓷畫家從國外引進色彩濃艷俏麗的釉料,創造出新粉彩瓷繪風格,為民初景德鎮日益衰落的瓷業開辟了新的發展道路,反映出民國時期景德鎮瓷繪家對于瓷業振興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在技術創新上開放包容的態度。其次,以傳統國畫技法和西方透視法相結合并在整體畫面上采用詩書畫相結合的文人畫結構,一方面契合了舊式文人的審美,另一方面迎合新興市民階層的審美需要,這種藝術手法使瓷器在商業上獲得發展,也使民初景德鎮瓷業得以興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