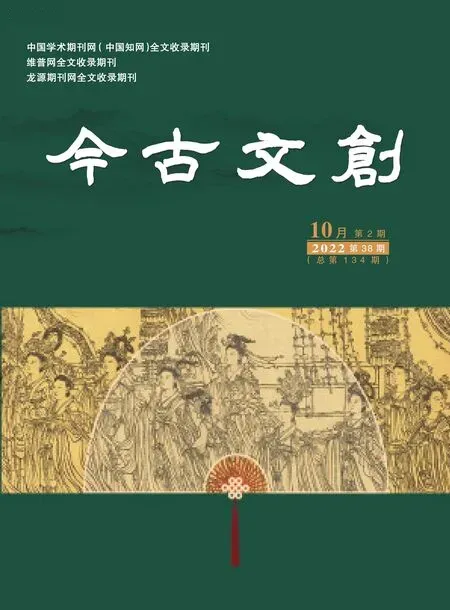福克納《我彌留之際》主題的接受美學解讀
◎蔣竺峰
(安徽師范大學 文學院 安徽 蕪湖 241003)
一、作品的“召喚結構”和文學接受
德國接受美學的代表人物沃爾夫岡·伊瑟爾提出“召喚結構”這一理論,他認為文學作品由文本和讀者兩個方面構成,讀者與文本存在一種互動關系,作家所寫成的文學文本具有召喚其創作之時所預想的潛在讀者的結構機制。伊瑟爾是在改造和創新現象學代表人物英伽登的文學藝術作品認識論以及闡釋學代表人物伽達默爾的視域融合論而提出這一理論的。在英伽登看來,一部作品的意向關聯物就是事物之多重圖式化方面的組合體或綱要略圖,它有許多“未定點”和空白需要讀者的想象來填充或“具體化”。在此基礎上,伊瑟爾認為,文學文本在成文之時不斷喚起讀者在閱讀期待作品時在既有視域的基礎之上,但喚起它不是為了讓讀者依照作者的意愿循規蹈矩,而是為了打破它,使讀者獲得新的審美閱讀視域,喚起讀者填補不定點、連接空缺、更新視域的文本結構,即所謂“召喚結構”。對閱讀的召喚性不是外在于文本的東西,而就是文本自身的結構性特征。依伊瑟爾的論述,召喚結構是將文學關注視點由關注文本本身到重視讀者閱讀對作品多重意義的生成作用,在相對穩定的視域中,一部作品所容納的復義元素越眾多而模糊,就越能激起讀者積極參與文本意義的建構,從而對作品接受和研究視野會更為廣闊和開放。福克納所作小說《我彌留之際》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吸引讀者的閱讀興趣就在于他敘述風格所形成的“召喚結構”。其具體體現在:
(一)敘述者多聲部獨立章節講述,各部分單一人物發聲,故事片段組合拼湊成為作品,會存在故事留白空間,引發讀者主動重組完整故事。小說共分為五十九個章節,其中包含十五個第一人稱敘述視角“我”的敘述者(包括本德侖一家七位和八位主要鄉鄰)來共同發聲的,每一章節以個人獨白來敘寫,其中包含各個人物的內心獨白、引述對話和情感判斷,采用第一人稱視角來推進。(除開第五十七節因情節需要未采用)再結合小說原標題,通俗直譯就是“當我躺著等死”(As I Lay Dying),常規閱讀思維會考慮到文本內容是主人公“我”在“等死”過程中所發生的一系列故事或者情節,但故事并非如此去展開。事實上是,大家所預想的標題里面出現的主人公“我”在文章情節出現的頭一天傍晚就已死去,小說所展示的主要情節并不是在“等死”之際,而是在標題中的“我”死去之后,標題中出現的“我”便是本德侖一家的女主人艾迪,但在正文敘事中“我”被分割為了十五個敘述者,與常規敘事角度筆法相異,暗含深意的分割“我”會造成讀者閱讀困惑,等待讀者介入其中去構筑關于“我”這一敘述主體完整的故事情節。正如王長榮在《美國現代小說史》中所言說:“福克納小說創作上的一個特點就是打破線型敘事順序,打亂時間順序,把故事分解成許多片段,讓各種人物從不同的角度講述故事。這樣就“迫使人們都從美學和道德上進行探索,讀者也被卷入了故事。”
(二)文中各個人物視角有限,依托自我價值取向和愿望來推動故事情節發展,召喚讀者作推理。小說以描寫美國南方普通農民家庭本德倫一家為主要故事背景,以運送女主人艾迪的遺體回家鄉杰克遜墓地安葬為脈絡。每一章節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我”各有打算和歸宿:男主人安斯想要裝假牙、大兒子一心打造母親的棺材,為運送棺材過河折了腿、三子珠爾為母親安葬湊買運送的騾子舍棄了自己最心愛的馬、女兒杜薇·德爾要買墮胎藥、幼子瓦德曼想要買小火車。而結尾卻是二兒子達爾因燒谷倉而被抓進瘋人院,杜薇·德爾沒有買到藥卻被猥褻,小說最后男主人安斯有了假牙,而迎娶新老婆。在所有章節中,某一件事會重復出現,但因不同敘述者價值觀、情感取向、愿望不一而各執一詞,因而作為賦予了每一敘述者有解讀其他敘事者的話語權力,比方說在達爾的話語體系里他弟弟珠爾眼里的母親是匹馬、而在幼子瓦德曼自己眼里俺娘是條魚。書中各個敘述者多元的價值判斷會促使讀者自己也想參與其中,發出自己的聲音,形成自我觀點。
(三)不合乎日常思維和邏輯的陌生化語言或意象,使得讀者莫衷一是,難以理解。在伊瑟爾看來,文學語言是一種待解讀的描述性語言,具有多重意義的可能性。小說中有諸多語言描寫和心理描寫匠心獨運,回味無窮,而最具特色的是福克納會賦予角色以獨特的語言和心理意象,形成語言的“復調性”。比如說達爾的話語和心理世界帶有迷狂和詩意,這是書中其他敘述者不具備的。除此之外,書中有部分章節的敘述者處于類似半夢半醒的心理狀態,因而敘述文本不帶標點符號,是一連串、不間斷的文本符號,這也是其語言特色。其小說打破了傳統意義上作品意圖僅依靠作者創作意圖所闡釋的體制。藝術作品的存在就是那種需要被觀賞者接受才能完成的游戲。所以對于所有文本來說,只有在理解過程中才能實現由無生氣的意義痕跡向有生氣的意義轉換。福克納在寫作時有意調動讀者參與進來,因此,讀者主動參與文本的解讀才能使其煥發新的活力。
二、小說主題涵義的多重意蘊
對于《我彌留之際》小說的解讀,大家要破除傳統小說那種單一的、線性的故事結構這一模式,福克納的小說創作往往是三維立體和多側面的。可以以各敘述主體的行動目的為切入,融合對于其語言風格、情節走向、環境描寫來進行主題意義的探尋。
(一)家庭小說。一般意義上來說,它是一部家庭小說,關于美國南方普通農民家庭的一部小說,是福克納構筑約克納帕塔法縣世系小說中的一部。它以本德倫家女主人艾迪的死亡為矛盾中心,每一家庭成員的所作所想為依托來推動情節發展,以洞悉小家庭所展露出的悲劇命運來反映20世紀三十年代美國南部窮苦白人沒落的生存狀況和迷惘的道德困境,同時也是鄉土世界傳統價值觀的崩塌和消亡的縮影。將其與《喧嘩與騷動》結合起來閱讀,會有更為深沉的關于那一時代家庭悲劇的理解,康普森與本德倫一家的家庭崩潰之源是相似的。
(二)流浪漢冒險小說。同時,該小說也是一本流浪漢冒險小說,跟古希臘傳統冒險題材作品《奧德賽》不同,它不是一個人的英雄苦難故事,而是本德侖一家的近乎堂吉訶德式的冒險悲劇。男主人安斯履行其妻的諾言,死后將她葬于故土。原本四十多英里的路程,卻空降暴雨,必經之路的橋梁遭洪水沖垮,折返繞道卻依舊如此,被迫從淺灘涉水,淹死了騾子,還差點折了棺材、死了大兒子。其后,因洪水耽誤時日,尸體在進城后發臭,遭到近鄰和路人指責,棺材還險些被燒毀。這是精神和肉體共滅的死亡之旅,家庭成員之間的矛盾在路途中被激化,暴露了本德侖一家在傳統道德觀中分裂自生的流浪漢本質。福克納的主要目的更像是迫使讀者以比書中的人物與行動第一眼看上去所要求的或值得的更高一層、更有普遍意義的角度來讀這本小說,來理解本德侖一家及其歷險。它使我們逐漸領會,在某種意義上,它是關于人類忍受能力的一個原始的寓言,是整個人類經驗的一幅悲喜劇式的圖景。因此它不僅僅是講述本德侖一家的苦難歷程,它更是整個人類冒險史的縮影。
(三)反諷寓言體小說。該小說還是一本反諷寓言體小說,全書假托本德侖一家的荒誕離奇的個體以及所經歷的環境為據,因采用第一人稱的敘述視角,每個人都具有相對典型和真實的個性特征,例如反復強調自我的艾迪是虛無的代名詞,反復言說出汗會死言辭的安斯是懶惰和自私的代名詞。除此之外,小說中也采用了環境中的意象物來讓作者參與解讀。例如在小說出現的“水”的意象,水沖毀了送葬之路的橋梁,還傷了卡什的腿,后來成功涉水,寓意著對本德侖一家的懲罰和凈化;而“火”的意象出現在小說行將尾聲之際,大火差點燒毀了棺材,達爾因此被抓捕,因而其寓意著懲罰;但在經歷了大火之后,棺材被營救了出來,最終順利安葬,它也寓意著希望。除此之外,在小說第九章節以安斯為第一人稱視角所言說的“路”也是值得深思的。在安斯眼里,路成了人化的對象,“路躺在那兒,正對著我家門口,來來往往的厄運都不會找不著門的”,而人反倒成了物化的對象,“可上帝本意是讓人住下不動的,就像一棵樹或是一株玉米那樣”,在安斯看來家里所有的厄運都是因為路帶來的。可事實上,是本德侖一家自我切斷了與外界的交流,同時家庭內部也存在溝通障礙,各懷鬼胎,這預示著后文送葬之路的艱辛磨難。但小說結尾卻又以喜劇式的結局收場,千瘡百孔的一家人最終團聚,暗示著歷經磨難后重燃了某種新的生存希望,路也是一種復活的寓意標志。最具反諷的是被送進瘋人院的達爾,他是集理性和浪漫于一身的悲劇主義者的寓意象征。
(四)宗教小說。全書正文處共直接引用了《圣經》共八處,在第八章節鄰居塔爾為第一人稱敘述視角聽聞安斯的“賞賜的是耶和華”一語,這句話語出《圣經·舊約·約伯記》:“約伯便起來,撕裂外袍,剃了頭,伏在地上下拜,說:‘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歸回。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此處是引用約伯的話來自我安慰或安慰死者的親人。而這句話卻語出自安斯,能夠理解在他心里死亡是一種精神升華和肉體解脫,他對死是無所畏懼的,戲謔地道出安斯對于生存現狀的壓抑和苦悶,體現出他生不如死的精神狀態。除此之外,小說故事從“有罪——懲罰——凈化——救贖”這一基督猶太受難的原型情節展開。正如前文所闡述,本德侖一家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心計,個人私欲膨脹泛濫,可以說履行諾言即艾迪的遺愿是他們良心與道德最后的遮羞布,其小說的開頭正好是基督罪行即將審判家庭成員之時,女主人艾迪的死亡使家庭每個成員的私有欲望達到頂峰,而送葬之路正是悔罪之路,水與火的洗禮使他們回歸人性的正途。但最終這一復活正途是以一部分人的犧牲作為代價的,卡什斷腿、達爾被送進瘋人院、杜薇·德爾墮胎未果,而享受復活是一家之主的安斯本人,唯有他實現了自己的心愿,安上了假牙,迎娶了新老婆。但看似大團圓喜劇的結尾卻暗藏危機,小家庭重歸和諧但歷史的大環境依舊如此,安斯可能是一個潛在的惡魔。
本德侖一家是典型的《圣經》二律背反藝術表現手法的文學對象,福克納甚贊于《圣經·舊約》的二元對立的藝術表現手法,他曾說過:“對于我們來說,《新約》里充滿了各種觀念,我幾乎無法理解它。而《舊約》卻充滿了豐富的人物,他們既是完美、標準的英雄,也是像今天每個人一樣的惡棍。我喜歡讀《舊約》, 因為它具有豐富的人物,而不是抽象的觀念。”作者正是采用了這樣的二元對立描寫出了本德侖一家,因而《我彌留之際》中的主要人物形象豐滿而不單一的,在對立矛盾中體現“自我”。小說也充滿了眾多圣經原型式的象征意象,例如水與火、路、魚、馬、禿鷹、棺材,這些意象在《圣經》中有對應的原型,使小說彌漫著豐厚的宗教色彩,前文闡釋過一些意象,這里便不做過多贅述。
(五)復仇心理小說。從復仇心理入手,小說復仇的核心焦點在于本德侖一家成員之間扭曲而淡漠的感情,彼此間缺乏共識,其感情的肆意揮灑往往只有兩種方式呈現出來:一是自我心理內在排解;二是無法忍受之后的極端行徑。其中矛盾核心是愛情,主要是艾迪和安斯之間痛苦而麻木的愛。全書僅有一個章節,即第四十章是以艾迪為第一人稱敘述視角展開的,“也是這個時候我才懂得詞語是沒用的,就在人們說話想要表達的當兒那詞意就不對勁了。”艾迪用詞語這一符號表明了詞語能指和所指的斷裂的一面,意指的不可靠性導致了感情的虛偽和荒誕,揭示了她對感受過世間之物的厭惡,與存在的一切顯得格格不入,因而陷入了人生虛無的困境中。在與安斯生了第二個孩子后,她的受騙心理更甚,激發了她報復安斯的想法,“我的報復是讓他永遠不知道我在報復他。達爾出生后我要安斯答應,我死后把我運回杰弗遜安葬……”小說主線情節送葬之路就是在此基礎之上的蓄意復仇。達爾與珠爾之間的矛盾糾葛即也是父母愛情沖突的側面寫照,在第四十八章節里面達爾執著于追問“珠爾,你娘是一匹馬,可你爹是誰呢?”兄弟間的這一矛盾是同母異父、母親偏愛珠爾的愛情矛盾的仇恨的產物。尤其是小說的結尾是耐人尋味的,在安葬妻子前一向麻木不仁、面如死灰的安斯卻畫風突轉,在艾迪死后,他的人物形象在小說最后一章節的最后一段有所描寫,“一下子顯得高了一頭,頭似乎也昂了起來,既羞愧又神氣。”這樣的出乎意料的情節構造,卻也是情理之中的,這也許是安斯對于不忠艾迪的報復。他將以全新的復活的面貌結束過去地跟艾迪在一起的虛無困境,開始屬于他自己的新生活,而孩子們儼然已成為愛情的犧牲品。另一組比較淺顯的矛盾在于達爾和杜薇·德爾之間。達爾知曉其妹妹戀愛丑聞,彼此心照不宣,杜薇·德爾一直心生忌憚。等到達爾即將被抓之時,她內心恐懼的情感爆發了,“像只野貓似的猛撲向他……對著達爾又抓又扯”,由此可見,兄妹之間的沖突主要是妹妹與拉夫的地下戀情所產生的。
三、結語
本文從福克納的《我彌留之際》中挖掘出五大表現主題,重點結合接受美學中讀者接受這一方面論述了《我彌留之際》所含有的多元的主題意蘊,但顯然這是片面的,正所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隨著文學理論的發展和人類時代的演進,可能還會有更潛在和現實意義的主題等待讀者參與其中去挖掘,只要站在相對合理的閱讀視域走進作品,將自己的心靈與作者的心靈相對照,福克納筆下的本德侖一家可能會有更深刻的文化主題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