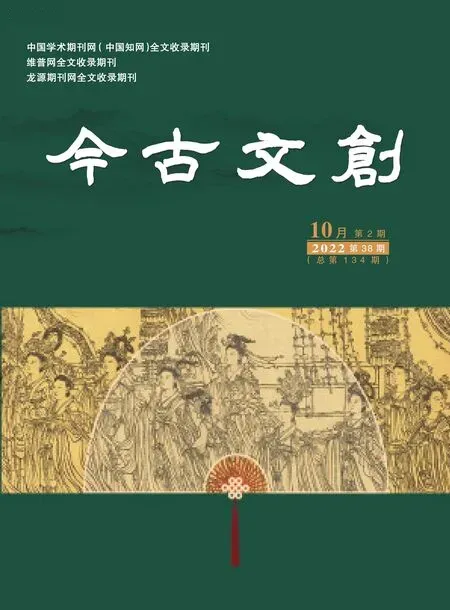論《莊子》思想在陶淵明田園詩創作中的表現
◎孫百慧
(西安石油大學 陜西 西安 710300)
作為道家學派的代表性著作之一,《莊子》承載著道家重要的思想內核——道為本源、清靜無為、齊物思辨等,其深刻地影響著后世的文學創作與士人的文化心態。從玄言詩、山水詩等的詩歌創作到儒道互補、歸隱不仕的中國古典文人獨特的精神支柱與信念,《莊子》所體現的道家思想已滲入了中國古典文化的內核,成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重要文化信仰。
所謂“田園詩”,可以將其定義為以關涉了農業生產生活的自然田園風物為主要題材的中國古典詩歌。廣義地講,凡是描繪村野風光且表現農業性社會生活的作品,基本都可以包括在內。田園詩與山水詩之別就在于詩中有無出現人與農事生產等因素——若僅表現了自然山水之景,而沒有農事、生產、人與自然相依存的痕跡,那就是有別于田園詩的山水詩。如謝靈運的主描摹的山水題材詩歌創作。
在一眾中國古典文學創作的題材流派中,清新自然、淡雅田娟又韻味悠長的田園詩可謂有著與《莊子》思想深厚而不可分割的關系——通過探究二者之聯系,將更好地理解《莊子》思想的文化影響和具體實踐,與田園詩所蘊含的以道家思想為核心的精神本質與文化內核。本文將以東晉陶淵明的田園詩創作為例,從自然樸素的價值追求、得意忘言的審美境界與清靜無為的人生理想三個角度,淺論《莊子》思想在陶淵明田園詩創作中的表現。
一、自然樸素之價值追求
《莊子》重視自然本身的規律及自然中的天然性,并以自然作為人與人類社會的標尺。其《內篇·應帝王》中“游心于淡,合氣于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指出了順遂自然天性之理,莫要人為干預,便可獲得政治上的成功。《外篇·天道》中“靜而圣,動而王,無為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則道出了《莊子》對自然及其屬性的崇敬與欣賞,且透露出了其對自然的效法與對無為的崇尚。《外篇·山木》中“既雕既琢,復歸于樸”是對天然純樸之本質的追求。《外篇·知北游》中“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即天地自然為道德、政治與美的最終標準。諸如此類,《莊子》明確指出了要恪守自然本性,而非進行人為的刻意追求,方能獲得至高、至善、至美的價值取向。這體現出了《莊子》對自然本性的追求,對人為強爭的排斥,與在自然中尋找道并獲得哲思的思維方式。
同樣,對自然樸素的追求可謂一直鑲嵌在陶淵明的田園詩中。正如沈德潛在《說詩晬語》中的評說:“陶詩合下自然,不可及處,在真在厚。”其“真”“厚”體現在田園中的一草一木,雞鳴,狗吠,白云,清澗等等普通而清新的自然風物,這些都是詩人贊美和沉醉的對象。陶淵明田園詩歌的質性自然已自成一境。自然境界,是陶淵明田園詩歌創作的精神特質和核心。其詩中體現出的自然境界既代表著陶淵明的哲學思想,又體現了他的實踐理性精神和審美價值取向。陶淵明在《歸園田居其一》“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與《飲酒》“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等詩句中明確地表達了對官場世俗生活即“無為”之反面——迎合世俗、追名逐利的厭倦。“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戴月荷鋤歸”“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則以田園生活景象、事務與環境直接而明確地表達了對于“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的由清凈、簡樸、純凈人心所構成的飽含天然本性、樸素美好的田園生活的贊美與熱愛。
由此可知,《莊子》與陶淵明田園詩中對自然樸素的追求是有相同甚至承繼之處的。題材上,在陶淵明的田園詩創作中,自然田園作為寫作題材當然是無有爭議的表現對象,其在意象上通過對農園自然風物的表現來表達作者的情感與“真意”正是對《莊子》以天地悟道的思維方式的繼承與情思表達的發展;思想上,將自然視為官場勞役等世俗生活之對立面,而求其天然、清凈、簡樸且使人能夠脫離樊籠、任真自得的陶之田園詩,則是更深入地,對《莊子》崇敬自然本性而無為思想的延伸。
二、得意忘言之審美境界
《莊子》在言意之辨及其關系上,注意到了二者之別,并得出了言不盡意、得意忘言的結論。《外篇·秋水》中“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其以言論者為“粗”,以意致者為“精”,可見《莊子》對于致意的區別與重視。《內篇·齊物論》中“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與《雜篇·外物》中“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均表達了但求言中之意而忽視言語表達(言之輕),且重視捕捉文字背后隱含著的深層抽象思緒或情感(意之重)的言意觀。概言之,《莊子》認為,領悟到了“意”便已超越了“言”。
陶淵明的田園詩中便流露出了同《莊子》得意忘言相一致的審美情趣。陶詩以恬淡獨成一家,其“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等質樸的寫作在東晉末劉宋初的文壇上既不同于時人好談玄說理、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玄言詩,又不同于前朝西晉時陸機潘岳等人造就的繁縟華美的太康之風。陶詩的自然樸素之語自帶靈氣,其看似未經雕琢的語言、簡單地對自然風物的呈現已是把陶之田園理想與審美旨趣盡數傾瀉于紙上。且《飲酒》中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更是明晰地表達出了身居偏遠之地而直致“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的自然之趣并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等清閑之樂的“真意”,而不在乎言甚至可以“忘言”的思維模式。這大概同陶淵明青年時所做《五柳先生傳》中所言的“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的觀念是一致的。此外,詩歌言辭之外的境界的開創也可謂是得意而超脫于言的表現。如《飲酒》十四中“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質樸地寫出了醉酒后不知物我之分、飄然如物我合一的超脫境界。
《莊子》中輕視言、重視意甚至道的審美與思維模式在陶淵明的田園詩中便具體表現為了直至自然田園質樸平淡的美意、樂趣之“道”或境界,而在創作時不求言語之華麗雕飾的言意表達。同時,其“意”上求自然樸素之美與“言”的簡單質樸得以相輔相成、互為表里、渾然一體。這可謂是《莊子》的言意思想在后世詩歌創作上的一次成功實踐。
三、清靜無為之人生理想
《莊子》與《老子》在思想上的相通之處離不開政治上的無為思想。與“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相似,《莊子》厭惡功名利祿與人為強爭,提倡清心寡欲。許由在拒絕堯禪位之邀時所言“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即是出自個人的利益考量,認為擁有天下之權位于我無用、非我所需的對于世俗所求的功利的厭棄。連叔同肩吾論及藐姑射之山上的神人時,說“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以虛構人物之口表達了《莊子》對掌天下之權而需辛苦經營的嫌惡,等等。從個人的角度來講,《莊子》如同儒家思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反面——從不視努力追求權力榮耀為正途,而是主張內心清凈,追求養生。從國家集體的角度講,其主張施政應順應自然本性,以“無為”為“為”而使得天下大治。
陶淵明的田園詩中明確地表現出了對努力追求仕途榮華的“世俗之路”的厭惡,且這種對浮躁人世的無意與對自然田園的向往是一致的——這正是其個人在理想追求上清靜無為的體現。正如其《歸去來兮辭》中所言,“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富貴非吾愿,帝鄉不可期”直言其本愿并非富貴通達。其詩歌中的“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開篇表白世俗所求如“塵網”,對自己而言不過是渴望掙脫的束縛罷了,并發出“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之類解脫的豁然之快。即便陶淵明在其《雜詩》中也表達過早年曾有儒家入仕的傳統思想:“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但縱觀其多數田園詩中的思想傾向、人生實踐與《歸去來兮辭》序中所言——即便家中貧窘至極,也終在一番猶豫之后選擇放棄烏紗帽而歸去自然,即便固窮守拙也不愿在官場“以心為形役”。這種對積極入仕、追求官場權力與榮耀名利的絕對厭惡著實是《莊子》所主張的內心清凈,但求無為的具體表現——實際上物我合一的渾然之感已經在陶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中表現出來了。
《莊子》的清靜無為在陶淵明的田園詩中具體地表現為對案牘勞形的厭惡,與對自然田園之清凈儉樸生活的向往。陶淵明在自己的田園詩歌創作中所融入的道家無為思想、所展現的田園風物意象,使得后世的讀者均能從這些詩句中感受到其悠然的人生觀與自得的理想境界。這對《莊子》而言是其無為思想的具體創作落實與生動的發展,對古典文學創作而言可謂是開辟了一個新的、使田園自然與歸隱哲思渾然一體的表現領域。從此,以山水田園言自己內心清凈與隱逸之志的創作風潮便流行開來。
四、余論與結語
作為田園詩的開創者,東晉時代的陶淵明廣泛地受到了儒釋道三家思想的共同影響。他有著明顯的歸隱清閑的本意,卻也飽受固窮背后的孤獨帶來的煎熬與對長久以來自身背離世俗追求的隱約懷疑——這使他常有如《雜詩》中“欲言無與和,揮杯勸孤影”的苦悶卻又無以訴說之痛、“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的美好歲月已逝后的失落,或“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的發自內心的厚重的悲涼。這些看似與《莊子》但求清靜無為與樸素自然的思想相悖,但我們若換一個角度審視,這也是陶淵明順應天性的自然表現——這些隱晦的苦悶與縱觀人生的沉重思考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其個人本性的抒發,這使得后人在其田園詩中更多地讀到了一個復雜而又真實的“人”,而非矯飾下執著于背離主流甚至標新立異的一個符號。陶淵明對自然田園的眷戀與不舍,既非出于追求虛浮的隱居高名,也非出于彰顯世俗的忠義道德,而是為了單純地保全一份質性自然的“真我”,這也就要求了陶淵明在自然生活中要坦誠面對自己的內心需求與情感,抒發自我的各種色彩的真情。而只有在回歸自然的過程中,才能得到心靈的凈化,并達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因而在更深層的意義上,陶淵明多樣而真摯的田園詩創作正是對《莊子》順應天然本性的實踐。
后世的田園山水詩創作基本也有陶詩中《莊子》道家思想的身影。但隨著更多元的思想的傳入、發展與彼此的溝通融合,后世田園山水詩已不再如陶詩般直接而鮮明地體現《莊子》的道家思想了——這在某種程度上,也體現著文學本身對《莊子》道家思想的選擇性發展,選取其部分思想元素并結合該時代的特點而使之重煥生機。盛唐著名的山水田園詩派代表詩人王維,如其《終南別業》“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固然關注自然天性與清凈內心,但其在深層文化性內涵上更多地涉及佛家禪意;孟浩然《宿建德江》中“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同樣是從山水自然中汲取天地本性中蘊含的闊大,但全詩除了在審美意境上擁有唐詩“興象玲瓏”之特點帶來的普遍的得意忘言之余緒外,道家思想、《莊子》思維已遠不及東晉陶詩濃厚了。隨著文學自身的發展、思想的多元化與時代的變革,《莊子》思想對后世詩歌創作的影響當然是因時而異的,甚至其在被吸收利用與改造后已趨于隱蔽。但后世田園山水詩歌的優秀創作,若沒有先秦《莊子》道家思想本質性的影響與注入,大概不會如我們今天所見般璀璨動人。由此看來,《莊子》思想對于后世以陶淵明田園詩為代表的山水田園題材詩歌的創作,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思想價值與文化影響。
綜上所述,《莊子》的道家思想對后世陶淵明的田園詩歌創作具有重要的影響,且《莊子》思想在陶詩中的表現也是多方面的。在當時可謂獨樹一幟的陶淵明的田園詩歌,其巨大魅力離不開其作品中蘊含著的受莊學影響而造就的樸素的價值追求與清雅的審美情趣。在《莊子》自然清純,言外有意,避于世俗喧囂而求清凈簡樸等審美與價值追求的影響下,陶淵明的田園詩擁有著超越時空的巨大藝術魅力與思想價值。同時,在先秦一眾探討政治與倫理的諸子學說中,《莊子》那獨特的基于社會人生的思考與樸素的人文關懷,也在后世的田園詩歌選擇性吸收與改造的創作過程中,得以重煥生機,并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前行。
注釋:
①???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上)》,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215頁,第74頁,第18頁,第18頁。
②③④?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中)》,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337頁,第506頁,第563頁,第418頁。
⑤(清)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六十四。
⑥⑦⑧⑨⑩?????????????????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76頁,第247頁,第85頁,第76頁,第247頁,第130頁,第85頁,第76頁,第247頁,第247頁,第247頁,第502頁,第268頁,第460頁,第461頁,第76頁,第76頁,第347頁,第247頁,第342頁,第338頁,第342頁。
?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下)》,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725頁。
?(魏)王弼注,樓宇烈校:《老子道德經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48頁。
??蕭滌非等:《唐詩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版,第158頁,第1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