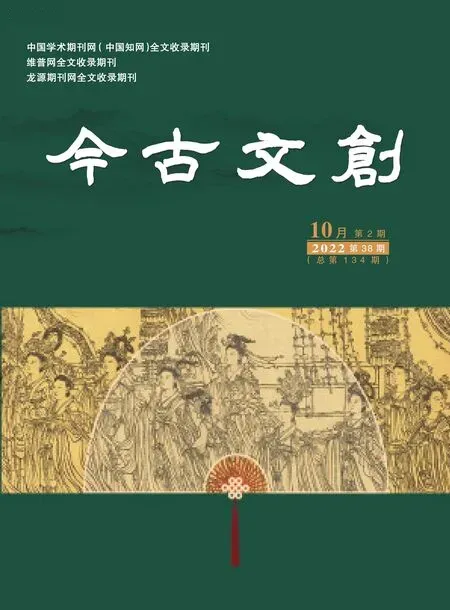余華《現實一種》的荒誕性解讀
◎韋靜璇
(廣西師范大學 廣西 桂林 541006)
“荒誕”本是西語中形容音樂的一個術語,指音樂節奏中不和諧、不協調的音調。隨著荒誕派戲劇的誕生,“荒誕”便確立了與傳統美學對立的基調。從字面理解,“荒誕”是怪異、奇特之意。從美學角度理解,荒誕是丑的次級審美范疇之一,它是對無內容的形式的拼貼呈現。荒誕藝術以不合理的、荒謬的、可笑的形式,表現不同社會背景下人們不知所措、迷茫的生存狀態。
余華的《現實一種》是作者嘗試進行荒誕寫作的試驗性作品,具有濃重的荒誕色彩。作者以多種不同的寫法與冷峻的筆調向讀者講述了一個家庭的悲劇故事。小說的荒誕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思想內容的荒誕性
在中華傳統文化的背景下,人們遵從并且倡導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關系。正如《禮記》所云:“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無論是貧窮或富貴,“家和萬事興”都是中華民族固有的文化認同。而《現實一種》以夸張、扭曲、變形的荒誕方式,顛覆了人們對家庭關系的傳統認知。讀者看到的是親人失和、情感虛空的家庭圖景。
一家人圍坐吃飯這件事情本身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之中,本就帶有強烈的團圓色彩,象征著家庭和睦。而在小說中,山崗一家人呈現的畫面是各人自顧自地吃飯,彼此之間沒有更多情感上的交流。祖母向眾人訴說自己的身體情況,沒有人回應;她接著說“我知道那是骨頭正一根一根斷了。”最后她提到“我胃里好像在長出青苔來。”然而,對于她的幾次發言,家里其他人都沒有任何明顯的回應。兒子的注意力轉向窗外的雨水,兒媳婦則“似乎沒有聽到母親的話,因為她們臉上的神色像泥土一樣。”單向地交流讓這家人的對話顯得無趣、重復。每個人都自說
自話,沒有向身邊的人給予多一點關心,每個人都不能在親人那里得到情感的宣泄和滿足。
而祖孫之間的互動,同樣顛覆了人們的日常經驗。皮皮偷吃了祖母的咸菜,祖母便眼淚汪汪地抱怨起來。祖母形象不是理想中的疼愛兒孫,而是為了一點咸菜哭了起來,這一情節設置本就與人們的傳統印象背道而馳。當早飯結束,一家人外出上班,他們一起走出胡同:“兄弟兩人走在一起,像是互不相識一樣。”山峰得知孩子死亡后的第一反應是責怪妻子以及兇狠的家暴行為;其次,山崗山峰兩位父親為了自己的孩子兄弟相殘,山崗更是殘忍地折磨山峰,讓親弟弟活活地笑死。在這個故事文本中,意外的喪子事件給親人之間帶來了無法磨滅的傷痛。即便面對自己的骨肉至親,仇恨并不會因此受到理性和道德的壓抑、緩和或者淡化,非理性的荒誕行為沖擊了一切理智思考。
種種象征團圓、和諧的家庭日常活動,在余華的筆下分崩離析,顛覆了人們對傳統家庭互動的固有認知,一種難以置信的荒誕感覺油然而生。小說的閱讀經驗與人們生活的現實經驗之間形成了巨大反差,凸顯小說內在的荒誕特性。
二、暴力行為的荒誕性
著名學者約翰·加爾頓將“暴力”解釋為“任何使人無法在肉體或思想上實現他自身的潛力的限制。”他認為“暴力”可以分為“直接暴力”“結構性暴力”“文化暴力”三類。其中直接性的暴力便是人們通常所認為肉體上的擊打、攻擊、武力打壓等。而“暴力”是余華小說偏愛的敘事主題之一,《現實一種》讓讀者面對的便是一種直接的、顯性的暴力行為,是直接由施暴者將赤裸裸的暴力行為掰開來、揉碎了展現在讀者面前。
如果說幼童的暴力行為是無意識的、無心之失,是深藏在人類靈魂深處的本能使然;那么成年人之間的暴力傷害行為,則是本我沖破超我和道德約束、沖破地獄之門的殺戮行為。在成人世界,“暴力”行為往往更復雜更殘忍。施暴者往往能夠理性地、周密地制定復仇計劃。在理性計劃背后卻是難以抑制的非理性暴力本能。兩位為孩子復仇的父親,一個代表的是瞬間的、殘忍的暴力行為;而另一個則是步步為營、隱忍不發最終將暴力演繹到極致。
山峰許諾,只要皮皮舔了嬰兒的血跡,這樁家庭悲劇便能結束。但他卻在妻子出現的剎那,被理智壓抑住的仇恨與暴力本能受到刺激之后,沖破理性的牢籠一發不可收拾——“山崗這時看到弟媳傷痕累累地出現了,她嘴里叫著‘咬死你’撲向了皮皮。”與此同時,山峰飛起一腳踢進了皮皮的胯里。可以說山峰被仇恨激起的這一腳,不僅擊碎這個家庭重歸于好的最后希望,也將山崗心中的理性防線徹底粉碎。
而山崗選擇了所有殺人方式中最為殘忍、折磨的一種——笑刑。他以一只小狗為作案工具,在山峰的腳底涂上肉沫,讓小狗去舔他的腳底,直到山峰窒息而亡。這種活生生把人笑死的方式,其殘忍程度比起瘋狂的拳打腳踢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壓抑在人性中深處、最根本的“惡”被刺激、釋放,非理性的暴力沖動在仇恨的刺激下,甚至能沖散手足親情。本我的非理性沖動沖破現實道義、法律規范的阻攔,最終造成無法挽回的后果。作者通過山崗極致的、理性徹底消失的復仇行為,對人性本身提出質疑,以荒誕的藝術表現方式反思人性。
三、寫作方式的荒誕性
余華為使自己的作品能充分表現出真實的世界,致力嘗試多種寫作方式,正如他自己所說:“現在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明白自己為何寫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更加接近真實。”
首先,在《現實一種》中作者有意減少人物的情緒變化、面部表情的相關描寫。
“任何人物都沒在任何一點上表現出人們在正常情況下與這種恐怖事件相關時所可能有的情感。相反,貫穿整個故事的情感表達,如微笑、哭泣、大笑,明確地表現為與我們所期待的內部動機分離。”比如老太太走到門口時,被幼兒的血跡嚇到,隨即躲回了臥室。而當山峰向老太太尋問兒子被誰抱出門時,她只是不斷抱怨自己看到血了。老太太對兒子的問話置若罔聞,卻希望通過不斷強調自己的見聞而引起別人對她的關注。面對小孫子突然的死亡,身為祖母的她不為所動,沒有表現出正常情況下該有的悲傷、難過等情緒,相反她一直處在只關注個人生存遭遇的狀態中。
無獨有偶,山峰因遭受小狗舔舐腳底而發出的“笑”則是建立在痛苦、悲憤的真實情緒之上。按常理而言,人們通常是遇到真正快樂的事情才會有大笑的情緒,而山峰的“笑”卻是被迫和痛苦的。山峰表現出的大笑情緒與真實的內心所想形成強烈反差。借用古代文論的批評話語,這樣的處理方式便是達到了“樂景襯哀情,一倍增其哀樂”的藝術效果。小說中人物的行為動作與讀者慣常的期待視野之間有了巨大的反差、隔閡,在審美效果上給予讀者震撼與沖擊。
其次,在描寫人物如何面對突發的死亡事件,作者選擇了顛覆日常生活經驗的處理方式。
當山峰的妻子發現孩子躺在地上,她首先看到兒子頭部的血跡,覺得并不真實;又回到臥室翻開抽屜;最后目光停留在空蕩的搖籃上。這一視覺畫面才刺激母親意識到孩子已經躺在屋外。妻子一系列的視覺活動表現了當時她的行為與意識之間存在延遲。視覺活動在這里被作者“用于凸顯對象/事件與對它的感知之間的差距的”時間的延宕將人物的行為與意識分離了。
如果說母親的反應是在極度刺激下、拒絕接受現實的失智行為,那么父親的悲痛反應則是接受悲劇事實之后極度的冷靜與克制。從山崗的角度分析,作為父親他想盡力彌補皮皮的過錯,忍受山峰的辱罵打擊,并提出經濟賠償。直到山崗忍痛割舍兒子,山峰的承諾又給了他一線希望。而山峰臨時變卦,突如其來的報復將山崗心中升起的希望再次破滅。山崗的讓步還是無法避免山峰向皮皮復仇,無法避免一家人陷入復仇的循環悲劇之中。山崗已經做好會失去兒子的心理準備,目睹兒子的死亡時,他表現得出奇地冷靜。山崗“心想沒辦法了”既是表明自己的兒子還是沒辦法救下來,也暗示著這家人最終還是走向冤冤相報、互相殘殺的末路,除了暴力相向之外“沒有別的辦法了”。這兩種不同的情緒反應都是極端化的,都是經過藝術處理之后的夸張表現。作者通過顛覆讀者的日常經驗,增大了讀者閱讀的難度和時延,令讀者與文中人物一道體會喪子的悲痛,在看似風平浪靜的表面之下,是無法言喻的極端痛苦。
再次,作者運用重復的敘事策略達到加深主題的目的。
縱觀整部小說,《現實一種》是由一次又一次的暴力死亡事件構成的連環悲劇。故事脈絡可總結為皮皮摔死堂弟——山峰向皮皮復仇——山崗折磨山峰——山崗被槍決。最終,以山崗的尸體被醫生肢解結束。每一次死亡都是暴力行為的升級,一次比一次殘忍,一次比一次荒謬。通過不斷重復相同的事件,從而達到加深主題的效果。“這種敘述的循環把一個充斥著血腥、暴力與死亡的悲劇世界展現得淋漓盡致。”重復荒誕事件背后的深意是作者對理性與非理性是否不可協調的質疑與思考,人與人之間的沖突是否終將走向不可挽回的局面,荒誕現實是否不可避免。
除敘事結構的重復之外,出現在不同人物身上的相同動作也是一種重復,達到前后呼應的反諷效果。其中最突出的是三次“舔”的動作。
第一次“舔”出現在山峰要求皮皮舔自己兒子血跡的場面。而山崗的妻子請求代替皮皮。從山崗的視角看妻子的動作是貪婪的。“妻子一走近那攤血就俯下身去舔了,妻子的模樣十分貪婪。”第二次“舔”的動作出現在皮皮身上,皮皮只是一個孩童,他對血沒有具體的認知,他將血跡與鮮甜的果漿聯系起來,血的滋味讓他感到可口。而最后一次“舔”的動作是由小狗完成的。不同的是前兩個人物是懺悔者的角色,而這只狗則是報仇殺人的工具。狗作為低等動物,不具備人思考的技能。對于狗(動物)而言,它并不是出于任何復仇的心理,只是面對食物的本能動作。一個相同的動作,由人到動物重復出現,模糊了人性與動物性的界限。狗嗜血是動物本能,而當這一動作發生在人類身上時,也暗示著人的動物性本能。將人類和動物放在同一個層面,是對人性的再一次叩問。用反諷的方式強調了人性與動物性之間界限的缺失。
《現實一種》中有很多對話重復的場景,在文本形式和內容上都實現了陌生化的藝術效果。比如祖母在早餐時間,向家人三次提到自己聽到骨頭斷掉的聲音。皮皮醒來后感到全身發冷,便向母親說了。隨后皮皮出現在父親面前連續三次說“我冷”。祖母在回答山峰誰把自己兒子抱走時,幾次回答都是在說自己看到血了。皮皮的重復暗示了他意識到自己做錯事后內心的不安與恐懼;而祖母不斷重復個人的遭遇表明了她處在一個只關注自己而漠視他人的狀態里。無意義、無邏輯對話的重復,凸顯了家庭成員缺少情感上的有效溝通。
作者運用多種不同的寫作方法,為讀者展示了一個支離破碎的家庭,用非理性的荒誕形式向讀者描繪一個脫離理性的故事內容。在這個文本里理性已經不復存在。
四、荒誕性寫作風格的成因分析
余華對“荒誕”風格的偏愛與個人特殊的童年記憶、青年經歷有關。
由于家庭的緣故,余華童年是在醫院中度過的。過早的接觸死亡、尸體等血腥畫面,讓他對鮮血的恐懼漸漸地轉變為冷靜、麻木甚至癡迷。童年時期留下的醫院記憶,成了他日后寫作展開奇異、怪誕想象的素材。而曾經是牙醫的職業經歷,也讓余華接觸了更多流血、惡心的畫面,久而久之便對鮮血場面習以為常。
而余華個人的青年經歷為他的寫作增添了與眾不同的色彩。人與人之間出現信任危機的社會現實,讓作者對現實世界產生了失望與幻滅之感。由此,受個人成長經歷與社會大環境兩方面影響,余華都習慣了爭執、打斗等殘忍場面。因而有論者指出:“余華所做的‘局部修改’便是從他個人童年經歷出發,以一個孩童的視角,青年的口吻,輔以荒誕的手法完成了對往昔種種遭遇的重述。”
正因如此余華在寫作中對這些暴力事件表現出與常人不同的反應,能不帶個人感情地描寫各種荒誕的場面;而作者有意減少自身對作品的介入更有利于讀者直面文本,延長了讀者的閱讀時間,并增加了閱讀難度。
五、結語
《現實一種》中的人物行為都與中華傳統美德相距甚遠,表現出來的人性惡遠遠超過了人性善,以藝術化的方式表現了特殊時期人與人之間信任崩塌、人性扭曲的真實現象。以“荒誕的真實體現真實的荒誕”,其目的正是引起人們的反思,其背后的用意是引發人們對秩序、理性、和諧生活地追去。即便遠離了那動蕩歷史之后,余華的作品對當下的社會生活依然有警示的意義。
暴力與非暴力、理性與非理性之間是否真的不可調和,人的非理性行為是否荒謬不可遏制。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文學作品呈現的荒誕世界應該是人們現實生活中盡力避免的一個極端世界。荒誕美學一方面讓人體驗極致的爽感,而它的反面也指向了虛無。“荒誕的美學意義只有在以肯定性的審美活動作為參照背景時才是可能的。”
注釋:
①余華:《現實一種》,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頁,第2頁,第3頁,第19頁,第18頁。
②黎保榮:《中國現代文學“暴力敘事”現象的概念、綜述與意義》,《肇慶學院學報》2015年第3期,第1-8頁。
③吳義勤:《余華研究資料》,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5頁,第124頁,第127頁。
④李光輝:《論余華〈現實一種〉中的重復敘述》,《安徽文學》2012年第1期,第60-61頁。
⑤張露尹:《論余華小說中的荒誕書寫》,西南民族大學2021年碩士論文,第15頁。
⑥田燁:《余華〈現實一種〉的荒誕特征》,《文學教育(上)》2019年第1期,第28-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