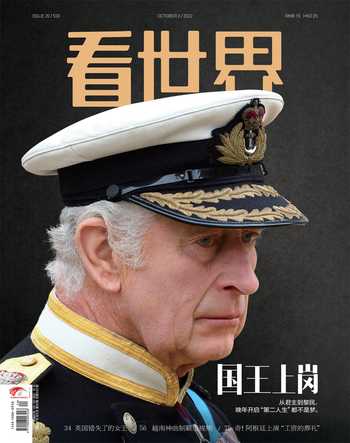弗里吉亞:行走神話歷史間
樓學

歷史悠久的弗里吉亞
從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出發,旅行者們大多一路向南,去卡帕多奇亞乘坐熱氣球,或是在科尼亞欣賞一場托缽僧的旋轉舞。
然而,鮮少有人將視線投向首都的西面—在安納托利亞的這片高原上,埋藏著無數王國的輝煌過往。我想要尋找的古國叫弗里吉亞,其都城戈爾迪翁至今仍沉睡在安卡拉省的西陲。
戈爾迪翁的預言
從安卡拉始發的巴士途經小城波拉特勒,幾個下車的當地人很快消失在周圍的街巷中,這座幾無游客的城市顯得暮氣沉沉。手頭的旅行指南完全沒有提及弗里吉亞的舊都戈爾迪翁,電子地圖上也沒有收錄前往遺址的公共交通方式。詢問過幾個不會說英語的當地人后,我想這次旅行恐怕要以失敗告終了。
直到我最后一次鼓起勇氣詢問當地人,才終于柳暗花明。他帶領我到達一家超市的門口,告知我前往戈爾迪翁的巴士就從這里發車,但此刻的停車場里不見巴士的蹤影。對語言不通的我來說,哪怕無從確認,也只能選擇相信。
在經歷漫長的等待后,去往戈爾迪翁的小巴終于姍姍來遲。我估計了一下往返需要的時間,似乎已經來不及趕上晚間離開的長途巴士,但已經付出了如此漫長的等待,我不甘心就此放棄。小巴司機和我說,戈爾迪翁有一個憲兵隊,如果實在回不來,不妨去那問問有沒有順風車。盡管聽得一頭霧水,但想著只要能去,就一定能回來,抱著這種沒來由的信心,我還是向戈爾迪翁進發了。

戈爾迪翁博物館內的陶器
甚至也有歷史學者認為,正是弗里吉亞人終結了赫梯帝國的漫長統治。
古都戈爾迪翁,坐落在Sakarya河旁的一處高地,曾是這片高原上最重要的城市。在古典時代口耳相傳的一個神諭中,“戈爾迪翁之結”(GordianKnot)是一個外部沒有繩頭的神秘繩結,據說能夠解開此結的人將會統治亞細亞。亞歷山大大帝東征之時,以一劍劈開繩結,他稱王的預言也果真應驗。
如今的戈爾迪翁擁有一座博物館、一片城市遺址和近百座大型陵墓。在博物館的介紹中,戈爾迪翁被稱作近東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我一度懷疑這是館方的自吹自擂。眼下這座門庭冷落的博物館,完全無法與人潮洶涌的特洛伊、以弗所或內姆魯特相比。
弗里吉亞的確有引以為傲的資本。公元前12世紀,偉大的赫梯帝國轟然倒下,其主要的政治舞臺安納托利亞半島,一時成為了政治的真空。許多小國從中涌現,弗里吉亞就是其中最醒目的那個。甚至也有歷史學者認為,正是弗里吉亞人終結了赫梯帝國的漫長統治。這支來自巴爾干半島的民族,陸續遷入小亞細亞,并在這里建起以自己民族命名的王國。
但戈爾迪翁似乎被悠久的歷史湮沒了。在整個博物館中,除了我以外,只有兩名本地游客,他倆嬉鬧著在展品前拍照留影,笑聲從古老的陶器和馬賽克壁畫的縫隙中傳來。迎面相遇時,他們請我幫忙拍一張合影,轉身離去時,我看到他們的衣服上印著“Jandarma”,正是土耳其語的“憲兵”。
神話照耀的米達斯
在弗里吉亞的歷代國王中,最著名的一定是米達斯。他的陵墓就坐落在博物館的對面。
這座圓形的巨墳尺度驚人,直徑達到300米,殘高仍有53米,是土耳其規模最大的古墓之一,在平坦的高原上頗為醒目。博物館的周圍共散落著近百處墓葬,不免令人想起中國的關中或邙山。

戈爾迪翁博物館內的壁畫
米達斯的陵墓可以入內參觀,其中還完好保留著公元前8世紀的棺槨,那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木質結構之一。
在希臘神話中,米達斯是最常出場的弗里吉亞國王。相傳他曾經為一場音樂比賽做裁判,將勝利判給了森林之神,落敗的太陽神阿波羅惱羞成怒,將米達斯的耳朵變成了驢耳,使這位國王不得不戴著弗里吉亞風格的無邊便帽遮丑。這頂帽尖彎曲的圓錐形帽子,在希臘—羅馬的文化體系中逐漸演化為“東方”的象征。希臘神話中許多非希臘的角色常常戴著弗里吉亞帽,來標示他們的“東方”屬性,比如特洛伊戰爭中的帕里斯王子。
在羅馬時期,那些釋放的異族奴隸也被要求戴上弗里吉亞帽。這頂帽子在成為身份羞辱的同時,也衍生出“自由身份”的象征。近代以來,這頂源自弗里吉亞的帽子被重新解讀,在法國大革命中,紅色的弗里吉亞帽被引申為真正的“自由”。那幅著名的油畫《自由引導人民》,畫面中央的自由女神就戴著一頂弗里吉亞帽。而中國旅行者最熟悉的形象,則一定來自動畫片藍精靈,它的帽子同樣代表著自由精神。
關于米達斯的另一個神話,則與地理環境有關。米達斯曾拯救過酒神的老師,作為回報,酒神滿足了米達斯的愿望,使其擁有點石成金的超能力。這項傳奇的技能在英文中就被稱為“Midastouch”,但對當事人而言,這卻意外成為了災難—他觸碰的食物變成了黃金,他擁抱的女兒成為了一座金像。他最終只有把手指放進了一條河中,才解除了這項超能力—這條帕克托勒斯河,是歷史上有名的金礦產地,成為弗里吉亞的后繼者及對手—呂底亞的經濟命脈。
自由與囚禁、財富與禁錮,看似截然相反的命題,卻意外在米達斯的神話中統一。當這座大墓被發掘時,許多人都依據其龐大的規模、相近的測年,將其歸屬附會到了米達斯身上,但從嚴謹的考古學出發,這并非沒有爭議。只是人們在狹長的甬道中行走時,還是希望自己走向的是那個長著驢耳朵、戴著圓尖帽、點石成金的國王吧。
遺址驚魂記
從博物館和王陵區出來,我要去都城戈爾迪翁的遺址區,還有大約兩公里,只能徒步前往。走了沒多遠,迎面而來的一輛轎車停在我的身邊,剛剛在博物館里偶遇的兩位憲兵向我招手,問我是不是要去遺址,可以搭我一段“順風車”。這顯然并不順路,他們已經看完遺址區,正要返回。

在戈爾迪翁眺望國王米達斯陵
不過在邀請之下,我自然也樂得少走這許多路,慶幸自己的舉手之勞也換來他人的善意。很快就到了遺址區,他倆問我大概要看多長時間,我說:“或許40分鐘吧,可以把背包留在你們的車上嗎?”
“當然可以。”他們滿口答應。可當我剛下車關上車門,敞開的車窗內傳來兩個人的大笑聲,汽車立刻啟動了,馬上消失在遺址區的土路盡頭。
我本以為他們會在遺址區門口等我參觀出來,但猛然驚醒之后,我甚至來不及記下完整的車牌號,更無從判斷這是否是一個騙局。電腦、行李、現金都在背包中,好在最重要的護照、相機和幾張信用卡留在隨身攜帶的小包里—我安慰自己,哪怕成為了這樣的“孤家寡人”,也一定是可以回國的。
希臘神話中許多非希臘的角色常常戴著弗里吉亞帽,來標示他們的“東方”屬性。
我幾乎硬著頭皮走進了遺址區,相機仍舊拍個不停,但早已沒有心思看任何介紹了,滿心都盤算著要怎么報警,要如何描述我的窘況。爬到遺址的制高點上,不遠處的米達斯陵如同一座小型的火山,下面無邊的草原上是許多羊群,這樣的美景反倒激發我又生發出許多悔恨之情,要是時間撥回到在米達斯陵徒步的時候,我一定不會這么武斷大意了!
直到大腦空空地逛完一圈遺址區出來,時間只過去20多分鐘—直到后來重新整理照片時,才發現這座遺址似乎從未在我的記憶里存在過。在接下來十余分鐘的等待里,我越來越絕望、越來越生自己的氣。一直謹慎的我,怎么會犯如此愚蠢的錯誤呢?
我眺望著那條土路的盡頭,期盼著滾滾塵煙再次升騰起來,終于感受到了“望穿秋水”是什么滋味。
不過,這一次我太幸運了,后來的這一幕比所有古跡都令我印象深刻—隱隱的馬達聲傳來了,我看見他們的小車從主路上拐了下來,尾氣和塵土仿佛騰起的云霧般,然后是敞開的車窗里傳來的音樂聲和大笑聲。
“走吧,我們回波拉特勒。”
我笑著和他們打招呼,仿佛剛才一切的恐慌、悔恨、憤懣都未曾發生。
特約編輯姜雯jw@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