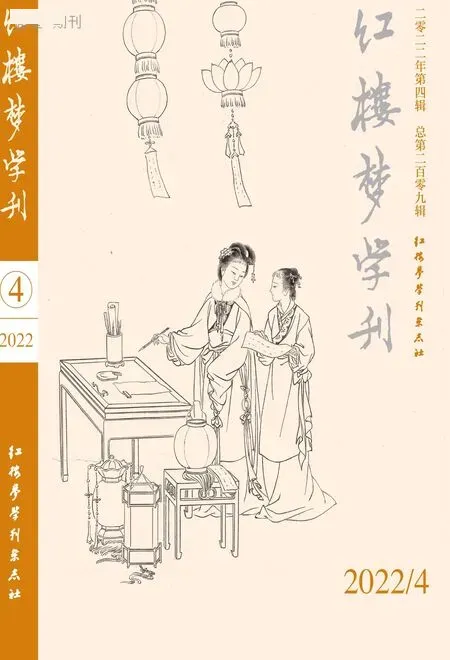董康與己卯本及陶洙
沈治鈞
內(nèi)容提要:關(guān)于乾隆己卯本《脂硯齋重評(píng)石頭記》民國(guó)遞藏史,一粟《紅樓夢(mèng)書(shū)錄》稱(chēng)“董康舊藏,后歸陶洙”。此語(yǔ)源自陶洙親口,跟董康或陶洙有過(guò)密切接觸的紅學(xué)家及藏書(shū)家,對(duì)此均無(wú)異議,甚至明確表示認(rèn)可或贊同該說(shuō),證實(shí)該說(shuō)可靠。董康購(gòu)藏己卯本是在1935年末至1936年初,后者可能性更大。爾后,它主要由陶洙負(fù)責(zé)保管。這是因?yàn)槎斩私徽x甚篤,董又洞曉“心如耽于紅學(xué)”。陶洙“影抄”功夫極精深,幾可亂真。己卯本補(bǔ)抄部分、北師大藏本與庚辰本筆跡局部相似,甚不足為奇。己卯本與庚辰本均為古籍文獻(xiàn),真實(shí)可信,絕非贗品。董康死于1948年5月4日,臨終前將己卯本正式饋贈(zèng)給陶洙。
乾隆己卯本《脂硯齋重評(píng)石頭記》原藏主,現(xiàn)知一是武裕庵,二是董康,三是陶洙。此抄本殘存四十一回又兩個(gè)半回,今藏國(guó)家圖書(shū)館與國(guó)家博物館。所謂己卯本現(xiàn)代原藏主董康與陶洙,專(zhuān)指國(guó)圖藏本部分。
茲將相關(guān)情況扼要梳理一番,主要考察董康與己卯本及陶洙的切實(shí)關(guān)系。核心為三點(diǎn):董康究竟是否己卯本原藏主?董康何時(shí)購(gòu)得己卯本?董康為何將己卯本傳給陶洙?另涉董康與陶洙各自的家世、生平、履歷及交游情形。
一、己卯本首位民國(guó)原藏主董康
董康(1867—1948)原名受金,字授經(jīng),別作授金、綬金、綬經(jīng)、受經(jīng)、壽金、壽京,號(hào)誦芬室主人,江蘇武進(jìn)人。光緒庚寅進(jìn)士,刑部主事、大理院推丞、法律館纂修,又留學(xué)東京帝國(guó)大學(xué),歸國(guó)任大理院長(zhǎng)、司法總長(zhǎng)、財(cái)政總長(zhǎng),先后執(zhí)教?hào)|吳大學(xué)、上海法科大學(xué)、北京大學(xué),戰(zhàn)時(shí)出任偽華北政府委員、議政委常務(wù)委員、司法委委員長(zhǎng)、最高法院院長(zhǎng),戰(zhàn)后瘐斃宅中。工書(shū),嗜藏弆,有《中國(guó)法制小史》《書(shū)舶庸譚》《曲海總目提要》《課花庵詞》等。祖本仁,父介貴、母唐韞貞,兄祺,妻遲氏,子鐵寶(妻梅鎮(zhèn)安)、申寶(妻壽曼麗),孫輩邁、愷、晨,重孫凌峰,重外孫女張宇白,友沈家本、王克敏、王賡、趙尊岳、郭則沄、史良,同榜文廷式、夏曾佑、俞明震、史履晉。參看董秉清編《宜興胥井武進(jìn)前街董氏合修家乘》(民國(guó)丁卯刊本)及董粹曾編《常州青果巷董氏族譜》(2019年家族自印本)。內(nèi)中民國(guó)家乘,董康曾參與纂修,可信度甚高。
董本仁曾官山東章丘典史,轉(zhuǎn)文登令,調(diào)觀城知縣,保升知州。榮成孫葆田《職官志·國(guó)朝宦跡》:“董本仁,字季容,江蘇常州人,咸豐十一年權(quán)觀城事。時(shí)城為賊陷,道路不通,從直隸大名入境,招集難民筑城為保。賊至,即以民夫偕團(tuán)勇守御,人心亦漸固。越歲,城工竣,而教匪方熾,邑中恃以無(wú)恐。”(《山東通志》卷七六)江陰繆荃孫著錄:“《秋瘦閣詞》一卷,傳鈔稿本。武進(jìn)閨秀唐韞貞撰。韞貞字佩衡,唐與忠女,適同邑董介貴。存詞一卷。壽京比部,其次子也。”(《藝風(fēng)堂藏書(shū)續(xù)記》卷七)此中“壽京比部”即董康。唐韞貞(1843—1893)字佩蘅(繆著訛),其《秋瘦閣詞》有光緒朝徐乃昌刊本,見(jiàn)《小檀欒室匯刻閨秀詞》第五集;另有《雨窗詞》一卷,見(jiàn)《詞綜補(bǔ)遺》卷五三引《常州詞錄》。董介貴(?—1868)早逝,邑庠生,幾無(wú)建樹(shù)。董祺(1862—1921)原名受祺,字綬紫,光緒己丑舉人,山東候補(bǔ)道、庫(kù)倫鎮(zhèn)撫使公署司法科長(zhǎng),因公殉職于外蒙古事變,大總統(tǒng)通令嘉獎(jiǎng)議恤,附祀忠烈祠,有《吮雪詞》《鑄鐵詞》《碧云詞》。董鐵寶(1916—1968)與董申寶(1917—2010)昆仲及梅鎮(zhèn)安(1918—2014)俱為著名科學(xué)家,愛(ài)國(guó)人士,成就卓越,譽(yù)望隆崇。
董康一門(mén)書(shū)香,詩(shī)禮傳家,漸趨西化,在近現(xiàn)代史上有一定代表性。關(guān)于董康即《脂硯齋重評(píng)石頭記》己卯本民國(guó)原藏主,首先見(jiàn)諸周紹良與朱南銑筆下。一粟《紅樓夢(mèng)書(shū)錄》:“此本董康舊藏,后歸陶洙,現(xiàn)歸文化部。”該書(shū)錄初版于1958年4月中,彼時(shí)陶洙尚健在。周紹良與陶洙私交甚篤,所言當(dāng)源自陶洙,可信度極大。除非陶撒謊,但撒謊的動(dòng)機(jī)何在?委實(shí)無(wú)從想象。2001年10月18日,周紹良對(duì)特意前來(lái)叩詢(xún)的曹立波說(shuō):“陶心如抄過(guò)庚辰本。當(dāng)時(shí)庚辰本十兩金子,己卯本一兩金子。陶心如抄的庚辰本,用己卯本改過(guò)。我和他來(lái)往很多的時(shí)候,是在1952到1953年,那時(shí)他自己抄的書(shū)(指庚辰本)已經(jīng)賣(mài)掉了。我認(rèn)識(shí)陶心如時(shí),他的書(shū)已經(jīng)不全了。……我和他來(lái)往是來(lái)往,但不是搞《紅樓夢(mèng)》。他抄書(shū)的本領(lǐng)很大,抄過(guò)很多善本書(shū)。我們請(qǐng)他補(bǔ)書(shū),給他點(diǎn)兒錢(qián),他很窮。”周紹良與陶洙曾有交往,一度過(guò)從頻密,此毫無(wú)疑齪。故而《紅樓夢(mèng)書(shū)錄》所謂“此本董康舊藏,后歸陶洙”之說(shuō)相當(dāng)可靠。
對(duì)此,同樣跟陶洙有過(guò)親密接觸的俞平伯毫無(wú)異議。1953年10月30日,俞平伯已大體完成《脂硯齋紅樓夢(mèng)輯評(píng)》的整理工作,撰寫(xiě)引言說(shuō):己卯本、甲辰本、戚序本“在我手邊”,至于甲戌本“我現(xiàn)在有的是近人將那本脂評(píng)過(guò)錄在己卯本上的”,而庚辰本“藏西郊北京大學(xué),我有它的照片”。一般估計(jì),俞平伯當(dāng)時(shí)掌握的己卯本原件及攝影藍(lán)曬庚辰本均來(lái)自陶洙,起碼己卯本原件只能如此。翌年3月30日,俞平伯在香港推出《紅樓夢(mèng)隨筆》第二十八則:“曹雪芹的畫(huà)像,前聞陶憶園先生說(shuō),在上海曾見(jiàn)兩種:……據(jù)陶先生云兩幀相貌相同,自屬可信。”此證俞平伯與陶洙確有私交。俞平伯親手使用過(guò)己卯原本,倘對(duì)《紅樓夢(mèng)書(shū)錄》“此本董康舊藏”之說(shuō)持異議,定會(huì)明言。豈止此也,跟陶洙有過(guò)密切接觸的汪吉麟、朱啟鈐、夏仁虎、商衍鎏、沈鈞儒、陳半丁、陳叔通、黃炎培、陳垣、葉恭綽、沈尹默、鄭家相、尹文、于照、汪旭初、胡佩衡、曹家麒、彭醇士、溥儒、陳之佛、汪慎生、張伯駒、黃君璧、徐操、馬晉、惠均、金啟靜、鄭曼青、金南萱、傅抱石、趙萬(wàn)里、何瀛、吳恩裕、周汝昌等,均及見(jiàn)《紅樓夢(mèng)書(shū)錄》付梓乃至增訂,也都對(duì)“此本董康舊藏”說(shuō)無(wú)異議。其中趙萬(wàn)里是王國(guó)維弟子,寫(xiě)過(guò)《紅樓夢(mèng)》版本方面的專(zhuān)題論文,身為北京圖書(shū)館善本特藏部主任,己卯本入藏北圖為善本,必經(jīng)趙手;吳恩裕專(zhuān)門(mén)研究過(guò)己卯本的散失部分,結(jié)論為此本源出怡親王府;周汝昌使用過(guò)影印己卯本,著述連篇累牘,屢屢提及陶洙。他們仨若不贊同“此本董康舊藏”說(shuō),絕不會(huì)長(zhǎng)期保持緘默。事實(shí)上,吳恩裕和周汝昌都重復(fù)過(guò)《紅樓夢(mèng)書(shū)錄》中的相關(guān)說(shuō)法,表示認(rèn)可并贊同“此本董康舊藏,后歸陶洙”之說(shuō),見(jiàn)《己卯本〈石頭記〉散失部分的發(fā)現(xiàn)及其意義》(載《光明日?qǐng)?bào)》1975年3月24日)及《紅樓夢(mèng)辭典》(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己卯本條。這從另一個(gè)角度證明“此本董康舊藏”說(shuō)當(dāng)屬可信。
聊起紅學(xué)家,莫忘掉顧頡剛。看看他的日記。民國(guó)丙戌1946年9月17日星期二(農(nóng)歷八月廿二日):
到蜀腴赴宴。九時(shí)許到溫知書(shū)店,為寫(xiě)劉季洪信。今晚同席:徐森玉、陶心如、鄭振鐸、陳乃乾、謝剛主、顧起潛、徐伯郊(文坰)、孫實(shí)君(以上客)、孫助廉(主)。
內(nèi)中“蜀腴”是一家川菜館,位于滬上廣西北路。陶洙既出席晚宴,則大家都是他的熟人。徐森玉詳下。鄭振鐸(1898—1958)是陽(yáng)歷10月17日遇難的,那時(shí)《紅樓夢(mèng)書(shū)錄》已初版半年多。陳乾(1896—1971)字乃乾,浙江海寧人,上海通志館及文獻(xiàn)委員會(huì)編纂;謝國(guó)楨(1901—1982)字剛主,河南安陽(yáng)人,中央大學(xué)教授;顧廷龍(1904—1998)字起潛,蘇州人,上海合眾圖書(shū)館總干事;徐文坰(1913—2002)字伯郊,浙江吳興人,上海銀行經(jīng)理;孫誠(chéng)溫(1902—1966)字實(shí)君,河北冀縣人,修文堂主人;孫誠(chéng)儉(1905—1970)字助廉,誠(chéng)溫之弟,溫知書(shū)店老板。同席者全是古籍文獻(xiàn)方面的第一流行家,顧頡剛與鄭振鐸還是紅學(xué)家,他們均及見(jiàn)《紅樓夢(mèng)書(shū)錄》初版,完全不可能誰(shuí)都不曉得“此本董康舊藏,后歸陶洙”之說(shuō),卻俱無(wú)異議。此時(shí)董康系獄,陶洙竟?fàn)枱o(wú)恙。
認(rèn)識(shí)陶洙的學(xué)者無(wú)異議,認(rèn)識(shí)董康的學(xué)者也無(wú)異議,例如徐鴻寶(1881—1971),字森玉,浙江吳興人,曾任京師圖書(shū)館采訪部主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zhǎng)、國(guó)務(wù)院文史館副館長(zhǎng)、上海博物館館長(zhǎng);再如張宗祥(1882—1965),字閬聲,號(hào)冷僧,浙江海寧人,曾任京師圖書(shū)館主任、浙江教育廳長(zhǎng)、浙江文史館副館長(zhǎng),有《鐵如意館隨筆》。我在《徐星署小考》中已揭示,董康、徐星署、徐鴻寶、張宗祥等同為傅增湘祭書(shū)會(huì)中人,彼此甚熟稔。徐張兩公也都是陶洙的老朋友,陶張二氏同為秦淮畸社社員。徐鴻寶和張宗祥均及見(jiàn)《紅樓夢(mèng)書(shū)錄》初版,若知“此本董康舊藏”說(shuō)欠妥,也會(huì)出面講話的。當(dāng)然,他倆都不是紅學(xué)家,對(duì)于“此本董康舊藏”說(shuō)或許沒(méi)感覺(jué),無(wú)所謂,或許皆不能肯定該說(shuō)正確與否,只得乖乖閉嘴。另有一種可能,隔行如隔山,他倆壓根便不曉得該說(shuō)存在。
那么,現(xiàn)請(qǐng)出一位大牌紅學(xué)家。胡適是讀過(guò)《紅樓夢(mèng)書(shū)錄》初版的,他也跟董康有過(guò)來(lái)往。且看1960年5月30日的胡適日記:
史語(yǔ)所新得的大陸出版物四十多種,其中有一部分的紙張很粗糙。有一粟編的《紅樓夢(mèng)書(shū)錄》一冊(cè)。《例言》中說(shuō):……所記“新月書(shū)店”一段,荒謬之至!我抄存此段,作大陸的學(xué)人作風(fēng)。此錄又記:“過(guò)錄乾隆己卯(1759)冬月脂硯齋四閱評(píng)本石頭記……此本董康舊藏,后歸陶洙,現(xiàn)歸文化部。”又記:……一粟不知是誰(shuí)?
胡適橫眉立目(甚罕覯),痛詆關(guān)于“新月書(shū)店”那一段,毫不客氣,卻對(duì)“此本董康舊藏”說(shuō)未駁一辭。翌年5月18日他為影印甲戌本寫(xiě)跋時(shí)說(shuō):“近年武進(jìn)陶洙家又出來(lái)了一部‘乾隆己卯(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冬月脂硯齋四閱評(píng)本石頭記’,止殘存三十八回:……這個(gè)己卯本我沒(méi)有見(jiàn)過(guò)。俞平伯的《脂硯齋紅樓夢(mèng)輯評(píng)》說(shuō),己卯本三十八回,其中二十九回是有脂評(píng)的。據(jù)說(shuō)此本原是董康的藏書(shū),后來(lái)歸陶洙。”胡適還寫(xiě)道:“后來(lái)因?yàn)槲倚麄髁酥幖仔绫救绾沃匾瑦?ài)收小說(shuō)雜書(shū)的董康、王克敏、陶湘諸位先生方才注意到向來(lái)沒(méi)人注意的《脂硯齋重評(píng)石頭記》一類(lèi)的鈔本。”顯而易見(jiàn),胡適對(duì)《紅樓夢(mèng)書(shū)錄》“此本董康舊藏,后歸陶洙”是認(rèn)可的,甚至是贊同的。他特地談到董康、王克敏、陶湘及陶洙受他影響,皆緣己卯本與庚辰本。
胡適比董康小二十四歲,兩人卻是老相識(shí)、忘年交,有胡適日記為證:
(1922年7月1日)與董授經(jīng)談?wù)巍4巳耸且粋€(gè)好人,但不配處于這個(gè)時(shí)代這個(gè)地位。我很可憐他。他問(wèn)我對(duì)時(shí)局的意見(jiàn),我勸他主張“臨時(shí)政府”之說(shuō),可以解決一切糾紛,可以消除南方的意見(jiàn)。他頗贊成此議,并說(shuō)“黃陂是可以做到這個(gè)辦法的”。(眉注:“他自己說(shuō),司法界中人才,他還知道;財(cái)政人才,竟是‘兩眼墨漆黑’!”)
(1933年6月14日)哲生舉一例更好。……我提了三個(gè)名字給哲生,請(qǐng)他添聘為憲法顧問(wèn):林行規(guī)、董康、孟森。
(1934年9月9日)晚飯席上與董康、傅增湘、章鈺、孟森諸老輩談,甚感覺(jué)此輩人都是在過(guò)去世界里生活。章式之(鈺)已七十歲,精神極好。
董康、傅增湘、章鈺都是藏園祭書(shū)會(huì)中人,醉心舊笈。孟森(1869—1938)字莼孫,號(hào)心史,江蘇武進(jìn)人,清史專(zhuān)家,北大教授。如果這幾位老前輩縱談古籍庋藏鐫刻之類(lèi)話題,胡適定會(huì)覺(jué)得索然無(wú)味,并暗自發(fā)噱。盡管如此,他還是喜歡敷衍周旋。董康《書(shū)舶庸譚》將付剞劂,胡適1930年6月28日晚間欣然命筆作序,贊揚(yáng)說(shuō):“董先生是近幾十年來(lái)搜羅民間文學(xué)最有功的人,他在這四卷書(shū)里記錄了許多在日本流傳的舊本小說(shuō),使將來(lái)研究中國(guó)文學(xué)史的人因此知道史料的所在。”末署“十九、六、廿八夜”。董康與胡適彼此熟悉、欣賞、默契到一定程度,方有此序。因此,胡適認(rèn)可《紅樓夢(mèng)書(shū)錄》“此本董康舊藏”才顯得特別有意義。新紅學(xué)宗師必定是信息交匯點(diǎn),胡適一人常可代表學(xué)界態(tài)度。同時(shí)理應(yīng)承認(rèn)“此本董康舊藏”說(shuō),證項(xiàng)略嫌孤單(多為默證),須繼續(xù)探索。
對(duì)于《紅樓夢(mèng)書(shū)錄》此說(shuō),學(xué)界普遍采納。首篇專(zhuān)題論文的作者陳仲竾便說(shuō):“此本舊為董康所藏,后歸陶洙。……此本一向?yàn)槎⑻斩宜讲兀瑑H其故交幾個(gè)人曾據(jù)以傳鈔,此外寓目者很少。解放后,此本歸于國(guó)家,移交北京圖書(shū)館。”陳仲竾(約1910—?)一名仲箎,湖北廣水人,供職北京圖書(shū)館展覽部,有《中國(guó)營(yíng)造圖案史概述》。陳仲竾與陶洙相識(shí),二人曾同為中國(guó)營(yíng)造學(xué)社社員。
迄今所知,除董康及陶洙外,最早閱讀并使用己卯原本的紅學(xué)家是俞平伯,隨后是王佩璋、陳仲竾。至于鄭振鐸、趙萬(wàn)里,詳情俟考。后面還會(huì)提到鄧之誠(chéng)、王克敏、傅增湘、徐星署等為己卯本寓目者,他們都不算紅學(xué)家。
二、董康何時(shí)購(gòu)得己卯本
胡適說(shuō)“這個(gè)己卯本我沒(méi)有見(jiàn)過(guò)”令話題轉(zhuǎn)向,促使我們追問(wèn):董康何時(shí)購(gòu)得己卯本?倘若較早,譬如1930年前后,胡適便有機(jī)會(huì)獲悉并讀到它。此以董胡交誼為前提。胡適既沒(méi)見(jiàn)過(guò)己卯本,表明此本到董康手里是有點(diǎn)晚的,即在1933年1月22日胡適讀罷庚辰本之后,又在1948年5月4日董康病故之前。關(guān)于董康卒年,以往眾說(shuō)紛紜,莫衷一是,均欠精準(zhǔn)。今已明白確定,歸功于紅學(xué)界外。清華大學(xué)法學(xué)院教授陳新宇《董康與近代中國(guó)的法律改革》附注:
北京市檔案館所藏檔案詳細(xì)地記載了董康逝世的情況。檔案號(hào)J184-002-04391,北平市警察局檔案,1948年5月4日義字64號(hào)第二分駐所“呈為地院會(huì)同檢驗(yàn)董康因病身死由”:一據(jù)第七段警長(zhǎng)程啟新報(bào)稱(chēng),本日十四時(shí)馀有地方法院檢察官任維屏、檢驗(yàn)員傅長(zhǎng)林等到段會(huì)同聲稱(chēng),因管界西磚胡同甲九號(hào)住戶(hù)董康,系漢奸案保外醫(yī)治,現(xiàn)因病故,前往查驗(yàn)等語(yǔ)。二當(dāng)由該長(zhǎng)帶同戶(hù)警鍾毓杰隨同前往,由該員等驗(yàn)得該尸委系無(wú)傷因病身死,當(dāng)發(fā)給抬埋執(zhí)照一紙走去,除先行電報(bào)分局外,理合附同知會(huì)一紙一并呈報(bào)。巡官×××呈。
董康終年81周歲,也算高壽了。西磚胡同位于北平市南城原宣武區(qū)中部,在宣南坊范圍內(nèi),明朝叫磚兒胡同,北起廣安門(mén)內(nèi)大街,南接七井胡同,西交醋章、培育兩胡同及法源寺前后街,東會(huì)蓮花、永慶兩胡同。檢察官任維屏是河北涿縣人,北京法大學(xué)校畢業(yè),京兆司法協(xié)進(jìn)會(huì)干事,1946年冬曾參與勘驗(yàn)白云觀道士火燒住持致死案,在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有一定知名度。董康身負(fù)漢奸罪案,不是個(gè)普通人,所以他的死頗受重視。以往傳言瘐斃獄中,訛誤,應(yīng)予糾正。
關(guān)于董康何時(shí)購(gòu)得己卯本,梅節(jié)進(jìn)行過(guò)認(rèn)真探討。他說(shuō):“此本解放前原為陶洙(心如)所藏,而陶洙自云得自董康。”隨即逐步展開(kāi)辯證,結(jié)論是:“我們大致可以肯定,董康購(gòu)得己卯本的時(shí)間,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其間梅文有個(gè)較為嚴(yán)重的歷史誤會(huì),即認(rèn)為胡適撰寫(xiě)于1933年1月22日的《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píng)石頭記〉鈔本》沒(méi)有立刻發(fā)表,董康也便不能及時(shí)讀到它。而實(shí)際上,胡適此文不僅立刻發(fā)表了,并且還是提前發(fā)表的。因《國(guó)學(xué)季刊》延遲出版,胡適此文居然是刊登在去年(1932)第3卷第4期上的。換言之,寫(xiě)成于今年,發(fā)表在去年,彷佛時(shí)光倒流。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梅文這一小小瑕疵,使得上引結(jié)論的準(zhǔn)確性大可懷疑。前邊講過(guò),胡適與董康有交情,董康購(gòu)得己卯本不會(huì)太早(例如“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否則胡適就有機(jī)會(huì)寓目了。現(xiàn)將梅文的證據(jù)粗粗檢視一番,引文凡出自梅文者不再另行注釋?zhuān)瑑H點(diǎn)明舛訛。
董康《書(shū)舶庸譚》卷一下,民國(guó)丙寅1927年1月24日:“吾國(guó)胡適之好搜輯小說(shuō)家文字,余亦頗欲撰小說(shuō)家列傳,苦于所見(jiàn)不多。”又卷四下,民國(guó)丁卯1927年4月27日:
(綺云)生平酷嗜《石頭記》,先慈嘗語(yǔ)之云:幼時(shí)見(jiàn)是書(shū)原本,林薛夭亡,榮寧衰替,寶玉糟糠之配實(shí)維湘云,此回目中所以有“因麒麟伏白首雙星”也。綺云欲本此意,改竄最后數(shù)十回,名《三婦艷》,以補(bǔ)其憾,惜削稿未就也。
內(nèi)中“先慈”即唐韞貞。時(shí)董康年逾花甲,其母已逝三十四載。此證董康喜歡《紅樓夢(mèng)》,他的母親和妻妾(綺云即綺卿)也都是《紅樓夢(mèng)》愛(ài)好者,這毫無(wú)問(wèn)題。關(guān)于“寶玉糟糠之配實(shí)維湘云”傳說(shuō)甚夥,與此處題旨無(wú)涉,從略。這時(shí)候胡適還沒(méi)從胡星垣手里買(mǎi)到甲戌本(尚差數(shù)月),董康也不像買(mǎi)到己卯本的樣子,否則自應(yīng)順帶提及。馮其庸《論己卯本——影印〈脂硯齋重評(píng)石頭記〉己卯本序》亦持此議。
董康《書(shū)舶庸譚》卷七,民國(guó)甲戌1934年1月13日:
狩野與余評(píng)論《水滸》及《紅樓》人物。余于《水滸》之宋公明無(wú)所可否,金圣嘆極端攻擊,未為至論。然第一流當(dāng)屬林教頭。若《紅樓》一書(shū),評(píng)者皆揚(yáng)林抑薛,且指薛為柔奸。余嘗閱脂研齋主人第四次定本,注中言林薛屬一人。脂研齋主人即雪芹之號(hào),實(shí)怡紅公子之代名。卷中寫(xiě)薛之美,如天仙化人,令人不忍狎視;寫(xiě)其情,不脫閨娃態(tài)度,純用虛筆出之。設(shè)置二人于此,吾知傾倒寶兒者必多于顰卿也。狩野深韙余言。
內(nèi)中“狩野”指狩野直喜(1868—1947),字子溫,號(hào)君山,別署半農(nóng)人,日本熊本縣人,京都帝國(guó)大學(xué)教授,實(shí)證派漢學(xué)家,工漢詩(shī),有《君山詩(shī)草》及《支那學(xué)文藪》,友內(nèi)藤湖南、桑原騭藏、張?jiān)獫?jì)。狩野之名梅文作“直吉”,形訛。“屬林教頭”梅文作“屬之林教師”。又“脂研齋”一名凡兩見(jiàn),梅文均作“脂硯齋”固然正確,但于董康原文則音訛。
董康說(shuō)“余嘗閱脂研齋主人第四次定本”何意?倘若那就是他所購(gòu)得的己卯本,必當(dāng)明言之,此處語(yǔ)氣顯然不是,而“注中言林薛屬一人”尤堪矚目。脂批:“釵玉名雖兩個(gè),人卻一身,此幻筆也。今書(shū)至三十八回時(shí)已過(guò)三分之一有馀,故寫(xiě)是回,使二人合而為一。請(qǐng)看黛玉逝后寶釵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謬矣。”(庚辰本第四十二回總評(píng))現(xiàn)存己卯本缺此回,無(wú)此批。董康具備充足條件“嘗閱”庚辰本原物。我在《徐星署小考》中揭示,至遲1922年初,董康跟徐星署已打得火熱。他倆同是傅增湘祭書(shū)會(huì)中人。又“脂研齋主人即雪芹之號(hào),實(shí)怡紅公子之代名”顯示,董康的確受到了胡適的直接影響及深刻影響。董康不僅讀過(guò)《考證〈紅樓夢(mèng)〉的新材料》(1928年早春談甲戌本),而且讀過(guò)《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píng)石頭記〉鈔本》。據(jù)此可以肯定,董康借閱過(guò)庚辰原本,此時(shí)(1934年初)他還沒(méi)有購(gòu)得己卯本。
董康《書(shū)舶庸譚》卷八下,民國(guó)乙亥即1935年5月13日:
三時(shí)許,詣文化研究會(huì)訪狩野,并晤倉(cāng)石、吉川。會(huì)中所儲(chǔ)叢書(shū)全部皆由蘭泉讓渡,以故與心如相契尤深。導(dǎo)心如至二階,逐一摩沙。陶氏以聚叢書(shū)鳴于一時(shí),各部精選初印及足本,于藏宋元舊槧外特樹(shù)一幟。歸途至佐佐木書(shū)店,購(gòu)紫式部《源氏物語(yǔ)》一部。此書(shū)紀(jì)宮闈瑣事,儼然吾國(guó)之《紅樓夢(mèng)》,惜文筆為當(dāng)日方言,非深于和學(xué)者,無(wú)從味其神境也。心如耽于紅學(xué),曾見(jiàn)脂硯齋第四次改本,著《脂硯余聞》一篇,始知是書(shū)為雪芹寫(xiě)家門(mén)之榮菀,通行本評(píng)語(yǔ)乃隔靴搔癢耳。
內(nèi)中“倉(cāng)石、吉川”是日本漢學(xué)家倉(cāng)石武四郎(1897—1975)與吉川幸次郎(1904—1980),“蘭泉”“陶氏”是陶湘(1871—1941),號(hào)涉園;“心如”即陶洙。此番是董康第七次東渡扶桑,為時(shí)二十五天,即從1935年4月23日至5月18日,乃應(yīng)彼國(guó)斯文會(huì)邀請(qǐng),參加?xùn)|京孔子圣堂落成典禮。董康偕陶洙同行,委以秘書(shū)職任,可窺親誼之一斑。“紫式部”梅文“式”訛“色”。
董康說(shuō)“心如耽于紅學(xué)”所關(guān)非細(xì),又講陶洙“曾見(jiàn)脂硯齋第四次改本”,這仍不像董康所購(gòu)己卯本,否則加一“余”字作“曾見(jiàn)余脂硯齋……”即可,何等徑捷。陶洙所見(jiàn)應(yīng)即徐星署購(gòu)藏的庚辰本。董康既借閱過(guò)庚辰本,陶洙要讀到它便很容易,遂給董康留下個(gè)“心如耽于紅學(xué)”的強(qiáng)烈印象。可惜《脂硯余聞》已失傳。讀者記清,直至1935年5月13日,董康仍未購(gòu)得己卯本。五天之后的18日星期六,董康、陶洙一行才買(mǎi)舟歸國(guó),購(gòu)得己卯本當(dāng)在此后。按《書(shū)舶庸譚》日期用陽(yáng)歷,無(wú)須換算。
由于時(shí)代不斷進(jìn)步,條件漸漸改善,一些珍稀材料陸陸續(xù)續(xù)披露出來(lái),個(gè)中謎團(tuán)似可迎刃而解。查己卯本上原有陶洙題記若干(舊影印本刪),先引三則:
(1)庚辰本校訖。丙子三月。(第二十回卷末)
(2)此本照庚辰本校訖。廿五年丙子三月。(第三十一回卷首)
(3)三十六回至四十回庚辰本校訖。廿五年丙子三月。(第四十回卷末)
按“廿五年丙子三月”是農(nóng)歷,杏花凋謝的暮春時(shí)節(jié),公元陽(yáng)歷為1936年3月23日至4月20日谷雨,中間插入個(gè)清明節(jié)。該年農(nóng)歷三月為閏月,既然陶洙未寫(xiě)“閏三月”,今只能如上理解。他校己卯本,用的是庚辰本原件還是攝影藍(lán)曬庚辰本?姑且不去管它。這些題記全是寫(xiě)在己卯本上的,那么“廿五年丙子三月”便是董康購(gòu)得己卯本的時(shí)間下限。換言之,董康購(gòu)得己卯本當(dāng)在1935年5月18日至翌年4月20日之間,范圍將近一整年。
董康所藏己卯本共計(jì)三十八回,即第一至二十回、第三十一至四十回、第六十一至七十回(武裕庵抄配第六十四、六十七兩回),另有零星殘缺。假設(shè)陶洙校訖頭二十回是在“丙子三月”初,已知校訖第三十一至四十回猶未出“丙子三月”,可見(jiàn)他大概二十天校十回,平均兩天校一回,速度適中。由此推算,他開(kāi)始校對(duì)的時(shí)間大約是農(nóng)歷正月中下旬(丙子元宵節(jié)前后),陽(yáng)歷則是1936年2月7日前后。董康與陶洙同鄉(xiāng)忘年,交誼匪淺,董康又深諳“心如耽于紅學(xué)”,而持己卯、庚辰兩本互校又是詳盡了解己卯本價(jià)值的必由之路,相對(duì)年輕些的陶洙理當(dāng)出工出力、盡心盡責(zé),故董康必在購(gòu)得己卯本之后,第一時(shí)間出示給陶洙,兩個(gè)本子互校隨即啟動(dòng)。董康與徐星署是老朋友,此前已借閱過(guò)庚辰本,這番再借有何難哉?倘陶洙此際已獲攝影藍(lán)曬庚辰本,那就更方便了,不用擔(dān)心窩工。據(jù)此估量,董康購(gòu)得己卯本的時(shí)間,籠統(tǒng)講是1935年底至1936年初;具體講(即最大可能)是1936年2月初,剛過(guò)農(nóng)歷丙子新年,元宵節(jié)未至。每臨新春,各類(lèi)古董交易都比較頻繁順暢,舊書(shū)店顧客盈門(mén)、生意興隆,苕賈們穿梭往來(lái)、忙忙碌碌。董康此時(shí)收得己卯本,實(shí)不足為奇。除了叫陶洙兩本互校,董康起碼會(huì)讓老朋友徐星署、傅增湘、王克敏、郭則沄等開(kāi)開(kāi)眼。此時(shí)董康和陶洙在哪里?上海還是北平?應(yīng)為北平,因董康已執(zhí)教于北大法律系。二十三年后的1959年冬,己卯本殘卷現(xiàn)身中國(guó)書(shū)店,由中國(guó)歷史博物館的于冠英偕王宏鈞購(gòu)得。據(jù)之判斷,董康購(gòu)得己卯本的具體地點(diǎn),當(dāng)為北平琉璃廠某書(shū)肆。
另有一項(xiàng)旁證,見(jiàn)鄧之誠(chéng)《五石齋文史札記》1936年11月20日(九月廿八日):
小陶來(lái),以《脂硯齋重評(píng)石頭記》見(jiàn)示,大約脂硯即曹雪芹以寶玉自命者。
此“小陶”即陶洙,相對(duì)于他的堂兄陶湘而言。鄧之誠(chéng)(1887—1960)字文如,號(hào)明齋,江蘇江寧人,北大歷史系教授,有《骨董瑣記》和《清詩(shī)紀(jì)事初編》等,時(shí)居北平。
陶洙此來(lái),所持《脂硯齋重評(píng)石頭記》必即己卯本,則前此董康業(yè)已購(gòu)得,料無(wú)疑義。十載后的1946年6月21日(五月廿二日)鄧之誠(chéng)在徐府親睹過(guò)庚辰本原物,又十載后的1956年12月19日(冬月十八日)還回顧過(guò)前事,見(jiàn)鄧氏文史札記(《徐星署小考》已引),鄧均未講陶洙今日所持即庚辰本,陶洙也決不可能拿一套攝影藍(lán)曬庚辰本去向大行家鄧之誠(chéng)顯擺。那樣做純屬丟人現(xiàn)眼。脂硯齋=曹雪芹=賈寶玉,這是胡適、俞平伯、顧頡剛以來(lái)經(jīng)董康到陶洙的一貫認(rèn)知,陶洙所撰《脂硯馀聞》也無(wú)非這類(lèi)見(jiàn)解。既出示己卯本,陶定會(huì)向鄧申明本子來(lái)歷,如董康今年初購(gòu)藏云云。鄧之誠(chéng)關(guān)心紅學(xué),也及見(jiàn)《紅樓夢(mèng)書(shū)錄》初版,能夠知曉“此本董康舊藏,后歸陶洙”等語(yǔ),何況還親見(jiàn)過(guò)己卯、庚辰兩本原物,可謂眼福奇絕,卻未嘗提出任何異議,可證“此本董康舊藏”之說(shuō)確乎無(wú)誤。
陶洙拿己卯本給鄧之誠(chéng)看,似屬自作主張。照理講,董康購(gòu)得己卯本,該應(yīng)首先拿給胡適瞧瞧的,卻竟沒(méi)有,以致胡適二十五年之后嘟噥說(shuō)“這個(gè)己卯本我沒(méi)有見(jiàn)過(guò)”。此中蹊蹺或差池,現(xiàn)無(wú)從參詳。也許董康覺(jué)得該本殘缺過(guò)甚,羞于示人;也許覺(jué)得不必著急,有的是機(jī)會(huì)。孰料翌年(1937年丁丑)爆發(fā)盧溝橋事變,董康與胡適分道揚(yáng)鑣、各謀其是,無(wú)緣面對(duì)面切磋紅學(xué)了。
陶洙不僅親校己卯本,還攜掣此本到處?kù)乓菜普淙舯种恪⒁暼艏何铮疵饪蛇印<?xì)味則不好笑,因該本最終就是落到了陶洙手里,如有神助,恍含天意,其實(shí)順理成章。
三、己卯本第二位民國(guó)原藏主陶洙
陶洙(1878—1959)字心如,一作星如,號(hào)憶園,江蘇武進(jìn)人。前清附生,江蘇巡撫陳夔龍幕客,北洋政府內(nèi)務(wù)部?jī)L事科長(zhǎng)、政事堂禮制館繪圖主任、典禮司司長(zhǎng)及蕪湖關(guān)監(jiān)督,國(guó)民政府時(shí)期賦閑,先后加入秦淮畸社、中國(guó)畫(huà)學(xué)研究會(huì)、古泉學(xué)社、西山畫(huà)社、中國(guó)營(yíng)造學(xué)社、蘇州正社、聊園詞社、蟄園律社,參與校勘《營(yíng)造法式》、編纂《清儒學(xué)案》,戰(zhàn)時(shí)出任偽華北臨時(shí)政府司法委員會(huì)秘書(shū)長(zhǎng)。居北京城南安平胡同,己亥冬歿于寓所。工書(shū)畫(huà),喜藏弆,著述多散佚。祖世贊,父輩錫番、錫祺、恩澤,從兄珙、湘、瑢?zhuān)幼鎮(zhèn)ィ蹲婀狻⒆嬉恪⒆娲唬瑢O女揚(yáng),侄孫宗震,友董康、郭則沄、陳仲竾、闞鐸,徒弟潘素。參看陶珙等《溧陽(yáng)陶氏遷常支譜》(民國(guó)乙亥石印本)及高文晶《陶洙校抄本〈脂硯齋重評(píng)石頭記〉研究》(中央民族大學(xué)2011年春碩士學(xué)位論文)。其幼子陶祖?zhèn)?1934—1992)生前是北京八中校長(zhǎng)。
關(guān)于陶洙生平事跡,紅學(xué)界所知偏少。寧夏圖書(shū)館的白淑春《中國(guó)藏書(shū)家綴補(bǔ)錄》饒富新意,顯有獨(dú)立于紅學(xué)領(lǐng)域的信息渠道,較為特殊,如昧于誕歲卻詳知忌季,甚覺(jué)寶貴,茲迻錄數(shù)段:
陶氏喜藏文玩古籍,鑒賞古泉尤精。其收藏中以畫(huà)譜詩(shī)詞書(shū)籍和古泉拓本最多,尤其注意收集抄本、稿本書(shū);所藏清德宗(愛(ài)新覺(jué)羅·載湉)光緒間傳抄本《永樂(lè)大典》八卷(四冊(cè)),原本早已不傳,賴(lài)此得以保存,極為珍貴,所憾是未按原本行格字?jǐn)?shù)。1959年中華書(shū)局將這四冊(cè)抄本與其他藏本一并影印出版;收藏中還有一百二十回舊抄本《紅樓夢(mèng)》,朱黃批校;所藏古泉拓本尤多。
陶氏擅書(shū)畫(huà),俱臻妙境。常影抄古本時(shí),繪制插圖,畢真畢肖,如非認(rèn)真詳審,幾可亂真。董康影印宋本《周禮疏》時(shí),其中缺葉部分由陶氏據(jù)阮刻《十三經(jīng)注疏》之疏文,摹仿宋刻本字體將缺葉抄配齊全,后又以影印本上版刻印,其抄配部分如無(wú)知底細(xì)者均不能辨,一時(shí)為書(shū)林稱(chēng)頌。
陶氏與董授經(jīng)(康)交誼最厚;熱心代人校刊書(shū)籍,曾代其從兄陶湘(字蘭泉)校刊宋《營(yíng)造法式》,代天津徐世昌刊印《清儒學(xué)案》。陶氏晚年生活緊迫,平生所藏陸續(xù)散出。
內(nèi)中“收藏中還有一百二十回舊抄本《紅樓夢(mèng)》,朱黃批校”聞所未聞,當(dāng)即己卯本之訛傳。這個(gè)說(shuō)法,表明寧圖的白淑春對(duì)紅學(xué)相當(dāng)隔膜。
又“影抄古本”一節(jié)勾起一段往事。倏忽十四載前(2008年夏季)有人在網(wǎng)上拋出激烈指控,稱(chēng)己卯本上陶洙補(bǔ)抄庚辰本文字、燕大庚辰本、北師大藏本,三者局部筆跡高度近似,幾乎毫無(wú)二致,純?nèi)怀龊跻皇郑矢奖窘^對(duì)是假古籍,偽造者即陶洙。非僅如此,全部脂本皆贗品,偽造者都是陶洙。當(dāng)時(shí)有學(xué)者指出陶洙乃“影抄”庚辰本,故字跡相似,惟妙惟肖,卻遭訐斥,詈辭囂囂,聞?wù)吣@詫。同時(shí)《新世紀(jì)周刊》記者許荻曄報(bào)道:“這篇題為《百年紅學(xué)造假第一大案水落石出人贓俱獲》的博客7月21日發(fā)表,截至7月31日,點(diǎn)擊量已近10萬(wàn)。”那么知道該事件的,及今應(yīng)不下百萬(wàn)。事雖歇,筆跡一模一樣屬實(shí),尚欠合理解釋。今讀白著,終獲答案,真相為之大白。陶洙身懷絕技,確乎具備特異本領(lǐng),他的“影抄”功夫果然分外了得,非常人所能想象。盼白淑春披露資料來(lái)源。苕溪漁隱《癡人說(shuō)夢(mèng)》作證,甲戌、己卯、庚辰、楊藏、列藏、蒙府、戚序、南圖、舒序、甲辰、鄭藏本均為珍貴的古籍文獻(xiàn),真實(shí)可信,絕非贗品。
白著說(shuō)“陶氏與董授經(jīng)(康)交誼最厚”亦屬實(shí)情,甄選貶義詞一丘之貉、一路貨色、如蟻附膻、狼狽為奸、彼沆此瀣、臭味相投、同惡互濟(jì)、同流合污……來(lái)形容也可以,他倆確曾失足附逆,背叛國(guó)家民族,大節(jié)有虧。因不惟武進(jìn)同鄉(xiāng),他們兩個(gè)家族還住常州古運(yùn)河北岸同一條青果巷,世代比鄰,姻戚綿延,簡(jiǎn)直親過(guò)一府,所以董康與陶洙一見(jiàn)如故,堪稱(chēng)莫逆。二人相差十一歲,亦師亦友,如兄如弟,從來(lái)知己可忘年。張伯駒《舊僧》:
拋卻袈裟換布袍,隨人茶飯住僧寮。董家版本今何在?長(zhǎng)念先生五柳陶。(寺僧長(zhǎng)修已還俗,仍居寺司雜役,舊在法源寺,隨故老友陶心如先生為董康刻書(shū)。)
陶洙為董康刻書(shū),上引白著已談及,舊時(shí)人所共知。張伯駒是民國(guó)四公子之一,另有袁克定或袁克文。張?jiān)瑑杉揖銥楹幽享?xiàng)城人氏,早已相熟。民初袁世凱要登基稱(chēng)帝,身居內(nèi)務(wù)部典禮司司長(zhǎng)的陶洙忙前忙后一通張羅,諸如設(shè)計(jì)衣冠、敲定禮儀、布置會(huì)場(chǎng)……均須安排妥帖。張伯駒暮齡回憶過(guò)此事,那時(shí)候他便認(rèn)識(shí)了年近不惑的小個(gè)子陶洙,后來(lái)他倆又同是蟄園律社社員,經(jīng)常一起吟詩(shī)作賦猜燈謎,也少不了偶爾聚首欣賞奇書(shū)古畫(huà)。張伯駒最后一任夫人叫潘素(1915—1992),字慧素,蘇州人氏,全國(guó)政協(xié)委員,工山水花鳥(niǎo),代表作《黃葉村著書(shū)圖》,陶洙是她的繪畫(huà)老師之一。董康與陶洙交誼怎樣,張伯駒知情,潘素也知情。對(duì)《紅樓夢(mèng)書(shū)錄》“此本董康舊藏,后歸陶洙”張伯駒無(wú)異議,潘素也無(wú)異議。張伯駒名士風(fēng)度,迷戀紅學(xué),有不同見(jiàn)解是會(huì)張口的。
董康《書(shū)舶庸譚》每每寫(xiě)到陶洙,如民國(guó)丁卯1927年1月3日及3月11日均記載有信寄陶心如,足證友誼。至民國(guó)乙亥1935年春夏之交,董康偕陶洙同訪東瀛,著墨尤多,茲僅摘引卷八上四月之事若干:
(23日)余復(fù)有日本之行。……余以校務(wù)孔亟,函托陶心如向清水婉辭。清水君以余名居首,事關(guān)國(guó)際,囑勉為一行。未幾,心如南來(lái),慫勸。不得已,遂定是日乘長(zhǎng)崎丸東航,并約心如權(quán)知秘書(shū)。而杭州高生錫昌亦奉命至東留學(xué),結(jié)伴同行。是日清晨,陶、高二人來(lái)舍,料簡(jiǎn)行裝啟程。……余所居室為一〇五,陶、高二君之室為一〇七。
(24日)午后一時(shí)許入長(zhǎng)崎港,偕高、陶、湯三君登陸。……是日為余與心如誕辰。親友中與余同生日者凡五人,若仁和孫慕韓并同歲,書(shū)肆所刊星命書(shū)常引之。
(25日)小林母堂來(lái)談,已登八五高齡,尚健飯,贈(zèng)余手制財(cái)賦數(shù)事,與陶、高二人均分之。小林談至夜深始別。
(26日)途中風(fēng)物如昨,而心如則孕無(wú)窮之感慨。……余居松之間六番,陶、高二君居五番,為上年楊無(wú)恙之室。
(29日)十時(shí),田中夫婦及乾郎來(lái),偕余及心如至榛原服部三越購(gòu)物。在三越食堂午餐,食品為天夫羅,味至美,心如尤嗜之。斯文會(huì)邀赴東寶劇院觀少女踴,余囑乾郎伴心如代表前往。
(30日)八時(shí)半,偕心如赴圣堂。
此中清水董三(1893—1970)是日本駐華大使館書(shū)記官、間諜頭目、中國(guó)通,工畫(huà),與吳昌碩、齊白石、張大千、溥儒等多有過(guò)從;小林母堂(1851—?)是漢學(xué)教授;田中慶太郎(1880—1951)是京都書(shū)店文求堂主人,與郭沫若關(guān)系甚深,有《羽陵馀蟫》;其長(zhǎng)子田中乾郎(1910—1953)戰(zhàn)時(shí)曾游學(xué)北京,亦通漢籍。高錫昌后來(lái)是浙江地方法院候補(bǔ)檢察官;湯錫祥后來(lái)是中國(guó)蠶絲公司副總經(jīng)理。楊無(wú)恙(1894—1952)名元愷,字冠南,江蘇常熟人,工詩(shī)詞書(shū)畫(huà)。孫慕韓(1867—1931)名寶琦,號(hào)孟晉,浙江杭州人,官至內(nèi)閣總理。
由上引文字可知,陽(yáng)歷4月24日即陰歷三月廿二日是董康及陶洙誕生之日,二人竟?fàn)柾健_@是對(duì)于友情的一種古老暗示,今生有緣,前世注定。難怪董康與陶洙雅誼殷殷,形同管鮑。按《書(shū)舶庸譚》不時(shí)流露出對(duì)國(guó)內(nèi)現(xiàn)實(shí)狀況的極度失望,對(duì)日本社會(huì)文化的由衷膜拜,此為董康戰(zhàn)時(shí)附逆的思想基礎(chǔ)及情感誘因。陶洙也好不到哪里去。此番訪日,董康原無(wú)興致,遂函托陶洙“婉辭”;陶洙非但沒(méi)有設(shè)法推掉,反而“慫勸”不已,終至成行。“途中風(fēng)物如昨,而心如則孕無(wú)窮之感慨”較含混,陶洙的親日心態(tài)或即由此萌生乃至膨脹。據(jù)張同樂(lè)編《華北日偽政權(quán)職官表》,從1937年12月14日起,董康出任王克敏領(lǐng)銜的偽政權(quán)常務(wù)委員兼司法委員會(huì)委員長(zhǎng),僅僅半個(gè)月后的翌年元旦,陶洙出任司法委員會(huì)秘書(shū)長(zhǎng)。一個(gè)委員長(zhǎng),一個(gè)秘書(shū)長(zhǎng),自然是董康提攜陶洙,或陶為董所浼。陶洙根本不懂什么司法,他若自己峻拒,誰(shuí)都無(wú)法勉強(qiáng)他,恐怕是正中下懷,如愿以?xún)敗?/p>
莫跑題,還是拉回到紅學(xué)。壞蛋的友誼也是友誼,也會(huì)遵循東方的人情世故。戰(zhàn)后,董康以叛國(guó)罪身陷囹圄,后保外醫(yī)療,纏綿宅中病榻,陶洙諒必常來(lái)探視慰問(wèn)。彌留之際,董康理應(yīng)明確己卯本(大部分藏書(shū)當(dāng)已抄沒(méi)充公)該怎么辦。他的兩個(gè)兒子(董鐵寶與董申寶)都是學(xué)理工的,對(duì)古書(shū)沒(méi)啥興趣,況且當(dāng)時(shí)雙雙遠(yuǎn)在美國(guó)。客觀情勢(shì)如此,董康又深悉“心如耽于紅學(xué)”,則結(jié)果不言自明。陶洙是個(gè)窮鬼,買(mǎi)是買(mǎi)不起的,董康只會(huì)無(wú)償贈(zèng)送給他。吳恩裕回憶說(shuō):
董康死后,現(xiàn)存己卯本才到了陶洙手里,并由他加以裝裱。據(jù)陶洙告訴我,董康死后到他手之前,也有部分散失的可能性。
這份證言非常重要。陶洙手里的己卯本獲自董康,此信息確實(shí)是陶洙本人透露出來(lái)的。陶洙不僅告訴給了周紹良及朱南銑,還告訴過(guò)吳恩裕。信息途徑非單一,才能有效避免尷尬的孤證不立。準(zhǔn)此,陶洙獲得己卯本擁有權(quán)是在“董康死后”,亦即1948年5月4日之后。
由于這是吳恩裕轉(zhuǎn)述,而非陶洙親筆,細(xì)節(jié)會(huì)打一點(diǎn)折扣。陶洙己卯本題記:
(1)此己卯本闕……均用庚辰本鈔補(bǔ),因庚本每頁(yè)字?jǐn)?shù)款式均相同也。凡庚本所有之評(píng)批注語(yǔ),悉用硃筆依樣過(guò)錄。……與庚本同者,以〇為別。遇有字?jǐn)?shù)過(guò)多無(wú)隙可寫(xiě)者,則另紙照錄,附裝于前,以清眉目。己丑人日燈下記于安平里,憶園。
(2)庚辰本八十回內(nèi)缺六十四、六十七兩回,此己卯本封面亦書(shū)……只得鈔附于后,以存初稿時(shí)面目。丁亥春記于滬上,憶園,時(shí)年七十。
這兩條題記的時(shí)間和地點(diǎn),一是“己丑人日”即1949年2月4日在北平,二是“丁亥春”即1947年1月22日至5月19日在上海。由此可知,董康死前及死后,己卯本都在陶洙手里。具體講,至遲董康死前一年多,己卯本已由陶洙負(fù)責(zé)保管,陶在那上面校來(lái)校去,補(bǔ)來(lái)補(bǔ)去。換言之,縱使董康臨終沒(méi)打算把這個(gè)本子傳給陶洙,也無(wú)用。陶洙掌握己卯本,已是既成事實(shí),難以更改。董康兩手空空在北平蹲牢房,陶洙則拿著己卯本在上海樂(lè)逍遙,乃屬歷史事實(shí)。參看前引顧頡剛?cè)沼?1946年9月17日),陶洙在上海出席鄭振鐸等人參加的書(shū)界聚餐。緣此,應(yīng)不存在吳恩裕所謂“董康死后到他手之前,也有部分散失的可能性”。己卯本缺什么不缺什么,陶洙了如指掌,比董康都清楚得多。
陶洙是否根本未經(jīng)董康首肯,而巧妙地?zé)o恥地竊取了己卯本所有權(quán)?我覺(jué)得尚不至于。陶洙沒(méi)有一直躲在上海灘,最終還是返回到了董康埋骨的北平城,應(yīng)含有為老友送別之意。因獲授權(quán),董康歸西,陶洙搖身一變,正式修煉為己卯本第二任民國(guó)原藏主,遂愈發(fā)肆無(wú)忌憚起來(lái),在己卯本上一通胡亂“鈔補(bǔ)”。學(xué)界公認(rèn),對(duì)珍貴的己卯本而言,那無(wú)疑是一種野蠻糟蹋,陶洙簡(jiǎn)直愚蠢透頂。他在這個(gè)本子上面涂抹了許多廢話,卻吝于交代它的具體來(lái)歷(即董康購(gòu)藏始末),理應(yīng)提出嚴(yán)肅批評(píng)。所幸他沒(méi)有向?qū)W界刻意隱瞞董康的庋藏之功,略可恕宥。
結(jié)束語(yǔ)
茲有周紹良、朱南銑、吳恩裕書(shū)面作證,乾隆己卯本《脂硯齋重評(píng)石頭記》為“董康舊藏,后歸陶洙”。此語(yǔ)源自陶洙親口。跟董康或陶洙有過(guò)密切接觸的紅學(xué)家及熟稔紅學(xué)的藏書(shū)家,胡適、俞平伯、顧頡剛、鄧之誠(chéng)、鄭振鐸、陳仲竾、趙萬(wàn)里、張伯駒、潘素……對(duì)此均無(wú)異議,甚至明確表示認(rèn)可此說(shuō),贊同此說(shuō)。其中鄧之誠(chéng)早在1936年底便親睹過(guò)己卯本原物。因之能夠肯定《紅樓夢(mèng)書(shū)錄》所謂“此本董康舊藏,后歸陶洙”可靠可信。
董康購(gòu)藏己卯本是在1935年末至1936年初,后者可能性更大。爾后,它主要由陶洙負(fù)責(zé)保管。這是因?yàn)槎斩私徽x甚篤,董又洞曉“心如耽于紅學(xué)”。董康死于1948年5月4日,臨終前將己卯本正式饋贈(zèng)給陶洙。由于董陶二氏都沒(méi)有留下相關(guān)的文字材料,所以關(guān)于董康如何購(gòu)藏此本(地點(diǎn)及方式等),現(xiàn)已無(wú)從稽考,期待未來(lái)能夠有所發(fā)現(xiàn)。國(guó)家博物館所藏己卯本三回又兩個(gè)半回殘卷,它的遞藏史跡是另一道風(fēng)景線,此處暫且從略,留待異日觀賞。
① 一粟《紅樓夢(mèng)書(shū)錄》,古典文學(xué)出版社1958年版,第5頁(yè)。
② 張俊、曹立波、楊健《北師大〈脂硯齋重評(píng)石頭記〉版本來(lái)源查訪錄》,《北京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2年第1期。
③ 俞平伯《輯錄脂硯齋本〈紅樓夢(mèng)〉評(píng)注的經(jīng)過(guò)》,《光明日?qǐng)?bào)》1954年7月10日《文學(xué)遺產(chǎn)》專(zhuān)欄第11期。
④ 俞平伯《曹雪芹畫(huà)像》,香港《大公報(bào)》1954年3月30日。
⑤ 顧潮整理《顧頡剛?cè)沼浫罚_(tái)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719頁(yè)。
⑥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8冊(c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16—721頁(yè)。
⑦ 胡適《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píng)石頭記影印本》,見(jiàn)《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píng)石頭記》卷尾,臺(tái)北商務(wù)印書(shū)館1961年版,2ab。
⑧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3冊(cè)第713頁(yè)、第6冊(cè)第221頁(yè)、第6冊(cè)第410頁(yè)。
⑨ 胡適《〈書(shū)舶庸譚〉序》,見(jiàn)《董康東游日記》附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頁(yè)。
⑩ 陳仲竾《談己卯本脂硯齋重評(píng)石頭記》,《文物》1963年第6期。
[11] 陳新宇《向左轉(zhuǎn)?向右轉(zhuǎn)?——董康與近代中國(guó)的法律改革》,臺(tái)北《法制史研究》第8期(2005年12月)。此文收入《尋找中國(guó)法律史上的失蹤者》,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
[12] 梅節(jié)《論己卯本〈石頭記〉》,見(jiàn)《紅學(xué)耦耕集》增訂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112頁(yè)。
[13] 陶洙題記三則,見(jiàn)《脂硯齋重評(píng)石頭記》影印己卯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0年版,第440、677、899頁(yè)。我曾到國(guó)圖善本部借閱己卯本,嘗目驗(yàn)陶洙題記。
[14] 鄧瑞整理《鄧之誠(chéng)文史札記》,江蘇鳳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頁(yè)。
[15] 白淑春《中國(guó)藏書(shū)家綴補(bǔ)錄》,寧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頁(yè)。
[16] 許荻曄《陶洙偽造或陳林臆造》,《新世紀(jì)周刊》2008年8月11日。
[17] 張伯駒《叢碧詞定稿》,見(jiàn)《張伯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18頁(yè)。
[18] 王君南整理《董康東游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46、247、248、249、250、250頁(yè)。
[19] 吳恩裕《現(xiàn)存己卯本〈石頭記〉新探》,見(jiàn)《曹雪芹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頁(yè)。
[20] 陶洙題記兩則,見(jiàn)《脂硯齋重評(píng)石頭記》影印己卯本,第1、17頁(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