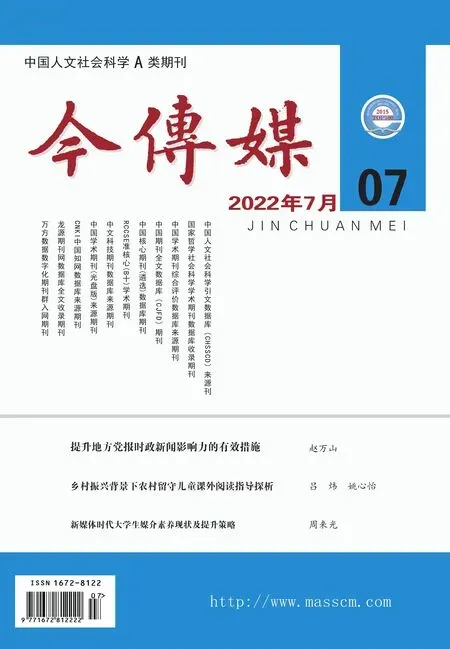淺析博物館游戲化設計的形式與風格
張夢涵
(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上海 200072)
一、游戲、游戲化、博物館游戲化的含義
(一)什么是游戲
日常最熟悉的事物往往難以下定義。傳統的娛樂活動如捉迷藏、體育活動、棋類比賽等均是游戲,但是,當我們真正談論娛樂、體育時,它們通常指的是唱歌、打球等并非意指游戲的活動。“游戲”概念所體現的這種含混與非典型的特點,正是游戲的“典型”特征。游戲的含混性表現在:一個概念其下有許多類別關聯在一起,未必有清晰的共同點;可以與外界非游戲事物劃界線,但這種界限并不嚴密、固定。
目前,不少學者對此展開了研究,試圖找出游戲的共同點、劃清游戲的邊界,并探尋游戲的目標、規則等共通性特點。2003年,凱蒂·薩倫和艾瑞克·齊默爾曼發現,關于游戲的定義大多是對規則、目標和玩法的描述;2013年,歐內斯特·亞當斯在總結游戲定義時說到:“參與者們在規則條件的限制下完成或實現至少一個主觀的、或一般的目標”;簡·麥戈尼格爾在 《游戲改變世界》一書中直接用游戲的四大特征對“游戲”下了定義:目標、規則、反饋系統與自愿參與。
游戲不僅僅是某種行為舉止或生活形式,它還可以作為基礎工具來分析、理解其他學科。荷蘭學者約翰·赫伊津哈在 《游戲的人》一書寫到:“‘游戲’并不是人類文化中的一個附屬部分,而是文化的固有成分,在某種意義上,游戲是一切文化的根基。”
(二)什么是游戲化
基于上述對游戲的理解,可以從兩方面去探討和理解游戲化:一是游戲目標、規則等元素在其他領域的應用;二是游戲作為基礎工具在其他領域的實踐。2011年,Zicherman和Cunningham認為,游戲化是指利用游戲思維和游戲機制來推動問題解決和用戶參與;Deterding認為,游戲化是指在非游戲情景中使用游戲設計元素和游戲設計技術;2004年,Warbatch認為,游戲化是指將某項活動變得像游戲一般的過程。從這些學者的研究中可以總結出,游戲化是通過在非游戲情景中使用游戲設計技術和游戲元素,幫助人們從事物中發現樂趣,通過流程讓各類社會活動變得更有吸引力。
(三)什么是博物館游戲化
博物館是陳列、展示、傳播人類文明和自然遺存的重要領域,需要以自身的環境進行教育、學習以及娛樂活動。博物館游戲化是以博物館的文化內容為支撐,采用游戲化的形式,讓人們在參觀博物館時有更好的體驗感。將游戲機制運用到博物館展陳或傳播實踐中,能夠讓參觀者獲得近似游戲般的參與感、沉浸感、愉悅感以及滿足感。游戲化元素和現代技術創造活態歷史場景,突破時空界限,能夠滿足參觀者的個性化需求;通過互動的形式,參觀者可以參與到設計中來,形成獨特的文化感知體驗,對生活等其他領域產生聯想和反思。
二、博物館游戲化的必要性
(一)博物館現存的問題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的文化需求日益增長,博物館也正在從“以藏品為本”轉向“以人為本”,呈現出特色化、生態化、社區化和人性化的趨勢,但是,依然不能產生持續的關注度。
關于“我們為什么不去博物館了”,旅行者專欄作家奧利弗·史密斯在英國 《每日郵報》的網站上發表了一個調研總結,共有21個原因。其中,多數原因為展品很無聊、博物館環境氛圍太沉悶、博物館的主題內容離我們太遙遠等。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系教授陸建松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除了展覽水平不高、展品常年不變外,關鍵是博物館普遍不重視以館為中心的教育活動,未能與外界形成良好的互動。如今,國內外許多博物館紛紛開始探尋寓教于樂的道路,期望突破傳統博物館固有的模式,高效地傳播博物館文化。
(二)博物館游戲化趨勢
博物館游戲化是連接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紐帶,能夠打開文化傳播的新篇章。意大利作家AlfredoM.Ronchi認為,在信息時代,數字媒體信息已經成為了最受人們喜愛的文化藝術傳播方式。因此,應采用大眾喜聞樂見的方式,靈活多樣地傳播更容易被人們感知、接受和認可的內容,能夠提升公眾的參與度和獲得感。
博物館是非正式學習的場所,游戲也是休閑娛樂和非正式學習的重要途徑,因此,博物館游戲化就是在探索一條突破傳統模式、順應時代潮流的新道路。
三、博物館游戲化設計的形式與風格
(一)參觀者的參與式體驗
博物館是非正式學習的場所,文化內容具有隱晦、間接、需要自我理解的特點,因此,博物館需要強化展覽信息的傳播能力,吸引參觀者主動參與。主動性是參與式體驗的主要特征,參觀者作為主動的參與者,可以用展覽的內容創造并延伸自己的想法。在參與式體驗的過程中,博物館既可以了解到參觀者的需求,還可以與參觀者形成良好的互動關系。
傳統博物館一對多的參觀方式和參觀者散點狀的分布狀態,導致參觀者之間缺乏互動交流;而參與式體驗屬于多對多的體驗方式,參觀者需要完成共同的目標,共同進行探索和學習。在參與式體驗中,參觀者從散點狀態轉變為組合團體,相互交流溝通,最終連接成網狀,傳播著博物館的文化內容。
比如,在首都博物館的“互聯網+中華文明”數字體驗展中,互動桌面的交互展項隨處可見。參觀者圍坐在互動桌面旁,協作點擊桌面上的虛擬按鈕,才可以發現更多有趣的文物介紹,這種方式進一步加深了參觀者彼此之間的交流。
(二)游戲化設計作品的風格特點
博物館游戲化展項設計作品是博物館游戲化最核心的載體,具有以下三個特點:
1.動態展示形式
近幾年,博物館文物的展示方式已由最初的圖文靜態傳輸發展為動態陳展,部分博物館也引入了AR、三維全景等技術,讓展品“動”了起來、講解“活”了起來。比如,動起來的 《清明上河圖》 《雍正行樂圖》,讓“沉睡”在庫房中的文物“蘇醒”了,獲得了良好的展示互動效果,實現了博物館之間的文物流動。
2010年上海世博會,《清明上河圖》再次復活了北宋時期百姓的生活,譜寫了文化傳承與發展的新篇章。巨幅動態 《清明上河圖》運用數字動畫與巨幕投影技術,在展現汴京繁華景象的同時,創造性地融入了夜景。該作品將白天和夜晚分別設置為2分鐘,4分鐘完成一個晝夜交替;色彩搭配也完全還原了原作的古韻、典雅之美,黑白對比,富有新意。
2.交互形式多樣
妮娜·萊文特和阿爾瓦羅·帕斯夸爾-利昂在《多感知博物館》一書中指出,人們在體驗感受一個物體時,會自然而然地想象它的樣子。博物館游戲化設計中的互動設計,意在引導參觀者去體驗文化,讓參觀者在所感受的氛圍中進一步理解文化內涵,實現文化的高效傳播。
博物館游戲化的交互形式可以分為三種:作品之間的交互、作品與參觀者之間的互動、參觀者之間的互動。作品之間的交互往往體現為設計之間的關聯性,通常表現在互聯網技術的連接以及觀展順序的先后方面;作品與參觀者之間的互動,即參觀者體驗的過程;參觀者之間的互動,即參與式體驗多對多社交的特點。
2021年1月21日,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推出了“The Met Unframed”(大都會無限游)沉浸式虛擬藝術和游戲體驗,這款線上展項包括十幾個數字渲染展廳和五十多件館藏珍品,其中,一個數字展廳幾乎模擬了整個博物館的空間。在該游戲中,參觀者不僅可以欣賞梵高的 《麥田與柏樹》、埃及廳宏偉的丹鐸神廟以及14世紀描繪藥師佛的中國壁畫等,還可以參與小問答、謎語和“放大與尋找”挑戰,鼓勵參觀者認真觀察藝術品和其描述的內容。
3.視聽體驗豐富
人類的視覺系統是動物界發展最完備、最發達的器官。人和動物感知外界物體的大小、明暗、顏色、動靜,以獲得對機體生存具有重要意義的各種信息,大部分是經視覺獲得的。19世紀中期,博物館對參觀者行為的嚴格約束與限制,使得他們只能透過展柜玻璃、沿著單調的展線參觀博物館,視覺成為了參觀者主要的感官體驗。如今,博物館界開始重視參觀者的多維度體驗,關注人類的感知和認知,更多地考慮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身體感覺等感官體驗之間的組合和交互。
浦東美術館與泰特美術館聯合展出利斯·羅德斯于1957年創作的 《光旋律》,由兩臺放映機在墻面上形成黑白線條,配合著高頻的數字聲音,線條隨著聲音頻率、振幅大小的變化而變化,延伸出形態各異的“聲音圖形”。黑白線條與光影下形成的人影色塊穿插,給參觀者帶來別樣的色彩構成體驗。
詹姆斯·特瑞爾的 《雷瑪爾·藍》相比 《光旋律》就顯得寂靜一些,其將顏色、光線巧妙結合,放大了人對空間的感知能力,參觀者被完全包裹在一個色彩的空間中,強調讓參觀者去感受、體驗顏色本身。
博物館交互裝置設計注重感官體驗,營造出時空感、沉浸感,為參觀者更好地理解博物館的文化背景、文化元素,以及藝術家想要表達的意圖提供了場景。
四、結 語
如今,國家越來越重視數字媒體對優質文化內容的普及和推廣。博物館游戲化就是一條行之有效的道路,它集科普、交互于一體,能夠以游戲要素的形式承載優質內容,承擔文化傳播的使命,并且具有一定的趣味性,既是文化傳播的新途徑,也為展覽、展陳設計開辟了新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