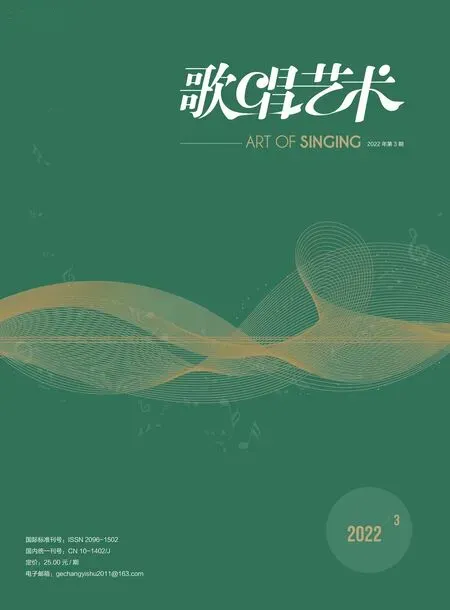喜歌劇院的一場(chǎng)重演:威爾第的《茶花女》
〔法〕德彪西著,張?jiān):套g
喜歌劇院最近隆重地重新上演了歌劇《茶花女》,意義超過(guò)了重演這個(gè)事實(shí)本身,使某些事情回到了自己原來(lái)的位子上,特別是那來(lái)自意大利的(而且也可能回到意大利去的)真實(shí)主義,有人以為真實(shí)主義可能會(huì)影響法國(guó)音樂(lè)……這些事情至少在咖啡館里成了談資,使得有關(guān)所謂“拉丁民族”的反科學(xué)的爭(zhēng)論又重新活躍起來(lái)。
在歌劇《茶花女》中,我們看到了一些意大利年輕音樂(lè)家喜愛(ài)的手法:被觀眾要求重復(fù)的“幕間曲”,讓觀眾拿出手帕來(lái)擦眼淚的浪漫曲,等等。
采用一般能獲得巨大成功的法國(guó)題材來(lái)寫(xiě)作,這一奇怪的欲望,人們也注意到了吧?先是威爾第改編《茶花女》。新近,普契尼先生和萊昂卡瓦洛先生同時(shí)改編了《藝術(shù)家的生涯》。這兩部作品的文學(xué)價(jià)值不該由我來(lái)評(píng)論,但這兩部作品代表了法蘭西情感的一個(gè)特殊時(shí)代,完全可以不借助音樂(lè)而流傳。威爾第的改編至少是率真的。從浪漫曲到詠嘆調(diào),來(lái)回轉(zhuǎn)換,聽(tīng)眾可借以消遣娛樂(lè),因?yàn)樗麄儠?huì)從中時(shí)不時(shí)地發(fā)現(xiàn)至愛(ài)真情。但這些從不自詡深刻,一切都是表面的,盡管處境悲慘,也總會(huì)有些陽(yáng)光的。這種藝術(shù)的審美肯定是不真實(shí)的,因?yàn)樽髡邲](méi)有通過(guò)歌曲反映生活。但是,威爾第的作品有一種違背生活的勇敢方式,而生活也許比意大利年輕學(xué)派試圖論說(shuō)的現(xiàn)實(shí)更美麗。普契尼和萊昂卡瓦洛自以為是在研究人物的性格,甚至是表現(xiàn)一種本能的心態(tài),實(shí)際的結(jié)果只能是簡(jiǎn)單的情節(jié)。
兩部《藝術(shù)家的生涯》就是這種情況的明顯例子。一部是社會(huì)新聞的生搬硬套,感情的表達(dá)帶有“那不勒斯坎佐納歌曲”所特有的齆鼻頭的聲音。在另一部里,雖說(shuō)普契尼試圖找回巴黎人和巴黎市井的氣氛,但仍帶有意大利的喧鬧聲。我無(wú)意責(zé)備他是意大利人,可是為什么非數(shù)《藝術(shù)家的生涯》呢?
馬斯卡尼先生和他包羅萬(wàn)象的《鄉(xiāng)村騎士》,使我們重新掉進(jìn)了社會(huì)新聞的污水里,而該劇想要抨擊生活的夸張手法把污水弄得更臟,結(jié)果只能是騙人的詭計(jì)。令人厭煩透頂!
出于跟意大利人差不多的想法,法國(guó)也曾流行過(guò)尋找外國(guó)的題材,盡管大家總是經(jīng)常發(fā)現(xiàn)一本好書(shū)多么可能會(huì)變成一出糟糕的戲劇。因此,很容易得出結(jié)論:好書(shū)并不一定會(huì)變成好歌劇。
我們?cè)倩氐剿^的“意大利影響”這個(gè)話題上來(lái)吧。“意大利影響”只限于這一研究,而且是局部的。至于法國(guó)聽(tīng)眾是否會(huì)喜歡上意大利味兒的法國(guó)故事,那是另一回事,等著瞧吧……我們有的爭(zhēng)呢。有些人和有些作品,以其只有法國(guó)才有的高尚智力活動(dòng),大聲回答這些雞蟲(chóng)得失的問(wèn)題。應(yīng)該要特別加以肯定。為了把音樂(lè)從謊言的泥潭中解脫出來(lái),使音樂(lè)恢復(fù)原有的美,我們所做的那么多努力,不能就停滯在真實(shí)主義這個(gè)虛無(wú)的工廠里震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