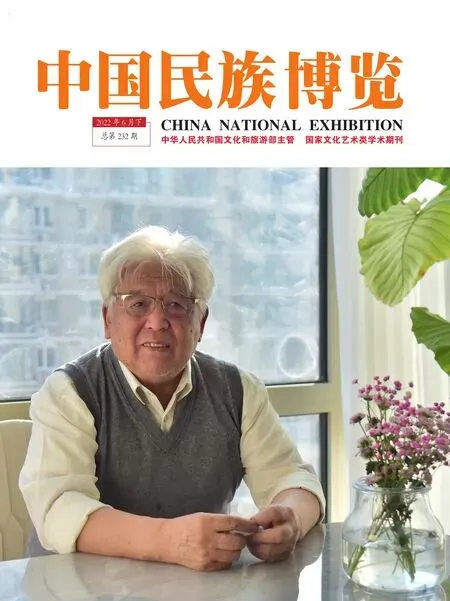現代戲劇傳達悲劇性精神體驗的三種途徑
王東澤
(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甘肅 蘭州 730070)
一、悲劇、悲劇意識與悲劇精神
戲劇文學在步入工業(yè)資本入侵的現代社會之后,呈現出獨特的悲劇性審美特質。馬泰·卡林內斯庫在《現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提到現代具有時期、特征、體驗三種意義,本文所探討的現代戲劇即借用“時期”層面來界定。卡林內斯庫劃分現代的時期即為“在十九世紀前半期的某個時刻,作為文明史階段的現代性科學技術進步、工業(yè)革命和資本主義帶來的全面經濟社會變化的產物”。“現代悲劇”就是此種現代定義下的結果,一種作為在人類文明史進入現代工業(yè)社會后出現的戲劇類型,而非局限于僅具有現代主義或后現代主義特征的戲劇作品。
悲劇一般內含于戲劇這一整體概念中,但悲劇的概念同樣也是難以界定的,事實上關于中國是否存在悲劇的爭論也仍未停息。對此筆者只對部分觀點進行闡釋。總體上看定義悲劇有兩種途徑的嘗試,一是文體意義上的悲劇,二是泛審美意義上的悲劇。亞里士多德定義悲劇毫無疑問是文體上的,將其界定為“悲劇是嚴肅完整的,對有一定長度的行為的摹仿,通過憐憫恐懼,受眾情感得到陶冶。”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形式上符合這種程式并且使受眾獲得固定的審美體驗的文體就是悲劇,包括主體必須受到不可避免的沖突,人性受到傷害,從而引起受眾的悲壯憐憫或恐懼,最后精神得到升華。受眾在閱讀或觀看悲劇時會產生強烈的心理效應,感同身受此種結局可能發(fā)生在自己身上。尼采獨創(chuàng)性地引入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來理解悲劇,認為悲劇源自酒神精神,它破除以代表夢境狀態(tài),造型藝術的靜態(tài)的日神精神的外觀幻覺,與本體溝通,最后直視人生悲劇。這本身便與叔本華的哲學不謀而合,即認為人的存在即伴隨著痛苦,而悲劇快感便是一種形而上的慰藉,它使我們暫時逃脫事態(tài)變遷,感到事物基礎中的生命堅不可摧并充滿快樂。這便是泛審美意義的而非文體意義層面的定義,因為它只規(guī)定了受眾在審美過程結束后需要獲得的心理感受,沒有規(guī)定具體的文本程式和戲劇主人公必須受到損害并伴有悲劇結局的要求。石娉娉相似地指出存在廣義上的悲劇概念。廣義的悲劇是泛指人類在現實生活中所遭受到的不幸、苦難、痛苦以及隨之而來的悲慘性的結局。石娉娉討論的廣義的悲劇已經超越了狹義的悲劇,更接近常說的“悲劇性”,而且這種悲慘性結局不一定是主體被毀滅,且不一定伴隨著雙方激烈的沖突矛盾與斗爭反抗。
沿著這一思路出發(fā),若要對悲劇相關概念進行較為正確的分析,則應一分為二地從文體與審美兩種層面進行判斷。這樣便有助于對“中國有無悲劇”等問題做出回應。首先要先分辨“悲劇”是作為文體還是泛審美范式來討論。有學者指出中國古代沒有西方意義上的悲劇,但也有學者認為中國古代同樣有悲劇,只是中國古代的悲劇作品與西方的悲劇作品具有不同的藝術特征。前者是從西方文體意義上的悲劇為模板在中國古代文學典籍中搜尋,后者則是采取類似于石娉娉的廣義的悲劇觀點來看待此問題。于是單從文體意義上看待,就有了第一種觀點。中國古代沒有具有古希臘悲劇那種規(guī)模和范式的文學作品。而當我們把中國古代那些我們當下稱為悲劇的作品納入西方悲劇美學理論的范疇時,打破西方“悲劇”概念固有的封閉性, 我們就有了第二種觀點。朱立元認為先秦時代的文學作品便反映出中國古人的悲劇觀,其包含著人生價值觀和宇宙觀等不同的層面,如《詩經》《楚辭》以及《莊子》中,這些文本都有對于人生中有價值的東西被毀滅表現出無奈和感傷的悲劇意識,都表達出對人生的終極結果的疑問,對于生死離合從審美角度上進行了把握和描繪。
至于悲劇意識與悲劇精神,大抵也是由文體意義延伸到審美意義上來的,只不過兩者的主體有所不同。悲劇意識是人的意識,不管悲劇是否發(fā)生,悲劇意識都始終存在,貫穿了人類發(fā)展始終。悲劇精神則是作為文體的悲劇帶給觀眾或讀者精神上的一種震撼,側重于悲劇發(fā)生后,劇中主人公所彰顯的一種契合悲劇特質的精神。石娉娉強調悲劇意識是一種憂患意識,“悲劇意識是一種人生觀,是一種人類與生俱來的、如影隨形的憂患意識,一旦出現了誘因,就會爆發(fā)。所以,悲劇意識最主要的表現就是憂患意識。憂患意識是人生悲劇感的一種體驗模式,是一種自覺的痛苦”。她所理解的悲劇意識是一種自覺的同情,這無疑強調了悲劇帶給人的精神感受。王富仁從文學的歷史進程中闡釋悲劇精神與悲劇意識。“在這里,有人類對自我存在的悲劇意識,有貫穿于這個神話故事的悲劇精神……司馬遷建立起了自己的悲劇意識,他的悲劇意識并沒有導致對人的悲劇精神的否定”。王富仁看待悲劇意識是對于個人,個體而言的,而悲劇精神是對整個人類而言。除此之外,王富仁提出了悲劇意識與悲劇精神在不同文學體裁中的表現,“悲劇意識可以在短小的抒情詩中得到強烈表現,悲劇精神則只有在敘事性作品中才能得到真正有力的表現。因為悲劇意識是一種沒有長度和闊度的情感,而悲劇精神卻必須在一種長度和闊度中才能得到更充分的表現。小說和戲劇都是敘事性的作品,也都有可能表現悲劇的意識和悲劇的精神,但西方的悲劇主要是指戲劇中的悲劇,這是因為戲劇比小說更集中、 更單純。它的悲劇也是更集中、更單純的悲劇”。作為美學意義上的悲劇精神,雖然脫胎于古希臘悲劇,但在后期發(fā)展中定義發(fā)生了擴大,強調的是審美體驗上的悲劇性,可以表現為悲哀、痛苦、同情。如果泛悲劇化,那么可以體現悲劇精神的體裁不僅限于戲劇,還有小說甚至是詩歌。
可以肯定的是,西方的悲劇意識一開始就與宗教意識緊密聯系在一起,從宗教意義上來講,實際上西方悲劇崇尚的是一種犧牲。似乎一直延續(xù)到20世紀后現代主義,西方的美學思想都在關注人本身生存的幻滅感。而中國古代宗教意識相對淡薄,悲劇意識與宗教意識沒有直接聯系。就結局而言,中西古代悲劇也大相徑庭,古希臘悲劇所體現的是主客沖突及慘厲效果,這在中國古代文藝作品中比較罕見,取而代之的是大團圓結局。中國古典戲劇往往借助天地神靈的力量來改變人在現實中無法改變的命運,從而表現“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理念。
而當試圖論述現代戲劇文學是如何使受眾產生近似于古希臘悲劇那種憐憫、恐怖的莫名的悲哀時,會發(fā)現悲劇意識與悲劇精神都無法完全恰當地表稱這種審美體驗。因為這種體驗往往結合了個人和整個人類命運的思考。于是筆者使用“悲劇性精神體驗”一詞來指稱美學意義上現代戲劇給予受眾在閱讀劇本或觀看戲劇時產生的強烈的心理精神感受,并將之做以下定義,“悲劇性精神體驗表現的是戲劇受眾在閱讀劇本或觀看戲劇時面對自我的生存困境時,對自我人生、命運進行根本思考的一種身體性體驗。”這個概念是立足于戲劇受眾的立場而且從某種意義上可以包含美學意義上的悲劇意識和悲劇精神,適合對題目的表達。
二、現代戲劇表達悲劇性精神體驗的三種途徑
宿命論是作為第一種途徑出現的。人企圖掌控自己的命運,但最終仍陷入宿命的困局,這便是莫大的悲劇。人對于“命運”的無力往往是悲劇的根源所在,現代戲劇承襲古典戲劇,在對于“命運”的表現上把人在“命運”控制下的脆弱、孤獨與渺小表現得淋漓盡致,人的存在始終掙扎不出宿命。
中國新文學史上有曹禺的《雷雨》。其中“雷雨”作為神秘的第九個角色,始終貫穿全劇,從某種意義上說,造成了最后悲劇的發(fā)生。某種程度上的“雷雨”似乎可等同為古希臘戲劇中提到的“命運”。“命運”沒有辦法出場,但又和其他八個角色緊密關聯,甚至一些人物的主要性格的建構就是為了“命運”的到達而服務。《雷雨》可看作對古希臘戲劇的致敬。人無法擺脫命運,如劇中對魯侍萍的書寫。《雷雨》是社會悲劇與命運悲劇的結合,兩者組成了“宿命論”悲劇。從魯侍萍離家那一刻起,第九個角色“雷雨”就已經粉墨登場,“命運”將一切矛盾和巧合拿捏得恰到好處。無獨有偶,美國戲劇家尤金·奧尼爾在其戲劇創(chuàng)作中也對宿命論頗感興趣,只不過奧尼爾思想中的宿命和巧合大多是與“海洋”有關。前期現實主義作品《安娜·克里斯蒂》就刻畫了一個典型的被命運愚弄的水手長克里斯的形象,一生憎惡大海最終卻又回歸大海,甚至連女兒安娜的命運也要交付給大海。戲劇結尾表面上是大團圓結局,但深層次上更像是重復上一代人生命的輪回。作為象征因素的“霧”充滿著神秘主義色彩,仿佛告訴讀者人生就如同在迷霧中航行,無法主動選擇方向。奧尼爾對此種宿命觀的書寫并非是無意的。相反,這是作家對現代戲劇做出深刻理解之后產生的自然的行為。誠然,奧尼爾對于宿命論的審慎和偏愛也是源于古希臘戲劇,“用獨立并且明確區(qū)別于我們稱之為現實的戲劇的藝術來解釋生活,也許能表達那種巨大的力量,而現實只是這種巨大力量的一個蒼白無力的象征……簡單地說,戲劇應該回復到古希臘戲劇的那種宏偉的精神”。同時奧尼爾在諸多古希臘悲劇詩人中尤其尊崇埃斯庫羅斯,正是因為埃斯庫羅斯的悲劇中展現了一種無形的力量,它涉及諸神在內的一切人的賞罰和神秘的法則。正是欣賞自古希臘悲劇由來已久的命運觀主題,加之對現代社會人的存在的深切體認,奧尼爾將宿命論作為自己戲劇創(chuàng)作的重要一環(huán),目的即在于深刻而頗有洞見地展現生活的原貌。
悲劇性的荒誕書寫是第二種途徑。西方后現代主義戲劇家貝克特的《等待戈多》與阿爾讓的《血噴》正是這類的代表。作品論述在后現代主義中人的存在受到質疑,在信仰喪失、語言貶值的大背景下,是現代戲劇表達悲劇精神的新方式。荒誕一方面是工業(yè)化模式下看清自身價值后的人的自嘲,另一方面也是現代人的反抗理性主義、資本生產結構的手段。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戲劇的悲劇精神就等同于荒誕精神。荒誕精神內涵豐富,包含著語言的荒誕、情節(jié)的荒誕以及信仰的荒誕。在任何皆可疑的時代中,人不能成為人。在前工業(yè)社會,人更多地可以通過將客觀本質力量對象化反過來肯定自身,但如今人們找不到可以將之對象化的客觀實體,人的存在不再被肯定,人成為工業(yè)生產流水線上的一個螺絲釘。在具有荒誕情節(jié)的現代戲劇中,主體的無力感、內容的片面化、形式的丑怪使得人獲得悲劇意義上的憐憫與恐懼。在欲望橫行的現代工業(yè)社會,悲劇在表面上喪失了傳統(tǒng)的崇高與嚴肅,但于實在層面則更能引發(fā)“靜穆與偉大”的審美體驗。
貝克特對于悲劇性精神體驗的傳達,就是證明了“存在即死亡”的命題。當人身處現實社會卻無法對現實說“不”的時候,就是人存在的巨大的悲劇。因為既然這樣,為何不去選擇死亡?在現代戲劇中,個人存在的死亡有三個方面的呈現。首先是語言的死亡。《等待戈多》中,戈戈和狄狄在百無聊賴的生活中企圖用語言來填充虛無,結果語言也變得無意義。他們在戲劇開場時毫無邏輯的對話就表明,現代語言存在的意義只是填補無盡的時間,不作為有意義的溝通媒介。如狄狄和戈戈在等待戈多時的對話,似乎只是讓對話不再停止,因為一旦停止對話,就會陷入更大的空虛。在這種情況之下的對話,就喪失了意義所在。“戈戈:這倒是真的,你能肯定在這里嗎?狄狄:什么?戈戈:必須等待。狄狄:他說在樹前。你還能看到別的樹嗎?戈戈:這是什么樹?狄狄:看樣子是一顆柳樹、戈戈:那樹葉在哪里呢?狄狄:它可能枯死了。戈戈:漿液都沒有了。狄狄:興許還不到季節(jié)。戈戈;:它看上去更像是一種灌木。狄狄:一種小灌木。戈戈其次是個人的死亡,但這種死亡與古希臘悲劇的個人死亡截然不同,它不像俄狄浦斯一樣是肉體上刺破雙眼式的懲罰,也不是精神上的偉大自省、勇擔懲處,對抗命運的“自我放逐”,而是“被迫放逐”。貝克特把人放于二戰(zhàn)后的工業(yè)發(fā)展和消費主義把人的生存空間壓榨得所剩無幾的現代社會,就是要人喪失主動,喪失自我。或者說,人唯一能做到主動可能就是被迫追求無意義。狄狄和戈戈的等待戈多的行為看起來是掌握著主動權的,實際上,這仍然是荒謬的被動等待。他們不認識戈多,不知道戈多長什么樣子,不知道戈多的具體情況,甚至無法主動和他取得聯系。他們之間唯一的信息傳遞全部通過小男孩,而小男孩顯然是受戈多的操縱。而且,在戈戈狄狄和小男孩的對話中,小男孩都刻意回避使用描述性話語,而是以“我不知道,先生”或“是的,先生”這樣的語言回答,架空了戈多的存在,令狄狄戈戈無法了解戈多,阻礙了主體認識的能動性,造成個人存在的死亡。最后是信仰的死亡。在被普遍異化的現代社會,上帝再也不能以博愛來拯救世人,既然“上帝死了”,那我們便擁抱魔鬼吧。信仰魔鬼的結果就是第三種死亡即信仰死亡。人的精神向低級、虛無和情色靠攏。《等待戈多》中對基督傾覆的描述非常醒目,首先是戈戈和狄狄同戈多,那種像一些評論家一樣把戈多看作上帝的象征時的相約,這本身就是基督中神與人定下的契約精神,而結果卻是神的缺席和毀約。其次就是拒絕懺悔,當狄狄在猶豫要不要懺悔一下時,戈戈反問“懺悔什么”“為出生而懺悔嗎”。人的出生是無法選擇的,只能繼續(xù),因為不需要進行懺悔。
現代戲劇中在消解信仰的強度上,阿爾托顯然比貝克特更殘酷。他在《血噴》中直接寫道:“妓女:放開我!上帝!(她在上帝的手腕上咬了一口。巨大的血柱撕裂了整個舞臺,在火光的閃爍中,教士在不停地手畫十字進行祈禱。火光還在繼續(xù),所有人都死了,他們的尸體和殘骸散落各處。只有少男和妓女貪婪地注視著對方,隨后妓女跌入少男的懷中)”《血噴》里上帝被一個妓女反抗,甚至被咬出巨大的血柱,神的身份遭受徹底的質疑。上帝的鮮血意味著在如此荒誕異化的社會中,上帝和人一樣都會付出慘痛的代價。被工業(yè)碾壓過的現代社會,信仰喪失本質主義的神圣光輝,人作為上帝的杰作,本來也應天性美好,善良純真,但劇中的人物幾乎都是骯臟、惡心,猥瑣的,如“妓女像一片薄烤餅”“胸部已經干癟”“腫脹的乳房”。
最后,現代戲劇通過元戲劇來傳達悲劇意識,本質就是某種文體通過反對自身來獲得悲劇效果,可以看作是文學形式自身的后現代化。可以說,在現代戲劇表達悲劇性精神體驗的最后一個途徑就是否定戲劇自己。從這一意義上來講,元戲劇這一形式自身就飽含著十足的悲劇性審美體驗。宿命論和荒誕書寫這前兩種途徑都是現代戲劇作為主體施加給人物或情節(jié)以悲劇性效果,相比較而言,現代戲劇傳達悲劇性精神體驗的第三種途徑則更富有悲劇意味,它與后現代主義文學一切四散后空心的狀態(tài)達成和解。元戲劇有意暴露自身是戲劇本身,刻意拉遠同觀眾的距離。如戲劇《陽臺》第一場里,“伊爾瑪:該說的都說完了。等戲演完了……”到第一場結尾“伊爾瑪:很美,不過您必須走了。您把車停在路口了,電線塔旁邊……(主教很快換上了日常服裝,把他的教袍扔到一邊)”以及最后一場警察局長對羅杰飾演自己的評價,“演得好,他相信已經被我靈魂附體了”。《陽臺》徹底的“戲中戲”結構,在大陽臺俱樂部中,人們希望通過演戲切換自己的身份,滿足欲求,但“演戲的演戲”只會讓觀眾自覺地從沉浸中脫身而更關注演員的動作和戲劇形式,也更容易引起觀眾對自身的反思,即反思自己是否也是置身于一種大舞臺,為了演戲而生存。由此而來的對于生存的思考便直接地指向現代人的生存命運。可以說,讓·熱內的元戲劇比元小說更能起到懷疑自身的目的,很容易導致觀眾自覺地身份疊加,思考自己和臺上演員的身份關系,形成看與被看的社會層面上的二元結構。如果說前兩種途徑是文本受眾先在角色的身上發(fā)現了悲劇性因素后再引申在自我身上,那么,元戲劇《陽臺》則直接讓受眾在現實層面激蕩起悲劇意識,通過臺上身份(演員)和臺下身份(自身)的瞬間對照,通過“演戲”本身——只需要意識到這種形式,無需了解劇中人物是否有悲慘命運以及結局如何便進行自我反思,無需經歷一次思維轉換的過程,然后獲得一種快樂,這邊回歸了戲劇最本質的功能與最基本的意義上來。這比前兩種途徑更為高明。
三、結語
所述綜上,現代戲劇在表現悲劇精神上手法是多樣的,既有側重于主題意義,如借用古希臘戲劇沿襲而來的“宿命論”傳達悲劇性,也有現代社會的新的表達方式,如從文本內容層面帶來悲劇體驗的荒誕式寫作和從文本形式層面通過反抗自身形式來達到悲劇體驗的元戲劇。需要注意的是,悲劇性精神體驗也只是眾多現代戲劇所傳達的閱讀體驗之一,此外,它也會從一種且從不同角度看,對于“現代戲劇表達悲劇性精神體驗的三種途徑”這一命題的回答也有不同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