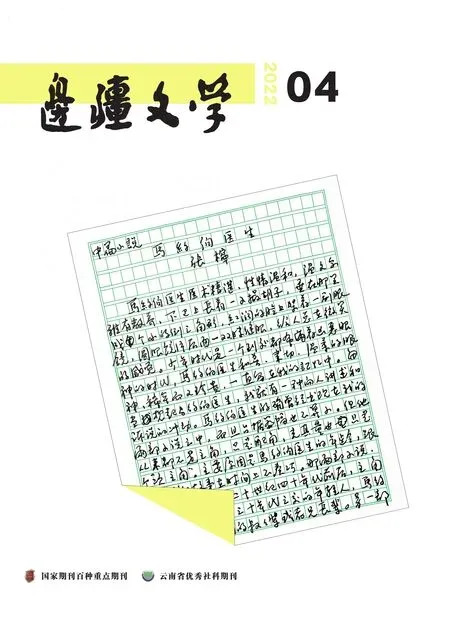泉子的詩(shī)
泉子
自責(zé)
一個(gè)只能記起自己名字的老人,
因迷路,
而踟躕于深夜的街頭。
當(dāng)幫助她的警察將她領(lǐng)回派出所,
她因不能提供更多信息
而深深自責(zé),
“我很討厭吧?”
她一遍遍地問。
而每一次聽,
你的眼淚
都抑制不住地,
滾落下來。
嚴(yán)寒
當(dāng)他對(duì)那個(gè)在剛剛發(fā)生的一件事上
虧負(fù)于他的恩人
說出一種惡狠狠的詛咒時(shí),
你的后背突然領(lǐng)受到了
由一根冰針尖頂
以及那同時(shí)從你心底浮出的冰山
所贈(zèng)予的嚴(yán)寒。
這個(gè)曾如此風(fēng)華正茂者
那個(gè)在熙熙攘攘的十字路口
突然大聲喊出我的名字,
而又在我的遲疑中主動(dòng)報(bào)出
自己名字的人,
我驚訝于這個(gè)曾如此風(fēng)華正茂者
在跨過近二十年的時(shí)間溝壑后,
此刻所擁有的
一張如是滄桑的面容。
我不知道用一個(gè)怎樣的詞語來描述她
我不知道用一個(gè)怎樣的詞語來描述她,
或是那由薄紗裙所勾勒出的
一條比完美尚過之的曲線,
仿佛 ——
你心中一條不知被誰的手指
撥弄后的琴弦,
又宛若
你在俯首的一刻所見的
那些落滿水面的波紋。
箭矢
詩(shī)是為對(duì)抗時(shí)間
與死亡
而發(fā)出的
一支支在你的凝視中
靜止不動(dòng)的箭矢。
歪脖子樹
一棵倒伏于地的歪脖子樹
引來了一陣陣狂笑,
“要有多懶才會(huì)長(zhǎng)成這個(gè)樣子?”
而你從他(她)們身邊經(jīng)過,
并繼續(xù)以踽踽獨(dú)行丈量著
這人世從來的艱難。
口琴
這個(gè)坐在孤山北麓的長(zhǎng)木椅上吹著口琴的
兩鬢斑白者,讓你想起亡兄,
他用從福利院領(lǐng)到的第一筆工資的近三分之一
買來一個(gè)锃亮的口琴,
并磕磕絆絆地吹出第一支完整的曲子時(shí)
那從臉頰上漫溢出
而又充盈于整個(gè)人世的歡喜。
你必須
你必須去成為
這繁華落盡的見證者,
你必須再一次說出
一個(gè)悲欣交集的人世。
老院長(zhǎng)
他曾幫助過無數(shù)的人,
但事后發(fā)現(xiàn)
其中的絕大多
都是不值得去幫的。
這個(gè)剛剛退居二線的老院長(zhǎng),
他聲音中有一種深深的沮喪,
與悲涼。
他接著說,
而人世又終究是
一次漫長(zhǎng)的修行。
不知曾幾何時(shí)
曾經(jīng)你會(huì)定期去抱樸道院,
沿葛嶺一側(cè)拾級(jí)而上,
在山腰盤桓半日,
繼續(xù)登頂,
然后從寶石山的另一側(cè)下山。
而不知曾幾何時(shí),
你更愿意去遠(yuǎn)觀,在白堤,
在逸云寄廬與錦帶橋之間,
去看那黃色的院墻
一次次從山的皺褶間浮出,
又一次次為蒼翠的樹枝
所掩翳。
每日之新
進(jìn)入現(xiàn)代主義之后,
對(duì)新的渴望幾乎是絕望
而接近于癲狂的。
那是一種無家可歸后的
每日之新,
是一顆無處安放的靈魂的
每時(shí)之新,
是“上帝之死”后
萬古長(zhǎng)夜中的恐懼
與絕望之新,
是一個(gè)進(jìn)化論,
或直線式的時(shí)空觀的信奉者
在每一瞬間的
分崩離析之新。
另一極
“五四”諸干將的言論
在今天看來是有諸多過激之處的。
但如果我們能獲得
一次歷史更深處的看的話,
又是合理,
或依然是守中的,
就像鐘擺剛剛抵達(dá)
或越過的
另一極。
詩(shī)
詩(shī)是一個(gè)人未得究竟
又為這我們所自處的勝境吸引,
而毅然決然
而踽踽獨(dú)行時(shí)
所見的風(fēng)景。
山中無所有
山中無所有,
只此靜與詩(shī)。
圓月與枯荷
永恒的西子湖,
不朽的你我、圓月
與枯荷。
當(dāng)你認(rèn)定以良寬為楷模
當(dāng)你認(rèn)定以良寬為楷模
或你之命運(yùn)時(shí),
人世便突然間
獲得了
一種深深的靜寂。
二十年
二十年仿若彈指一揮間,
而你驚詫于 ——
你與這片山水
此刻所擁有的
一種如此殊勝
之關(guān)聯(lián)。
——帶你認(rèn)識(shí)口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