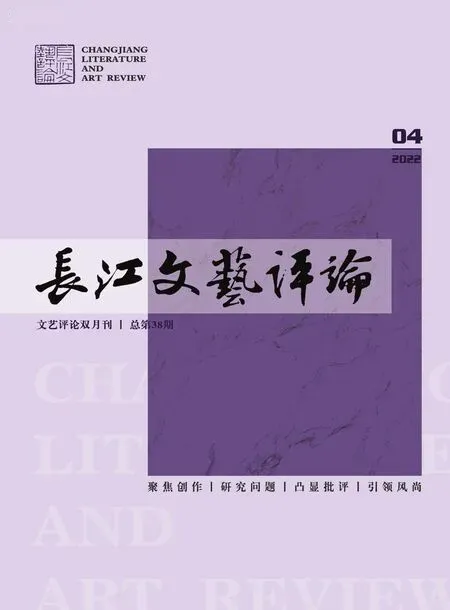文學汰存與經典裁量
◆劉詩偉
創作者為心中的塊壘而創作,并不是為了提交一部經典作品;即使當初他們預感自己的創作將是偉大的,這也并非他們投入創作的原生動因或動力。但是,文學和文明發展到今天,任何創作都在既有經典的叢林里發生,任何有雄心的創作都不可能不面對既有的經典;那么,一個明智的創作者在學習和冒犯經典的同時,是不是還應當了解文學汰存與經典裁量的真相及乖謬呢?
一般而言,每個時代都有當期社會主導者認可的文學經典,每個時代的不同社會階層(或族群)都有屬于本階層共賞的文學經典,每個時代的每個讀者都有自己主張的文學經典——作為讀者的作家也不例外。這是談論文學經典時容易看到和確認的事實。需要指出的是,這個事實到了當代,呈顯日趨多元復雜的態勢。
什么是文學經典?現在人們脫口而出的是卡爾維諾的那句名言:一部經典作品是一本從不會耗盡它要向讀者說的一切東西的書。作為經典的定義,專業人士公認這是一個好說法。所以好,除了對于經典的內在品質的揭示,還直截了當地明確了經典與讀者的關系——實際上確立了整體讀者對于文學作品的汰取資格與裁量權。“整體讀者”是作家的困難和研究者的麻煩,但它是談論經典的起點。
一部經典作品的“一切東西”為什么在讀者那里“不會耗盡”?
當然是它的品質或文學性決定的。文學不是簡單輸出知識、觀念和思想的載體,文學力圖以具有概括性的具體形象抵達人性與人生的深部,反映生活的深刻意蘊,讓讀者在閱讀中恢復對生活的感覺,感受陌生、具體、鮮活的事物,在感受的過程獲得審美愉悅。這便是雅各布森所說的:文學性是使一部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那個東西。在這里,“那個東西”便是卡爾維諾的“一切東西”。關鍵在于作品內涵與讀者感受:作品以形象訴諸感覺,閱讀感受即目的。形象不同于抽象,一旦由“畫工”轉為“化工”(李贄說法),可以大于思維,可以變幻意味,可以意味無窮;而感受不同于理性認知或被動接受,作為感受主體的讀者動用的是感覺(六感),感覺不是閉環狀,是開放、無界、蔓延和延展的,正好呼應藝術形象。
假定一部作品屬于經典,其表現人性與人生的深刻性便帶有普適性和普世性,因而得以長久映照現實生活;而且,在閱讀中,其藝術形象不再只是作者起初預設的意涵,會讓讀者的感受發生無限量的化學反應:首先,不同的讀者感受不同,“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其次,即使是同一讀者,如果在不同時期閱讀,由于心智心性心境的變化,也會讀出不同的意味,正所謂常讀常新或者“舊書不厭百回讀”;之后,時代更替了,經典仍然“映照”生活,又在新生讀者的心中發熱放光。
——原來是經典的“文學性”在讀者那里“不會耗盡”。
至此,忽然有一些問題接連冒出來:誰對整體讀者的文學閱讀做過“市調”?誰在沒有做“市調”的情況下言說和裁量經典?這種言說和裁量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這種言說和裁量與整體讀者究竟會發生什么關系?……有趣的是,在這些問題含糊不清或者尚未運用科學方法加以解決的時候,我們已經產生了經典,歷來都有產生,迄今已然汗牛充棟。而且,我們幾乎沒有理由不相信大多數既有經典符合關于經典的“公約”的圭臬。
也好,問題的研究倒是方便起來。當我們直接檢視這些既有的經典時,即刻就能抓住經典的兩個“卓越回應”:一是卓越回應時代生活,一是卓越回應過往的文學(包括經典)。
在回應時代生活方面,前面說過創作者心中的塊壘是文學創作的動因和動力,但塊壘只是關于生活的積淀與發酵,其文學效能取決于“積淀與發酵”的廣度和深度。所以,問題不在于是否對時代生活做了回應,而在于回應達到的程度——文學之高下云泥在此。以這個為理據,文學對生活的回應其實是文學性的實現:文學性注定以人、人民、人類的生存(存在)為中心,以人性、性格、命運及其環境為關切——以形象化、個性化的語言為形式與內容,以生動、神奇、美妙的形象(意象)為形式與內容,以新穎、獨特、迷人的敘事(包括故事、情節、細節、結構、節奏、色調)為形式與內容,以情感、趣味、理性的有機融合為形式與內容——從而生發藝術力量。所謂藝術力量,對作品而言是指藝術表現力,對閱讀則是藝術感染力,“二力”實為一體兩說,一部作品兼而有之,才稱得上經典作品,才會產生經典效應。莎士比亞戲劇故事在莎翁之前有人寫過演過,莎翁再寫再演,之前的那些作品全都被淘汰了;塞萬提斯之前有人寫過類似堂吉訶德的故事,讀者唯獨鐘愛塞氏《堂吉訶德》;多數讀者只知道歌德的《浮士德》,從來不曾聽說歌德之前還有多種浮士德版本:為什么?因為文學性的超越,而且后來沒有同類作品可以與之匹敵,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文學高峰,一茬又一茬地“收割”閱讀者。所以,與其說經典是對生活的卓越回應,不如說經典是文學性達到了某種頂峰。但此處必須馬上交待:一部經典作品,其創作主體秉持至真、至善、至理、至美的藝術理想,在創作中,必然規約文本的真、善、理、美的向度;如此,文學性與藝術感染力實際上包蘊了思想精神和文學倫理。閱讀的情形也正是這樣,感染讀者的東西無外乎文本溢出的情感、趣味和理性——而情、趣、理既屬于思想精神范疇,也是文學倫理的遵循。本質上講,文學沒有沒有文學性的思想內容,也沒有沒有思想內容的文學性。這應當是文學的元義,也應當成為考察文學回應生活的最根本的方法論。
所謂經典對過往文學的卓越回應,是指新的偉大作品在回應時代生活時取得了新的藝術成果,但強調的則是新的偉大作品在回應時代生活時不同于(或超越)過往文學的藝術突圍。所有偉大創作都會自覺回應過往的文學——不單是學習、借鑒與繼承過往的文學(包括經典),更重要的是在學習、借鑒與繼承的基礎上,讓創作的核心部分規避過往文學的形式與內容,有所冒犯和揚棄,從而奉出不一樣的新文學。人類迄今“公約”的文學經典中,沒有一部后來的經典跟它之前的任何一部經典相似或相同,其不同,不只是時代、人物、故事和敘事手法不同,根本在于作品意蘊和美學不同——不如此,后來的作品不可能成為經典。經典只能是唯一的。文學創作常有盲目慶祝的案例:一部作品完成后,作者及圈子里的朋友即刻歡呼杰作問世,但其實成就不高,不過是對過往文學(包括經典)直接或間接的因襲,本身跟經典無緣。倒不是說這樣的作品不可以去寫,問題是我們在談論經典,經典的大殿沒有給出這樣的席位。這是沒法調和的。因此,有人說過“女人是鮮花”,自第二個人起,再這么說或者像這么說都是平庸的,明擺著是朝向經典而背離經典的追隨。經典是獨行獸,卓爾不群地冒犯一切。這一點,對于創作的雄心是挑戰,也是啟示。否則,文學就成了可愛的自嗨或自慰的繁榮。
接下來,顯而易見的是,既有的經典并不是單一品種的收集和堆積,更像是一個品種多元的建制。其中,有山巒也有河海,有老虎也有杜鵑,有寫實也有幻象,有大塊頭也有小個子,有血與火也有風與月;有硬核敘事也有唯美書寫……有各種各樣的高級的文學性。它是生活訴求對文學的投射,是文學回應生活時的發現與發明,是趣味多樣化的閱讀選擇的結果。以作品內容的主要特征進行分類,至少有以下八種:一是終極呈現人的問題,如《圣經》《神曲》《浮士德》;二是宏闊再現社會生活,如《紅樓夢》《雙城記》《戰爭與和平》;三是深刻揭示時代人性,如《阿Q正傳》《高老頭》《鼠疫》;四是生動表現人生困境,如《包法利夫人》《罪與罰》《變形記》;五是深入探索人的精神世界,如《離騷》《尤里西斯》《生命不能承受之輕》;六是精妙表達情感風物,如《詩經》《項脊軒志》《雪國》;七是“越界”觀照人類社會,如《西游記》《瓦爾登湖》《時間機器》;八是作為歷史的書寫,如《斯巴達克斯》《三國演義》《創業史》。當然不止這八種,而這八種肯定還可以更科學地細分。但這里不過是要盡快得出結論:一切既有經典都在回應特定時代生活時做出了最好的藝術反映或表現,是文學在科學、哲學、神學之外對人類文明所做的不可替代的精神奉獻;同時,也折射了人類生活與人類文明對文學的期許、汰取和認領。人類生活持續運行,人類對于文學的訴求和對經典的需要將持續下去——這不單是少數吃文學飯的人的意志。
但事情似乎愈發麻煩起來:以上討論不僅沒有讓文學汰存與經典裁量變得涇渭分明,反而把問題帶入了渾濁動蕩的河流。
從歷史看,不同時代的同一國家(種族)、同一時代的不同國家的文學經典實際上不大一樣;而且,這種“不大一樣”是在排除文學閱讀障礙和圖書發行利益等因素的前提下,面對共有共知的文學作品時——發生的。為什么面對相同的作品會有不同的汰取?原來文學汰取的“通標”幾乎難以達成,除去極少數全世界“公約”的經典,更多的文學汰取與經典裁量受到時代和地域(國家)背景的“整體性”制約,不同的歷史、文化、風俗、經濟、制度、政治、教育各自匯合起來,形成不同的復雜的審美取向和文學選錄動機,從而完成了文學汰存與經典裁量——其中,包括短期內(甚至百年內)強力干預、一錘定音的短命的經典。無論如何,最后汰取的關鍵先生還是整體讀者。
不過,整體讀者向來不是清一色的純讀者,還需要進一步細分和定性。以現在的情形,除非人工智能介入,單靠人力沒法全面準確了解和細述各國不同歷史時期的每一類讀者;可以明確的是,越是大國的讀者,越是近期的讀者,成分越是復雜。就當下而言,我們的讀者大體可分為五類:1、大眾讀者;2、大學生讀者;3、專業讀者;4、文學機構負責人讀者;5、上層建筑讀者。顯然,此五類讀者的任何一類也不是清其一色的,還可以再分下去——但用“此五類”說明問題已經夠了。接下來,只要指出五類讀者各自的整體特征和彼此間的關系,就可以看出文學汰取和經典裁量的邏輯及復雜性。
——大眾讀者至少占整體讀者數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他們是文學傳播的主要對象和文學消費的基本主體。他們的生存與生活情況各不相同,智識和志趣千差萬異,通常因了原生的文學愛好與品味,加之個體的人生關切,自由順意地選讀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文學閱讀多么低俗,恰恰相反,他們原生的文學訴求與趣味正符合文學的發生;而且,由于他們是文學閱讀者乃至社會人群的絕對多數,讓文學保有了廣大的原生態——原生態才是文學性生長的溫床,才是文學性發熱放光的去處。只是,他們的原生訴求與趣味極容易朝兩個方向滑坡:一是趨向淺快愉悅的閱讀,更喜歡煽情離奇的“爽文”,從而為那些不太可能(或極少)成為經典的“流行文學”提供市場,并持續沉迷其中;二是“群眾”性,他們原生的文學訴求與趣味固然是良性因子,但因為缺乏眼界且美學根須單薄,往往更容易被意見導引,更容易跟風,更容易接受和捍衛,而有時許多荒謬的“導引”偏偏嗓門最為響亮。這類讀者從來沒有關于文學經典的直接裁量權,他們的趣味和選擇被專業人士用作文學汰取和經典裁量的參考因素,他們成了研究問題的對象。盡管“群眾”中不乏高人,但文學閱讀畢竟是無組織無紀律的。
——大學生讀者在這里專指文學專業的在校大學生(文學專業大學生畢業后一部分人將成為專業讀者;其他專業大學生和中小學學生的文學閱讀是業余的,姑且作為大眾讀者中的特殊群體)。這類讀者是專業讀者的新生代,他們進入了文學體制,但很大程度屬于被動接受文學或文學經典的群體。由于個人生活經歷和文學學習有限,他們在知識、情感與理性方面還處于空倉期,急于迎接或躺平等候文學作品的填充,多數人不會質疑、否定、反駁、抵制教科書里專業表述或羅列的經典,而甘愿(或者順應地)被填充、被傳播、被指導、被教化,并不知不覺地建立與之合拍的文學觀念。如此,教科書選用的文學表述與文學經典便成為了教育的百年大計和社會關注的熱點。假如某個時期的教科書里的表述不恰當,或陳舊,或偏頗,或忽略,或違背時宜,或結構不健全,就會導致文學文明的滯遲,就是對文明發展的虧欠;這種情況下,不排除出現個別另辟蹊徑的天才學生,不排除仍有少數眼界高遠的文學教師,但“個別”與“少數”于事無補,改變不了學生閱讀的基本面。這個“基本面”實際上成了文學經典的裁量者的種植園: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專業讀者包括文學專業研究生、文學(語文)教師、文學編輯、文學研究者、評論家和作家。這類讀者閱讀了大量文學作品,有(應該有)較完整的文學史與文學原理的知識,一般看重文學性,能自覺辨識和捍衛文學性。他們對文學的汰取和經典的裁量,其初心總是好的,眼光應當被尊重,取舍值得認真對待和討論。但是,專業人士中的一部分人的小專業知識與經驗特別容易生成窄化與保守的文學觀念。這些讀者作為裁量者的弱點伴隨他們的文學師承和個人職業生涯而來:由于專事細分的專業,往往容易淡漠或忽視專業之外的歷史、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文學、美學、哲學、人性以及社會生活演進,放棄大量新信息新知識,因而缺乏完備的思想資源和統籌裁量經典的睿見;相反,他們的專業知識和個人經驗在互證中不斷滋養發育,以至于個人化的文學觀念日趨頑強,不少人走在自己的窄道上,固執地發出反彈琵琶的聲調,其實對于評判和裁量經典不過是一家之言而已。部分人在閱讀選擇、知識傳授、選用稿件、評價作品、編修文學史、埋頭文學創作時,視野不是更寬闊,而是更獨特更褊狹,難免得珠失璣,有所偏廢。本來,這也是文學常態,觀點不同可以通過“百家爭鳴”尋求真理,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只可惜,很多時候“爭鳴”悄然“和諧”,文學專業開始在小把戲中“內卷”。實際上,多數專業讀者已把文學汰取與經典裁量權讓渡出去,受讓者是少數專業“更對口”、著作更多、地位更高、行走更廣的專家,他們成為了代表專業領域裁量經典的法定人士——這也是值得探討的。
——文學機構負責人讀者是有一定處置權的讀者。文學機構是指與文學相關的報刊、出版社、研究所、文學院(系)以及省市作家協會;這些機構的負責人,多數是文學專業的佼佼者,一般愿意尊重文學性并懷有文學使命,但他們的“位置與責任”決定他們同時還有非文學性的本職責任,比如完成某種文學任務和實現文學效益。按理,文學性并不天然排斥文學任務和效益,倒是可以與之互補相生并實現恰當的共贏;可惜實際情形復雜而不確定,氣氛總是緊張的,他們雖然沒有忘記文學性和文學使命,也不怠慢過往的經典(因為那些經典并不妨礙現實),但也有人寧愿規避文學汰取與經典裁量這種務虛的努力,全心投入眼下急務——如果在急務中得以兼顧“汰取”與“裁量”便是一箭雙雕。但一些機構在推出作品和鼓勵創作時,“急于近功”,搞成直奔主題,弄得文學走樣,看似業績不菲,實則無效;另一方面,一些實體機構在經營上“急于近利”,用心跟風,忽視藝術品質,雖偶有斬獲,實則耽誤文學和文學市場的未來,失去長遠效益。而一旦急功近利,接下來的動作便是話題噱頭、宣傳炒作、打榜頒獎,硬生生在上級和讀者的心目中快速整出幾部大作或暢銷書,然后,挑選其中的作品“落實”到選集和文學報告里。他們當然期待“急功近利”碰巧催生出佳作,而開明的負責人讀者一直在期待中。
——上層建筑讀者代表社會制度的文學意志與文學取向。所有國家都有上層建筑,上層建筑自然是閱讀和關注文學的,文學作為上層建筑之意識形態范疇,中外古今歷來高度重視。我國目前的文藝(文學)方向是“二為”: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社會主義文藝,從根本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并倡導“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學。我們還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毛澤東同志推介《紅樓夢》,偏愛李賀李商隱,是一位創作了經典詩詞的杰出詩人。一般而言,國家的文學方針與理念是基于經濟基礎的意識形態,必然成為文學汰取和經典裁量的總尺度。當然,上層建筑通常并不直接對文學經典做出具體裁定。許多國家對文學藝術采取“自由創作”“主題倡導”加“負面清單”的制度機制。我們的文學是有組織的事業,關鍵在于文學機構對于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根據歷史的經驗教訓,要特別預防個別人和中間環節把經念歪,并及時糾偏,從而確保建構真正滿足人民精神需求和人類文明需要的文學經典體系。
以上就是整體讀者的基本情形。
麻煩在于:由于五類讀者的交織與疊加,亦即各種文學取向與選擇的交織與疊加,在社會面,實際存在著大量“小眾經典”,其總量幾乎是一個無底數;如果對這個“無底數”不及時做進一步汰取和裁量,后果可能是經典失范和經典喪失———總不能人人都說我喜歡的就是經典吧。可是,文學經典既不能由強人或高人來指定,也不適合采用“定額”加“普選”的方式來解決:文學畢竟是大眾和歷史的,即便強人和高人指定的經典,也難免經典的文學性不會落空,歷史一直在證明指定的經典往往被大眾和歷史遺棄,或者被糾正——而真正的高人也不會把自己的選擇強加于人;如若“普選”,其結果則多半是流行的平庸之作占領“定額”,因為它們的讀者總是人數更多。
何以讓文學汰存與經典裁量符合文學文明與人類文明?
日常里,這個疑難似乎并不是一個尖銳的問題。一方面,因為文學汰存與經典裁量是長線的事兒,是整體讀者的志趣,沒有個體必須為之擔責;從根本上講,任何個人都不具有擔責的資格。另一方面,文學受到社會的重視與管理,不是荒原上任意生長或自生自滅的花草,也不會像物質商品那樣在市場上自由流通,社會對文學汰取與經典裁量安排了通路與程序,包括發表、出版、發行、再版、評價、傳播、研討、選編、修史等環節,一切皆由專業機構中的專業人士與負責人來操作和掌控;而實際上,掌控者得以在專業精神與位置責任之間飄逸、堅守、溝通、迎合、兼顧,回應各種顯在訴求和潛在需求……做出沒有剛性責任的汰取與裁定,即便弄過了,也沒什么職責大事,看起來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正常運行。
但社會卻是有態度的,普通讀者對經典這回事要么無感要么不滿。無感是因為文學消費不是剛需;不滿,則因為文學也是實用的,比如對語文范文和課外閱讀文本的選定不予認同。事實上,社會有理由對文學汰取與經典裁量的操作者和掌控者寄予期待。而且,人們不會忘記歷史教訓,比如1966年至1976年期間,少數人別有用心的文學汰取與裁定得逞后,給文學和社會帶來了巨大災難;同時,還有經典再發現的可能,比如《金瓶梅》。
現在,社會平穩發展,互聯網發達,網上的文學發表與閱讀方興未艾,數量遠超紙媒時代,雖然網絡文學良莠不齊,但畢竟是“齊放”局面,且不時彌補線下“躺平”的“爭鳴”,漸顯文學民主之勢;如此,網上文學為文學觀察帶來了直接而廣闊的視域,有利于讀者彼此探望、發現、咨詢和溝通,從資訊利用上講,可以幫助文學汰取與經典裁量,可以支持或矯正既有的經典體系。但是,如果海量信息不能加以科學利用,文學的汰取與裁量就顯得更加急迫,難度也更大。
近年來,“經典化”的呼吁頻率很高,正反映了現實的焦慮。但是經典化實在不應當是一項急于求成的工程。縱觀文學史,經典化不過是文學發展過程中的“集體無意識”的追求。現下,文學作品從編輯到發表,到廣告推廣(如訪談、見面會),到評論研討,再到打榜、排名、評獎等等,其中除了功利部分,也有經典化誠意,只要實事求是、適可而止也算合理,也會有所作為;只是,實際中,盡管用盡了好詞,打了榜,頒了獎,卻不能將作品封為經典,很多作品很快就會被讀者讀垮。以大概率論,一部不錯的作品自誕生起,大約要過去七八十年后方能評定高下和裁量其是否屬于經典;因為,七八十年后至少是第四代讀者,屆時的汰取與裁量將消除諸多干預與牽扯。總之,經典是“化”不了的,不必為眼下畫餅充饑或畫梅止渴。
所以,經典的裁量權還得交給時間。
透過時間,可以看見中外文學經典逶迤而來的陣容。以中國“四大名著”為例,起初在明朝時叫“四大奇書”,指《水滸》《西游記》《三國演義》《金瓶梅》,待《紅樓夢》問世,替換了《金瓶梅》;由明至清,并無“四大名著”之說,一度推舉“六大名著”,即后期的“四大奇書”加《聊齋志異》《儒林外史》;再后來,淘汰《聊》《儒》,才有跟“四大奇書”書同而名不同的“四大名著”;然而,以今天的眼光看,從“四大”和“六大”中踢出的《金》《聊》《儒》也是經典。而在這段壓縮的表述中,經典的裁量已歷經了幾百年的時間。時間的表情是鐵面無私,它永不停頓,一直在吸納、消化、積淀、汰洗世間的全部事物與意趣,確認真正的文學性:時間讓偉大作品澄出經典品質,比如《紅與黑》《包法利夫人》;時間持續坐實經典的魅力,比《堂吉訶德》與《浮士德》;時間也把名噪一時的大作打入冷宮,比如薩德的《貞女的厄運》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時間是各類讀者的磨合劑與協調師,也讓讀者一茬接一茬進步——只有時間,才能最后給文學作品定案和翻案。
但時間的深刻性在文學的背后。隨著時間流走,生活前行,科技進步,文明增長,社會發展,自然發聲,觀念更新,人類的生產生活發生變化……文學在不斷回應生活時,也不斷改變自身和拓展、修正、改變、顛覆讀者的審美取向與眼光,尤其是——必然呼喚和催生文學汰取與經典裁量的新尺度。與此同時,文學文本對于閱讀而言已經萬倍過剩,眼下,任何人工的文學汰取和經典裁量都難免有遺珠之憾,而與之相關的爭議越來越多卻越來越讓人不以為意。這么看,時間也給文學汰存和經典裁量帶來了兩個破壞因素:一是美學與尺度的波動,一是數量過大的災難。時間竟是時間的掘墓者。
令人慌亂的是,人類已經在時間里聽到人工智能的腳步,當人工智能時代——特別是人工智能超越人類智能的時代——到來后,機器人可以把所有事情(包括文學的汰取)辦得更好,那時,人類生活與人類文明是什么樣子?文學的生產與閱讀是什么樣子?現在的預料多半無效。可以肯定的,是人類面臨著顛覆性的未來——而且未來并不遙遠。我們現在對經典的裁定,依憑的仍是傳統經驗,很像是在既有格局的最后時刻辦一場華麗夜宴,并試圖樹立告別的豐碑。
一切都將改變。世界變了,文學經典會不變嗎?
那么,也就是說,在文明的現階段,時間正在破壞時間;在巨變的時刻,老時間對文學的汰取和經典的裁量也越來越不靠譜,越來越失靈,越來越容易把讀者帶上紊亂的節奏。這真是令人憂傷。然而,即使人工智能超人類智能的時代到來,也不意味著文學的終極滅絕;只要人在,人就需要文學,文學就需要文學性,文學性仍將決定文學的高下。既如此,要緊的是從沮喪中振作起來,擁抱時代生活,滿懷熱情地感受現實,然后繼續檢視人類文明與文學文明的空白,不斷——試圖——以經典去填補它。積極現實主義是面對未來的唯一可選的姿態。至于到了人工智能超人類智能的時代,那也是人類的幸運,人類可以跟機器人合謀,通過人工智能及時建構文學經典的體系。
還能怎么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