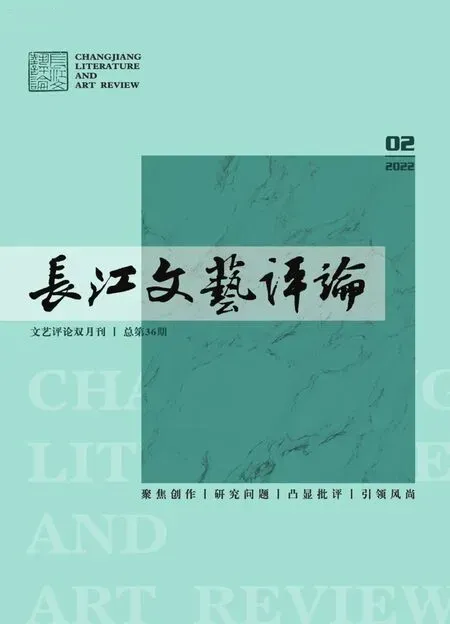舉重若輕,哭笑為戲
——觀武漢紅色曲藝劇《三教街四十一號》
◆楊曉雪
《三教街四十一號》是由武漢說唱團的曲藝家們創演的一部紅色曲藝劇,劇名來自于1927年中共八七會議的會址——武漢“三教街四十一號”。在戲劇舞臺上,很多經典的戲劇都是直接以地名命名的,比如《茶館》《龍須溝》《小井胡同》《窩頭會館》《桑樹坪紀事》等等,而故事往往也就在這一地理空間里發生發展。但《三教街四十一號》顯然是一部“非典型”的劇作,全劇從始至終,沒有一個場次、一個情節甚至一分鐘是真正發生在三教街四十一號的。三教街四十一號在劇中不是物質的、客觀的舞臺空間,而更多是一種符號和隱喻,是創作者為觀眾營造出的情感空間和想像中的心理空間,也是整部劇作所傳達出的極具象征意義的、神圣的詩意空間。與之相對應的是,整部劇講述的故事都發生在四十一號的外圍和周邊,在碼頭、茶館,在街頭、巷尾,在市井、民間。《漢書·藝文志》中說道:“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頭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街頭巷尾”,正是曲藝藝術的生存空間。而這種舞臺空間與劇名空間的獨特錯位,折射出的也正是該劇作為一部“曲藝劇”與其他類型的“眾劇”所截然不同之處。這也是該劇的創作者從曲藝本身的屬性、特點和優長出發所作出的獨具匠心的設計和最務實的選擇,從而也把一部極具特色、感人至深的優秀作品呈現在觀眾面前,給觀眾以別開生面的審美體驗。
關于曲藝劇這一藝術形式,一直以來在曲藝界有很多討論。特別是在曲藝理論界,對于曲藝劇姓“劇”還是姓“曲”、是否背離曲藝本體、是否有創新價值等問題,不乏爭議和否定的聲音。但從實踐層面來看,曲藝劇并不是新鮮事物。新中國成立前,常氏兄弟的啟明茶社就排演相聲劇以吸引觀眾。20世紀60年代和80年代,以陳涌泉為代表的北京曲藝團的曲藝工作者們,就從上海滑稽中汲取養分,在不同時段分別排演了一系列化裝相聲和相聲劇。臺灣賴聲川導演的“那一夜,我們說相聲”系列更是在海峽兩岸產生了廣泛影響。直至新世紀以來,全國各地曲藝團體紛紛創作推出了一大批曲藝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中國廣播藝術團說唱團的《明春曲》、濟南曲藝團的《泉城人家》、河南曲藝團的《老湯》《老街》、上海評彈團的《林徽因》以及武漢說唱團的《信了你的邪》《一槍拍案驚奇》《非常勿擾》《杠上開花》等一系列作品。無論對曲藝劇持怎樣的看法和態度,不可否認的是,曲藝劇是時代變化和曲藝實踐的產物。特別是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對整個文藝業態生態帶來猛烈沖擊,新的文藝形態的層出不窮,不同藝術形式的深度滲透、跨界融合以及各藝術門類邊界間的日益模糊,我們對藝術的變革也必然隨之更易接受,對新的藝術形態的價值也有了在更廣層面、更具包容性的理解和認識。當然,對曲藝劇這一曲藝形態的延展和外溢,筆者必須承認,藝術的創新應當是結果,而非目的;創新是創作者的落腳點,而不是出發點;創新是手段途徑方法,而決不是“為了創新而創新”。這是一切藝術創新的初心,也是其成功的關鍵。由此,我們看《三教街四十一號》,也就有了全面的感受和體悟。
一、舉重若輕,以曲藝的方式經濟地兼顧“史才”與“詩筆”
《三教街四十一號》是一部紅色劇作,關注的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重要轉折意義的一個重大事件——八七會議,就題材而言,其分量不言而喻。一般認為,曲藝作為“小技”,與縱橫捭闔的宏大敘事和波瀾壯闊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相距甚遠,是不適合、不兼容的。但我們如果回顧曲藝的源流就會發現,曲藝雖小且大,它雖然不同于廟堂的高文大冊,但“說書唱戲勸人方”,曲藝是以其獨特的方式傳承著“道之以德”的高臺教化傳統。曲藝作為民族的獨特敘事藝術,“講史”談天說地、談古論今,歷數盛衰、爭戰、興亡,以文為史、以史為文成為其辯證統一的鮮明特征。但曲藝的“史才”不是一般的宏大敘事,所謂“不隔語、不隔音,更要緊的是不隔心”,它是用“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通透、用“人、情、理”的可親可觸,把所承載、需要傳達的價值觀與其所處時代觀眾的當下旨趣、思想情感、審美理想緊密結合起來的。《三教街四十一號》題材雖大,但它“講史”是克制的、微觀的。劇中的“人”大多是掙扎在社會底層的老百姓,是小人物,主人公一家是舊社會地位低下的曲藝藝人,全劇最大的“官”也不過是個巡警隊長;劇中的“情”都是凡人之情,男主楚十五是一名人力車夫,與妻子、地下工作者梅梅夫妻情深,楚家的父子、父女之情,茶館老板對楚家的照拂之情,等等,都是普通人的喜怒哀樂、愛恨情仇,顯得平常卻不失真摯;劇中的“理”是合乎常理的,無論是舊社會人分“三六九等”的無奈現實、楚月對“當家做主”的美好向往,甚至是對“槍桿子出政權”這一重大主題的深刻隱喻,都是通過符合觀眾認知接受習慣和我們民族心理的方式,用生動的語言、生活化的細節,細膩、委婉地傳遞給了觀眾。所謂“美由心裁”,《三教街四十一號》的主人公他們雖然品質高尚,但行為方式卻不是“英雄化”的,楚十五有著小聰明、時常插科打諢,梅梅街頭賣煙、做著針線活,他們反而是極其世俗普通的,但正是這種對崇高感的削弱,打動了普通觀眾的心,增強了心理上的親切感,從而連接觀眾、感染觀眾、影響觀眾。曲藝劇正是這樣用最平易的、最經濟的藝術表現手段與觀眾“通心”,實現了現實之美和精神之美的完美融合,可以說是一部直觀形象的“歷史、生活的教科書”。
二、哭笑為戲,在喜劇與正劇的交叉點上取得平衡
戲劇理論家陳瘦竹說過:“笑是人們感情的自然流露,是一種美學評價。”曲藝自誕生伊始就是自娛且娛人的,喜劇意識和幽默取向是絕大多數曲種與生俱來的突出特征,深植在曲藝人的靈魂深處。一般而言,因曲藝風格的輕松性、旨趣的娛樂性,大多數曲藝劇都是喜劇,演員往往竭盡手段拋出“包袱”,給觀眾以歡樂愉悅的欣賞和審美體驗。但《三教街四十一號》無疑是不一樣的,其題材的主題性、特殊性,已經先天決定了它不是一部典型意義上的喜劇,但它又不同于其他同類題材嚴肅、沉重的正劇,而是一部既充滿喜劇元素、又蘊含歷史文化內涵,似乎是介乎于喜劇與正劇之間的一部另類之作。但如果回到曲藝的原初,這種“另類”實屬平常,它正是對曲藝本質和傳統的一種回歸、一種傳承。柏拉圖說過:“就是看喜劇時也是悲喜交集。”京劇藝術家蓋叫天說過:“可為了悲,也不可從頭哭到尾,有時笑比悲還悲呢!”曲藝的藝術觀念和審美法則中一直蘊藏著寓莊于諧、笑中帶淚的藝術辯證法,許多曲種中悲劇喜唱、寓哭于笑的高妙藝術手法往往能取得非比尋常甚至帶有哲理性的藝術效果。《三教街四十一號》中的喜劇元素是創作者的支點,創作者以喜劇元素設計情節,鋪排情境,賦予人物豐富多彩的性格;但同時又回到歷史現場,在宏大時代背景下構建總體框架,以正大氣象發人深省、令人深思,賦予作品深刻的社會意義、思想力量和審美理想。魯迅說:“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毀滅了給人來看”,他又說:“喜劇是將那些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三教街四十一號》一部作品同時做到了這兩點:楚月作為劇中最美好的化身,在黑暗的社會壓迫中選擇結束年輕的生命,“有價值”的美被無情毀壞;隊長二麻則是反面的典型,他跋扈、丑陋、自私、無恥,這種“無價值”的丑在劇中被直接撕破。但劇中對“丑”的揭露不是粗陋、直接的,不是表面的搞笑“噱頭”,而是用夸張、變形等滑稽類曲種常用的方式,賦予人物以獨特的語言、鮮明的個性、典型的形象,美丑對比,使丑反襯出美,從而讓觀眾發出由衷而會心的笑聲。特別是全劇最重頭的茶館拖住二麻的一場戲中,二麻的兩位太太爭寵的鬧劇一度讓全劇的詼諧熱鬧達到頂點,但緊接著楚月為反抗二麻的霸占、斷然自盡的情節幾乎無縫對接、急轉直下,觀眾的笑聲戛然而止,喜劇的背后隱藏的是最大的悲劇。該劇“以樂景寫哀”,鬧劇場面只是社會悲劇的一隅;“以哀景寫樂”,犧牲換來的是美好的未來。正如柳宗元所說的“嬉笑之怒,過于裂眥;長歌之哀,過于痛哭”,笑的力量不僅給予觀眾強大情感沖擊力和感染力,也啟迪觀眾心靈,讓觀眾在輕松之余進行理性的思考。
三、技藝并重,把湖北曲藝的藝術特色轉化為時空敘事的有效手段
曲藝之藝是技藝并重、形式與內容的完美統一。所謂“無技不成藝”,曲藝的技巧、技法、規律這些“看家之技”是曲藝受到廣泛歡迎的重要原因,也是曲藝藝術之美的根本。因此,曲藝劇在演劇的同時,不能少了曲藝味,離不開曲藝“技”。《三教街四十一號》在這一點上充分發揮了湖北曲藝的獨特優勢,劇中主人公被設定為曲藝世家,湖北大鼓、湖北小曲、評書、相聲等曲種在劇中占據很大比重,不僅僅是一般的敘事手段,甚至在關鍵劇情上起到了畫龍點睛、提神醒腦的作用。比如,說書人被用來作為開場、串場的媒介,這正是發揮了她作為全知全能的形象和在講述故事時的客觀地位,以敘述語言涵蓋了戲劇中的“旁白”“潛臺詞”,起到了統領全劇的作用。飾演楚十五的演員多次用相聲的手法來詮釋角色,包括報地名、報菜名,前后呼應,特別是一段考驗功力的《八扇屏》中的經典貫口“莽撞人”更是成為全劇亮點之一。“一方水土一方人,還是鄉曲最贏人”,曲藝離不開方言,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載體,“鄉音鄉情”是曲藝最重要的美學特質和獨特魅力。劇中反復吟唱的湖北小曲代表作《小女婿》,是對和平年代雖凡俗但美好的生活的向往;全劇最高潮處楚父唱出的湖北大鼓《武松打虎》,則是苦難生活中發出的吶喊,也是受壓迫的人民群眾覺醒反抗的吼聲,令人震撼。劇中湖北方言有很多種,不同的人物被賦予不同的地方語言,也鮮明體現出人物的形象與性格,如全劇開篇唱出的“漢口人有膽有量性情豪爽,一搭兩響絕不鬧醒簧”,充分反映出這片土地的歷史文化內涵、自然人文特色和及獨特的風土人情。曲藝的“跳進跳出”“說法中現身”的藝術特征,使觀眾容易在觀劇時產生某種與劇情的距離感和跳脫感,但曲藝與觀眾面對面交流的方式以及方言的運用,又讓觀眾產生了另外的沉浸感和參與感,這也許正是曲藝劇的獨特魅力所在。
曲藝是傳統的藝術,也是隨著時代不斷變化的一門藝術。傳統是有慣性、惰性的,有其封閉、保守的一面,但也有著存在的必然合理性、延續性。曲藝劇在繼承曲藝傳統的基礎上因時代而生,因時代而變,不斷呈現出新的面貌。《三教街四十一號》在紅色題材的表現上進行了有益的嘗試,當然它目前還不是完美的、還有不少可完善的地方,比如評書敘事手段應更精細一些、對劇情的交代需要更清楚,結尾的“穿越”設計過“實”、過“滿”,應該虛實結合、適當留白,以大寫意的手法突出今昔對比,等等。但筆者相信,《三教街四十一號》這部劇,定能為當下曲藝劇的發展帶來新的借鑒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