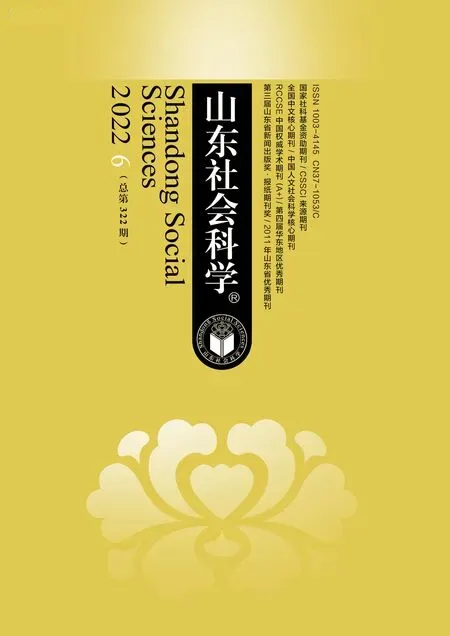近代中國黑熱病防治述論(1904—1937年)
徐 暢 夏 坤
(山東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黑熱病(Kala-Azar),學名內臟利什曼病,又稱達姆達姆熱,系熱帶性脾大或西爾卡里病,中國民間有痞塊病、大肚子病等俗稱。黑熱病是由杜氏利什曼原蟲的病原體經白蛉傳播后寄生于人體感染所致,患者常出現肝脾腫大、發熱、腹瀉、消瘦、貧血、皮膚發黑、腹部隆起等病狀及并發癥,如不治療,兩年內病死率高達75%—95%。中國是世界黑熱病主要流行區之一,晚清時期即已出現疑似病例,光緒年間成書的《乳石山房醫案》中有“年來疫痞流行”“重必齦爛,劇則腹大,每多壞癥”的記載。民國時期,黑熱病的傳播范圍更廣,病患數量日增,蘇魯豫皖等省疫情尤為嚴重。
在積弱積貧的時代背景下,黑熱病防治工作呈現出教會醫院首倡、政府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民間社會參與力度漸趨增強等特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國衛生防疫的演化路徑。鑒于黑熱病既有研究成果或局限于某一地區,或著眼于某一時段,整體性討論不足,本文以1904年中國首例黑熱病患者確診至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導致防治工作暫時中斷為時間維度,以疫情嚴重的蘇魯豫皖地區為空間維度,探討防治工作中的各方參與及其成效,以期管窺近代中國衛生防疫現代化的歷程。
一、首倡于西:近代中國黑熱病防治的西方因素
盡管中國黑熱病的疑似病例出現較早,但作為世界性流行病,起初的研究則來自西方國家。1903年,英國醫生威廉·利什曼(William Leishman)和查爾斯·多諾萬(Charles Donovan)首次在病患體內發現了致病的黑熱病病原體,黑熱病診斷自此具備科學依據。1904年,一名曾參加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德國士兵被確診為黑熱病,這是中國首個確診病例,相關防治工作即由此發端。但是,清末至北洋政府時期,由于衛生制度不健全,醫療水平較低,政府重視不夠,防治工作由具有一定基礎的教會醫院主導。
黑熱病病原體雖被發現,多地教會醫院也已開始診療,但因社會各界并未充分重視,所以發現的病例不多,到1911年,全國見諸報道者僅8例。事實上由于數據來自各地教會醫院收治的病患統計,缺乏全面的流行病學調查,所以這一數據無法反映黑熱病流行的實際情況。
1911年,考慮到當地黑熱病病例增多,尤其是出現大量疑似病例,美北長老會創建的安徽懷遠民望醫院開始向各地教會醫院發放調查問卷,首次進行全國范圍內的黑熱病調查。通過回收的70份問卷,民望醫院院長柯德仁(Samuel Cochran)發現,全國各地普遍出現臨床表現疑似黑熱病的病例,安徽、山東和江蘇確診病例尤多,僅民望醫院1912年收治的確診和疑似病例就達83例。柯德仁從調查結果出發并結合診療實踐,認為黑熱病在安徽宿州、潁州、太和等地流行較盛,蘇魯等地區同樣應當予以關注。民望醫院的調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黑熱病的流行情況,但由于民眾認識不足,對教會醫院也缺乏了解和信任,就診者有限,因此該調查數據仍無法全面反映黑熱病流行的情況。
民望醫院的調查揭示了黑熱病的嚴重性,然而除部分教會醫院診療力度有所加強外,并未引起政府和民間的重視。各方的忽視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黑熱病蔓延。1920年2月,在北平舉行的中華博醫會大會上,同樣由美北長老會建立的河北保定思羅醫院代表在題為《華北黑熱病》的報告中強調,華北地區的黑熱病流行嚴重,僅1918至1920年該醫院就收治了病患35人。1922年3月,為明確黑熱病的流行情況和傳播方式,思羅醫院和北平協和醫學院聯合對病患聚居的河北定縣進行了實地考察。結果顯示,黑熱病在當地頗為流行,在調查的9個村落中6個村落有黑熱病;在疫區中心沙流村,1922年前的4年間,每12個家庭就有1人確診。此次考察雖未取得關于黑熱病病理研究的實質性成果,但一定程度上明確了黑熱病的傳染強度,從而為下一步開展大規模調查奠定了基礎。
1922年12月,北平協和醫學院開始向更多教會醫院發放調查問卷,以期進一步明確全國黑熱病的流行情況。調查結果顯示,黑熱病患者數量在持續增長。北平協和醫院6年收治病患100人,濟南齊魯醫院2年收治116人,徐州基督醫院更是在1年半左右即收治297人。此外,陜西、甘肅和遼寧等地也發現有確診病例。不難看出,較之民望醫院1911年的調查,此時黑熱病的蔓延區域已明顯擴大,傳統流行區域的疫情愈加嚴重。據徐州基督醫院反饋,汴塘(Pien Tang)診所收治的125名病患中,患黑熱病的有25名;徐州東南的丁莊(Ting Chwang)甚至每2名兒童就有1名患有黑熱病。協和醫學院的調查不僅豐富了人們對國內黑熱病流行情況的認知,而且還推動了對黑熱病患者年齡發病率、體溫曲線和血液分析等病理問題的初步研究。
1923年,美國洛克菲勒中華醫學基金會資助協和醫學院成立了黑熱病實地調查組,考察疫情嚴重的徐州地區。在為期4年的調查中,工作人員逐戶調查了駱駝山和獅子山2個村莊,自1923至1926年,發現獅子山700位居民中有黑熱病患者68人,駱駝山900位居民中有黑熱病患者44人。與此同時,調查組還結合實際,研討了黑熱病的流行周期、季節發病率、城鄉發病率、村落結構與疫情的關系等問題,并與印度的黑熱病進行了比較。調查組初步分析了黑熱病的傳播途徑,確定白蛉為傳染黑熱病的高度疑似病媒。協和醫學院調查組的研究不僅使國內對黑熱病蔓延態勢的認識有所深化,而且從病理層面初步鎖定了傳播媒介,是防治工作的一大突破。
在協和醫學院赴徐州調查的同時,1925年齊魯大學與英國皇家熱帶病學會合作組織了黑熱病調查團,實地考察山東疫情。山東是黑熱病傳播較為嚴重的地區,自1920至1926年,僅齊魯醫院即診斷黑熱病患者301人,分布于36個縣。與協和醫學院的調查類似,齊魯大學調查團一方面利用醫院收治的病患記錄分析和總結病患的性別、年齡、季節發病率和持續時間等信息,另一方面實地考察黑熱病一度流行的位于山東東北的村莊陳李家(Chen Li Chia),結果發現224戶有黑熱病患者81人。此外,齊魯大學調查團還通過對黑熱病血清學、原蟲培養物和白蛉物種進行一系列實驗,證明中華白蛉是黑熱病傳播最為重要的病媒,從而驗證了協和醫學院調查組的結論。
縱覽早期的黑熱病防治,無論是病患診治、流行范圍調查還是病理分析,都由教會醫院主導。教會醫院發起的流行病學調查,大致明確了疫情流行區域;實地調查初步查明了傳染媒介,從病理層面為后續的防治工作打下了基礎。在此期間,教會醫院還持續為病患提供治療,減輕患者痛苦。應當承認教會醫院在早期黑熱病防治工作中發揮的作用,但是作為一項社會治理工作,缺乏政府的支持,無法形成有效的防控體系,無疑會影響防治效率,實際成效有限,所以僅靠教會醫院,無法有效防控已成規模的黑熱病。
二、西鳴東應:近代中國黑熱病防治的政府介入
近代中國黑熱病防治最初為西人主導,部分由于在華西醫與本土醫界相對疏離,部分則與清末民初政局混亂、衛生防疫不發達有關。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面對黑熱病快速蔓延的態勢,如何建構衛生防疫體系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于是各級政府逐漸主導了防治工作。
南京國民政府名義上統一全國、暫時結束軍閥混戰局面后,開始強化衛生防疫事業建設。1928年,內政部頒布《傳染病預防條例》,為傳染病防治提供了法律依據。1932年,內政部衛生署和全國經濟委員會中央衛生設施實驗處(后改為衛生實驗處)先后成立,為建設統一的衛生防疫體系提供了機構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衛生實驗處專設有寄生蟲學系,致力于寄生蟲病調查及防治研究,以寄生蟲為傳播媒介的黑熱病即為其關注重點之一。總之,國家政策和機構的頂層建構為政府主導黑熱病防治提供了保障。
1930年代蘇魯豫皖頻發水災,黑熱病疫情爆發,是促使政府介入的直接原因。1931年,江淮流域發生嚴重水災,據國民政府主計處的調查,蘇魯豫皖等省損失最為嚴重,受災超過858萬戶,占農戶總量的26%。水災為黑熱病的傳播提供了溫床:第一,水災過后的潮濕環境間接促成病媒中華白蛉的生存與繁殖;第二,災民營養不良、體質變差,抵抗疾病能力減弱;第三,災民為謀生計而遷徙流動,傳播風險隨之增加。所以,洪水退去后,黑熱病迅速爆發。據不完全統計,自1931至1933年,僅清江浦、宿遷、徐州、懷遠四地教會醫院收治的黑熱病患者即達10537人,山東、河南等地醫院收治的病患數量同樣出現激增。到1934年,蘇北和皖北地區病患已達18萬之多。此次疫情尚未平息,1935年黃河又在魯南決口,水流南溢蘇北,淹沒農地800余萬畝,造成災民100余萬。水災之后,蘇北黑熱病“流行之盛,傳染之酷,區域之廣,幾如星火之燎原”,甚至造成“一家數病者有之,舉家全斃者有之”的慘象。
教會醫院的早期工作給國民政府防治黑熱病打下了一定基礎。首先,為政府掌握疫情提供了依據。為了解疫情實況,1934年1月,衛生署與衛生實驗處合作組成調查組,重點走訪了對蘇皖北部黑熱病防治有一定工作基礎的清江浦仁慈醫院、宿遷仁濟醫院、徐州基督醫院和懷遠民望醫院,并根據病患數量確認蘇北疫情最重、皖北次之。其次,對治療病患藥物的探究與使用便利了政府救治。1920年代懷遠民望醫院、清江浦仁慈醫院使用療效更好的有機銻劑,不僅縮短了療程,而且治愈率提高至95%。再次,推動了政府防治方案的制訂。衛生署實地考察蘇北疫情時,北平協和醫院派遣黑熱病專家李宗恩同行,輔助議定各項方案。衛生署與衛生實驗處綜合考慮疫情、治安及交通等因素,決定在江蘇淮陰清江浦設立工作隊。1934年4月,工作隊正式成立,此為國民政府首次大規模參與黑熱病防治的開端。
清江浦黑熱病工作隊一面治療病患,一面尋找病因。首先,每周一、三、五上午開設門診,采用銻劑注射治療,由于治療“概不收費”,求診者數量眾多,“門未啟而門庭已若市”。自1934年6月至1935年底,工作隊診療病患達31290人次,大大減輕了周邊民眾的病痛。其次,實地調研,在詳細調查淮陰、泗陽等地10個村莊后,工作隊在淮陰王石鼓莊病患家中收集的中華白蛉中發現了天然感染的黑熱病病原蟲,從而徹底證實了中華白蛉確為黑熱病傳播的重要病媒,為后期防治工作的完善提供了重要參考。最后,針對社會大眾防疫知識和衛生意識不足的情況,舉辦防疫成果展覽會,宣講疾病預防和公共衛生知識,增進民眾對黑熱病的認知,提升公共衛生意識。
清江浦黑熱病工作隊取得一定成效后,國民政府又采取其他措施,以進一步鞏固和擴大防治成果。第一,1935年6月,衛生實驗處派員赴黑熱病控制較好的印度學習防治經驗,深入了解黑熱病歷史、銻劑治療和白蛉防治等問題。第二,為明確各地疫情、推動防疫工作,1936年10月,國民政府派遣清江浦黑熱病工作隊隊長孫志戎等人赴山東、河南考察,在治療病患的同時宣傳防治經驗。第三,為培養黑熱病防治人才,1936年10月,衛生署發布熱帶病學講習班簡章,在全國挑選10名醫校畢業生,專門培訓熱帶病學、實用寄生蟲學、細菌學及流行病學等課程內容,并實地考察清江浦等疫病流行地區。國民政府采取的上述舉措,提升了防治的科學水平,培養了人才,為進一步防治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國民政府主導防治工作的同時,江蘇省政府也積極參與其事。1935年1月,江蘇省政府派出由省立醫政學院及民政廳人員組成的蘇北黑熱病調查團,調查蘇北黑熱病的傳染原因、蔓延區域和病患數目。調查發現,全省黑熱病疫情極為嚴重,僅寶應、淮安、淮陰、漣水、泗陽和宿遷等6縣患者即有六七萬人。面對迫在眉睫的防治任務,江蘇省政府一面向全國經濟委員會請求撥發治療經費,一面通過醫政學院培訓農村初級醫療人員。1936年,江蘇省政府成立淮陰區黑熱病防治隊,下設10個分隊,每分隊設5個防治站,在蘇北進行防疫治療。淮陰區黑熱病防治隊最初將診療費分為“普通費”和“半施費”兩類,前者收費5元,后者針對貧民,收費減半。在治療過程中,防治隊發現多數病患家庭貧困,能夠負擔“普通費”者寥寥無幾,大部分病患深感“半施費”亦甚高昂。為降低治療門檻,防治隊設法推廣貧民貸診治療,由保甲長或商戶為病患擔保借貸治療費用,在接診6個月后償還,擴大了施治范圍。在江蘇省政府的支持下,淮陰區黑熱病防治隊工作成效顯著,截至1937年7月,已治愈2500余人,患者死亡率不足4%。除成立黑熱病防治隊外,江蘇省政府還推動所屬各縣建立縣立醫院,施診地方患者,并于1937年6月設立江蘇省地方病第一研究所,繼續加強對黑熱病的防治研究。
山東、安徽等省雖未設立專業的黑熱病工作隊,但在江蘇省政府影響下,也不同程度地開展了防治工作。在安徽,懷遠民望醫院1937年1月至4月診治病患2700余人,政府在疫情嚴重的宿縣和壽縣設立黑熱病專門診所和病房,積極治療病患,控制疫情傳播。在山東,省立醫院亦積極派員調查各地疫情,救治病患。為加強疫情聯動防控,1937年6月,江蘇省政府組織召開了蘇魯豫皖四省黑熱病聯防會議,號召各省設立黑熱病工作機關,建立統一協調機制。但因全面抗戰不久爆發,該計劃未及實施即告流產。
1930年代初黑熱病疫情爆發后,國民政府和江蘇省政府相繼設立工作隊,通過財政支持、設立機構、配備人員等措施,確保了以救治病患為中心的防治工作不斷推進。在此期間,教會醫院雖然持續救治病患,但是政府通過行政力量強勢介入,主導了防治工作。總之,政府主導、教會醫院參與的防治體系,較之僅由教會醫院開展的黑熱病防治,主次更分明,力量更多元,成效也更顯著。
三、浸乎其下:近代中國黑熱病防治的社會參與
1930年代黑熱病防治成效較為顯著,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國家衛生防疫體系取得了積極進展,但是政府主導并非黑熱病防治工作的全部面相。一方面,“弱勢獨裁”的國民政府缺乏覆蓋基層社會的能力,也無法建成完整的衛生防疫體系,自上而下的防治效果終究有限;另一方面,作為現代化的重要表征之一,公民社會發展壯大是近代中國社會進步的表現,面對急劇發展的黑熱病疫情,實力不斷增長的社會力量有意愿也有能力參與其中。1930年代黑熱病疫情爆發初期,江蘇省政府即召集地方士紳、醫界共商救治辦法。隨著疫病蔓延,衛生署倡議“海內外慈善家捐資救濟”,“官民一致,共圖挽救”。因此,在政府主導防治的同時,包括中西醫、地方紳商和社會團體等在內的各界力量開始不同程度地響應政府號召,投身黑熱病防治。
早在1930年代初水災導致黑熱病蔓延時,中醫群體對此即有所關注。聲名卓著的上海國醫公會積極聯絡中央國醫館及蘇北地區中醫了解疫情,神州國醫學會亦派員進行調查,并提出防治建議。隨著疫病肆虐,各地中醫紛紛參與救治。在疫情嚴重的蘇北,淮陰中醫駱筱峰從中醫醫理出發,建議將“黑熱病”改名為更切合病情的“疫痞”,并積極研制疫痞煮黃丸、疫痞絳礬丸等藥物。淮陰國醫公會沙亦恕建議江蘇省政府充分利用中醫群體力量,建立疫痞醫院。西醫主要是將政府采用的治療措施行于當地。畢業于南通醫校的宿遷醫生沈之軍,采用新斯銻波霜注射治療救治病患。洋河王昆山等醫生下鄉流動治療,每逢集期診治病患三四十人,有效緩解了病患就診不便的難題。與此同時,西醫還建議設立巡回治療隊、開設研究班,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總之,中西醫從業人員從自身醫學知識出發,或借助傳統方法,或采用現代醫學手段,救治病患,獻計獻策,發揮了各自的作用。
較之掌握專業醫學知識的中西醫生,民間紳商則著力解決資金不足的問題。鑒于江蘇省黑熱病防治隊缺乏經費,當地紳商主動募集一萬多元。灌云縣中正鎮紳耆查少寶出資千元購藥,設立黑熱病診療所。上海一位不愿具名的慈善家聽說漣水醫療機構少、藥價昂貴,選購千元藥品,邀請曾經擔任紅十字會醫務長的王培元前往施診。雖然地方紳商個人捐獻資金缺乏統一籌劃,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傳統“賑災濟貧”慈善事業的翻版,“現代”意蘊有所不足,但是在政府“財力實難勝任”、亦無余力關注的情況下,地方紳商的善舉對疫情防治頗有助益。
傳統士紳之外,更具組織力和行動力的紅十字會、華洋義賑會等新興社會團體,在黑熱病防治工作中也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從具體效果看,社會團體既發揮了捐資助藥的傳統功能,也具備溝通協調的現代價值。首先,捐款捐物助力疫病防治。上海紅十字會為清江浦提供5000元治療經費;在疫病流行的徐州地區,華洋義賑會聯系基督醫院和坤維醫院免費救治,自1935年12月至1936年8月,受惠者超過6500人。其次,發揮聯系溝通的作用。例如華洋義賑會和紅卍字會聯絡士紳、代收募捐、分縣防治,以補政府工作之不足。華洋義賑會還將疫病和捐款信息刊登于報紙,廣為宣傳。因為能夠調動更加廣泛的資源,更加善于宣傳防疫措施,所以社會團體在黑熱病防治工作中的作用比捐資助藥的士紳更加顯著,也更加具有現代性。
四、結語
清末民初教會醫院憑借較為豐富的醫學知識和診治經驗治療病患、調查疫情,無論是知識更新還是技術提升,都對中國黑熱病防治有開創之功,但是我們也必須正視其救治工作中傳播“福音”和追求盈利是雙重驅動因素。1930年代南京國民政府和各地方政府通過機構建置、病患診療和科學宣傳等舉措,介入并主導了黑熱病防治,我們還能夠從中體味近代民族主義覺醒、國家能力提升等多重意蘊。以中西醫生、紳商和民間團體為代表的社會力量通過診療病患、捐資捐藥和組織協調等不同方式參與防疫,是社會進步的重要表現。總之,教會醫院首發其端、中國政府隨之主導、繼而社會力量參與的黑熱病防治歷程,大體可以視為近代中國衛生防疫體系變遷的縮影。
近代中國黑熱病防治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諸多缺陷和制約因素。首先,經費不足,衛生署專項經費不過是杯水車薪,江蘇省政府更是“省庫支絀,無款可撥”。其次,治安不良,蘇北、皖北盜匪橫行,影響了防治工作。再次,民眾公共衛生意識薄弱,人畜雜居,環境惡劣,于防治不利。最后,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打斷了剛剛起步的防治工作。總之,由于上述因素影響,黑熱病依然是解放前中國的流行病。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于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社會經濟發展,醫療衛生事業取得長足進步,黑熱病終于被基本消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