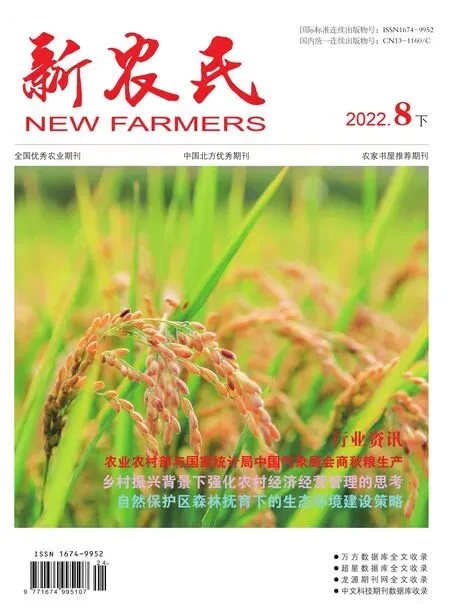“三權分置”入新修《農村土地承包法》的問題研究
周 怡
(華南農業大學,廣東 廣州 510000)
1 三權分置的相關要義
《“三權分置”意見》的主要內容和基本精神包括:一是闡明了“三權分置”實施的歷史必然性及其在現代農業發展進程中的重要價值;二是明確“三權分置”的指導思想與基本原則,并對土地集體所有權的地位進行確立,同時規定應嚴格保護農戶承包權、加快放活土地經營權和完善“三權”關系;三是對“三權分置”的具體實施目標以及要求進行了明確。
在20世紀70年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提高了我國農民的積極性,為國家發展予以了不可磨滅的支持。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的日益發展,以家庭承包方式存在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問題也逐漸成為人們眼中的焦點。作為在農村承包經營關系中的新型物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具有與傳統民法物權種類有著截然不同的特征。其一,該權利的標的不受其他的不動產,而是特有的耕地、林地、草地等;其二,承包人對生產資料獨立處分,排除任何個人乃至組織的非法干涉;其三,該項權利具有一定的期限,并且根據不同的土地類型,物權法予以了不同的期限規定;其四,土地承包經營權為特定的生產經營項目所使用。也正因為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獨特性,它的流轉原則也有了具體的限制:必須是出于平等協商之后,自愿有償的交易,同時不得改變農業用途——堅守耕地紅線的體現,流轉期限不能超過承包期剩余的期限,且受讓方必須有一定農業經營能力,同等條件下本集體組織成員享有優先受讓權。在現實生活中,對于土地承包經營權是否可以繼承的爭議時有發生,需要明確的是,農地的承包經營權是不能作為遺產處理的,由于它的特別性質,更對承包者和發包人作出了義務要求。
作為與農民利益相關的重要權力,宅基地使用權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都是不得受侵害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以下簡稱《土地管理費》)明確對集體所有土地上的建設用地的使用作出了規定,需要經過行政機關嚴格的審批和辦理相關的手續。如今,在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試點工作有四大任務:完善土地征收制度,包括提高征收的補償標準;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健全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方利益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實現個人收益提升;建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出于對農民生活的保障,以及防止出現土地兼并等情況所導致的弱勢群體流離失所,我國的法律以及政策都對宅基地使用權的流轉加以了嚴格的限制,在許多方面是禁止有部分是不必要或者不合理的,因而需要不斷地完善和進一步的探索。
2 三權分置“入法”的背景
2.1 現實面臨的要求
在我國的土地承包政策中,公布的修改一共有46處,內容涉及承包期的延長土地經營權,土地經營權的登記土地經營權流轉合同的訂立和解除,保護進城農民,保障婦女權益以及社會資本通過流轉取得土地經營權的資格審查制度等其他方面。
從安徽鳳陽小崗村拉開序幕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度已經在中國歷史上書寫了四十年,與前相較中國早已產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農村也不例外。也正是因為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許多農民進城打工,大片的土地被荒置,日漸增加的“空心村”的出現,因為土地的分散而難以集中利用而致使規模化農業生產受阻,這些都嚴重阻礙了新農村的經濟前進的步伐。同時,在《農村土地承包法》中的第二十一條中明確耕地的承包期限為30年,草地承包期限為30年至50年,林地承包期限為30年至70年。由于歷史向前發展,時至今日許多農村土地的承包期限也即將到期,這也使得許多對農村土地產生承包想法的人止步不前。為了子女的教育、醫療、住房等社會保障,許多想要落戶城鎮的進城農民也在近年來因自己的土地承包權是否將會被沒收而憂心忡忡。女性地位的提高,經濟關系的日益復雜,農村外嫁女的權益的維護……由此可見,在“三農”問題上我們遇到了許多亟須改革的地方,在保障改革,促使立法的進程中,對于現實生活所面對的重重困擾,我們所做的一切還需要繼續努力,通過法律的手段助力問題的解決,三權分置“入法”是現實的必然要求。
2.2 舊法存在的不足
從2003年3月1日起實施的《農村土地承包法》由于農業和農村形勢的發展變化,涉及土地承包的問題不斷增多,該法已經難以適應錯綜復雜的農村土地問題。如現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流轉登記制度難以起到應有作用,甚至在群眾中缺少必要的公信力。這是因為我國法律在土地承包經營權上采用的是債權合意主義,但其登記又并非權利確認的必要條件,所以其僅能產生一定對抗效力,而并不能進行明確的約定,導致實際應用中常引發各種糾紛問題。
從《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發包方和承包方的權利和義務在承包合同中約定。”以及《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時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中可以看出其中的無權債權化問題。也正因為如此,才會屢屢發生承包合同被當方撕毀的問題。究其原因就在于依據上述規定所形成的合同關系是債券而不是物權,而債權在對抗效力上又明顯不足物權,這就導致過去各種無視農民土地權力而占地、征地現象的頻繁出現。
與此同時,作為用益物權的一種,它的處分權在法律上諸多受限,在《土地管理法》《農村土地承包法》多有體現,例如取得的行政審批繁復,流轉甚至加以禁止,嚴重阻礙了農民賦予土地融資的機會。
綜合舊法存在的不足之處以及現實發展所面臨的要求等背景之下,三權分置納入新《農村土地承包法》無疑是大勢所趨,是群眾的呼吁,是黨和國家在農村改革的重視,是對舊法存在不足之處的修正,也是為三農問題的有效解決保駕護航。
3 三權分置“入法”的意義
3.1 歷史意義
從20世紀70年代到如今新一輪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冉冉升起,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確立到如今三權分置納入新《農村土地承包法》,象征著全面深化改革在農村土地問題上邁出的堅實步伐。
一直以來,我國的農村土地改革采取的是自上而下、從分戶到集中,再到高質量分戶的策略。這是因為農村土地本身就是國家的稀缺資源,對國家糧食安全、社會生產等大局有著直接影響。同時,其也屬于一種重要生產要素,對未來農業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三權分置的入法,是生產力的發展,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適應的結果,也是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客觀規律的體現,對改變農村落后局面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3.2 現實意義
三權分置的法治化意義深遠,這是因為其為新時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以及承包農戶的權益提供了必要保障。同時其也對我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鞏固與完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推進以及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有著積極意義。同時,“三權分置”入新農村承包法,實際上也意味著在“倒逼”土地管理法及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加快修法進程。《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刪去了現行土地管理法中有關從事非農業建設使用土地必須使用國有土地或征為國有的原集體土地的規定;同時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為工業、商業等經營性用途,并經依法登記的集體建設用地,允許土地所有權人通過出讓、出租等方式交由單位或者個人使用。最重要的是,針對現下存在的問題,“三權分置”在入法時都將解決的對策落實在制度上,以制度的框架保護農民的權益。例如,上述提到的農民落戶城鎮后土地承包權的問題,在新修訂的《農村土地承包法》中就對其進行了保護,明確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農戶進城落戶的條件。如果承包期內農戶進城落戶,應引導其根據個人意愿依法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轉讓土地承包經營權或者將承包地交回發包方,也允許其積極進行土地經營權的流轉。
綜上,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的角度看,“三權分置”入新農村承包法是有效地刺激了農村經濟,促進了農業的新勃興,也讓我們看到了改革的紅利,增強了對農村改革的信心和支持。
4 “入法”后面臨的問題
4.1 法律存在的漏洞
雖然三權分置被明確納入《農村土地承包法》,但就現階段而言,宅基地使用權實施三權分置仍只是在國內部分試點中進行,其還未形成成熟的可廣泛推廣的制度經驗。同時各方面對三權的認識仍不統一,還需進一步研究并形成共識。
再比如婦女權益保障方面,原有的《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條規定了在承包期內,婦女結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婦女離婚或者喪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而這條規定也出現在了“土地承包法修正案”中的第三十一條。還有該法的第六條中規定:“農村土地承包,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的權利。承包中應當保護婦女的合法權益,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剝奪、侵害婦女應當享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可是在法律規范是,這既可以被婦女新居住地利用作為拒絕分配其承包地的依據,也可以被婦女原居住地利用作為收回其承包地的依據,所以其是否真正能夠實現其法律目的還有待觀察。因此,在現實執行的過程中,未來也許還需要相關的解釋或者意見的出臺,結合實踐運用過程中所遇到的難點進行不斷的完善。
4.2 現實存在的矛盾
三權分入法保障后有助于把分散的農地集中起來發展現代化的農村規模經濟,但是由于流轉后的土地過度的集中,也有可能造成一定的風險存在。因為在整個過程中,涉及的主體由企業、農民已經集體經濟組織,合作社等等,不同的主體所承擔的能力不同,因而面對風險容易使得農業生產受損。同時,進城的農民將土地長期出讓承包,如果出于種種原因返鄉務農但是由于承包期較長,而短時間農民個人內不能收回土地以至于難以養家糊口等,自身的利益受損。由此可見,雖然三權分置入新農村土地承包法,但是在“入法”后依然在現實生活中存在矛盾與分歧。因而完善農村土地承包法不是一蹴而就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任重而道遠。
5 結語
從現實要求和彌補不足這兩方面研究三權分置入新農村土地承包法的相關背景條件,理清其中的要義,分析新修的條例對現實產生的重要影響和歷史意義,可知三權分置思“入法”是農村土地改革的重要舉措和必由之路,思考“入法”后仍需面臨的問題,有助于我們不斷促進法律法規的完善,在實踐中理解和適用法律,深入思考解決入法后當前存在的矛盾,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努力讓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讓農業得到發展,農民得到保障,農村得到改變。“三權分置”入法是從法律層面保障改革發展的一個措施,也是改革進程中向人民展示的一張優秀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