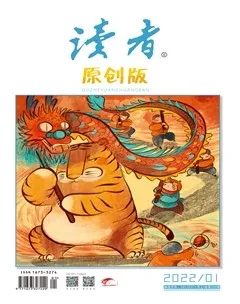飛翔的牧歌
文|安 寧
女孩牧歌像一只誤入房間的蝴蝶,光腳踩著地板上的陽光,歡快地奔來跑去。
她嘴唇青紫,臉色蒼白,跑幾步便停下來大口大口地喘氣,好像剛剛經歷了一場艱難跋涉。因為患有小兒唐氏綜合征,五歲的她只有三歲孩子的身高,五官則似永遠不會綻放的花朵,皺皺巴巴地蜷縮在臉上。這張小臉看上去有些扭曲、丑陋,好像上天隨手扯了一塊軟泥,漫不經心地捏出來,丟到人間。每個見到她的人,都會忍不住擔心:她將來如何在漫長的人生中躲過來自外界的好奇、輕視、鄙夷,甚至排斥?
這樣的擔心顯然是多余的。天生的心臟病和肺部缺陷,使她在人間的旅程即將結束。兩天前,她的父母和奶奶帶著她,從牧區乘坐火車,千里迢迢抵達我居住的城市,準備接受北京專家的免費心臟手術。最終,他們排隊等來的,是牧歌不僅不能手術,而且很快將離開這個世界的死亡宣判。五年來,時不時就生病住院的牧歌,給家庭帶來沉重的負擔,家里一次次賣牛、賣羊,為她奔波治病。或許,他們堅持了太久,有些累了,所以醫生的宣判并沒有給他們帶來太多的悲傷,似乎這只是一次習以為常的診治。在死亡抵達之前,牧歌依然是給全家帶來快樂的天使—盡管她長得不美,至今連一句話也不會說,又在上千個夜晚因為呼吸困難無法入睡,用尖銳的哭聲折磨著全家每個人的神經。
此刻,這一切塵世的憂煩,在牧歌心里沒有引起任何波瀾。她已被人生的第一次外出旅行完全吸引了。在她眼前,世界忽然打開奇特的畫卷。一株來自塞外的瘦弱小草,無意中闖入了大城市,見到櫥窗還房貸琳瑯滿目的商品、熙熙攘攘的街道,她小小的心被熱烈的火焰瞬間點燃。她拖著疲憊的身體,用一顆破損的心臟,感受著這座城市席卷而來的力量。她“啊啊”地喊叫著,說不出一個完整的詞語,但她蝸牛一樣蜷縮的耳朵可以聽見任何奇妙的聲響。
大人們一臉憂慮地注視著生命即將逝去的牧歌,她卻將這樣的關注視為對自己莫大的鼓勵,于是,她繞著沙發、餐桌、書柜、玩具,貓一樣靈巧地旋轉,起舞,飛奔。不過片刻,她蒼白的額頭上便浮起一層細密的汗珠,陽光落在上面,仿佛落在白色的沙灘上,熠熠閃光。那光讓她看上去有了一些生命的歡愉,身邊人便暫時忘了苦痛,重新回到日常的軌道上,絮絮叨叨地說著她能吃一碗米飯,喜歡喝營養快線,愛吃土豆,厭倦肉食;她不會說話,時常因無法表達內心所想而發脾氣,并將玩具扔得遍地都是;她沒有伙伴,見鄰家孩子來玩,便心生恐懼,“啊啊”叫著逃走;她短暫的一生,不會與幼兒園結緣,卻喜歡隔著鐵門,看與她同齡的孩子在秋千上蕩來蕩去。草原上吹來烈烈大風,她孱弱的身體猶如草葉,只微微晃動著吸入一些潔凈的空氣,便重新陷入孤寂。
其余更漫長的時間,牧歌都跟媽媽在簡樸的出租屋里度過。這是為她遮風避雨的溫暖家園,她生于此,也會在不久的將來從這里離去。在死亡抵達之前,她依然是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在沙發上快樂地爬上爬下,將客廳里的擺件逐一拿起來把玩,拿起書柜里的書好奇地翻了又翻。她還從來沒有讀過書呢,一個字也不認識,那些蝌蚪一樣跳躍的字符里,究竟隱藏了怎樣的秘密,她并不知曉。那些汪洋一般浩繁的知識,與她的一生毫無關系,她不需要了解它們,它們也永遠不會記住牧歌這樣一個在我們的星球上稍縱即逝的天使。她帶著疼痛的軀殼,在人間磕磕絆絆走過短暫的5年,無數漆黑的夜里,常常因為昏厥,給家人帶來對于死亡的無盡恐懼,而當黎明抵達,痛苦消散,她歡快奔跑的柔軟身體,又讓家人重新燃起活著的渴望。
正是春天,泥土蓬松濕軟,植物根莖彌漫著草木的清香,鳥兒在窗外高大的榆樹上啁啾鳴叫。天空藍得耀眼,大片的云朵簇擁在窗前,朝著春光滿園的人間好奇張望。一只小狗在風中發出歡暢的叫聲,無數蟄伏在地層深處的小蟲慵懶地睜開眼睛,注視著新奇的世界。這是萬物復蘇的季節,生命從腐爛的軀殼中重生。一切舊的事物都煥然一新。陽光遍灑街巷,將所有灰暗的角落一一照亮。
而牧歌,一朵尚未綻放的花朵,即將在這樣的春光里枯萎。只是此刻,死神還沒有抵達,人們便愉快地欺騙自己,以為它永遠都不會來。于是大人們繼續說說笑笑,逗引著她,將所有能讓她快樂的玩具統統送到她的面前。她皺皺巴巴的小臉,在親人的關愛里泛起點點紅色。這紅如同春天落在嫩芽上的一抹光,照亮了小小的孩子,也照亮了人間的哀愁。
那一天到底何時會來呢?人們不愿去想,牧歌更不會關心,她還完全不懂生與死是怎樣一件事。她來自塵埃,在人間飄浮了短短的一程,又將重新化為塵埃,消失在浩瀚無垠的宇宙中。或許,她會變成一顆閃亮的星星,只要思念她的人們抬頭,就會在夜空中分辨出獨屬于她的微弱星光。
那時,小小的牧歌將不再頻繁地出入醫院,她弱不禁風的身體上也不會再布滿針孔,她更無須一次次驚恐地打著手勢,告訴家人她不想打針,不想吃藥,不想走進醫院。她將疲憊又幸福地在星空中閃爍,就像天使注視著人間。
而此刻,她依然快樂,仿佛世間只有永恒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