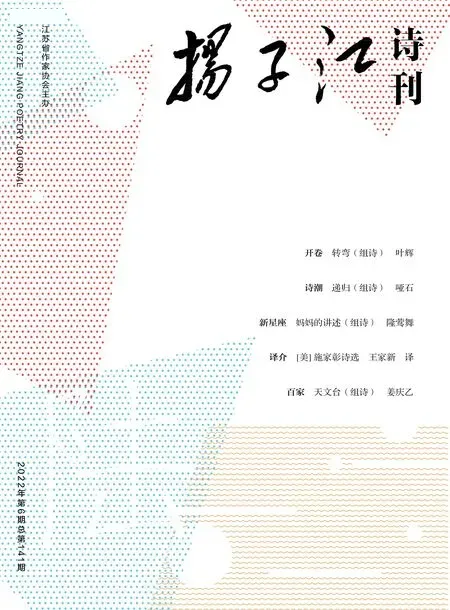蘋果樹(組詩)
清 越
影子愛人
呼吸,呼吸,模仿山谷
灰白色的煙和魚
——通往過去的魚
在洇開的筋骨上爬行
身體面向身體,學習彎曲
背行,延展,雙臂向前
抓住流逝的沉默的踽踽
將眼睛藏起來,接著是高歌
接著是二十三號染色體,杏仁。
被抒情折疊的隱喻,腳背
像一對稚嫩的耳朵
只有手指,你和我唯一的聯系
呼吸,呼吸,我們忍受羞澀
羞澀握著你的,藍色的
你的藍色的鏡子的臉
你正在問我,我正要回答你
而時間突然剪斷
只有旋轉與旋轉
站立原地
我以目光睡在母親的肚皮
我以目光睡在母親的肚皮
手術疤痕編織一座石梯
她保持著撩舉衣服的姿勢
手臂是低頭的柳枝,白魚
高音默誦命運的哀歌
共生于疼痛而羞赧的呼吸
目光代替我怯于坦白的
貧瘠的勇氣。我知道
另有一處疤痕在胸膛
形似表盤,甜蜜的酒窩
別在肉色胸口的計時器
母親的傷疤無法孕育生命
只孕育了死亡,一顆粉色的
扁桃仁。站在醫院等待審判時
她說起我出生的那天有雨,
“你的手像扁桃仁一般小”
寬容的手掌落在我的額頭
“去把花盆搬進院子里吧,
明天起要過秋天了。
都見見太陽。”
與貓度過的凌晨時分
貓在凌晨被送去動物診所
被目睹了疼痛的啃食
白色寓言在腸道里領路
靈魂交給耦合劑
打碎,我撲向我
一只奇崛的病虎——
它曾相信我能予以安撫
帶走疼痛如同帶來食物般容易
手掌扮演粉紅色的母親
而我無法解釋
不過是共存的關系
我們:貓和我 一個
匍匐的影子和另一個
在疼痛面前,并排扮演
無聲息的蠟像:
貓和我 我和我
冗長,又深褐的
去往柔軟處成為更柔軟的
費洛蒙、水、顯影燈
和野獸的吞咽
拯救或者趨于平靜
只能從身體的內部開始
如同等待戈多那樣等待種子
后來,
我們用盡了這一天
從凌晨到凌晨
互相依偎著
像垂頭的影子
唯有遠離日常的沉悶和不斷變化的欲望
多云。我無法舉起蠟筆,你也是
憤怒是我的城堡,沉默是你的
貓咪躺在春日底下,敲打著尾巴
日光困在云層里。我無法舉起畫布
你也是。很快我們將忘記爭吵,
重新創造時間。對于裝飾物而言,
二月的清晨與三月、五月的并無不同
藍
她舉起畫冊和碳筆
鵝黃的神情模仿眺望
身體的紅色方格里
游動迷途的鳥的眼睛
兩個孩子跑出線條外
手與日光交疊成一扇門
在放白的紙鳶、黑的紙鳶
是壞孩子,也是好孩子
她臉上被添加的斑點
嬗變星辰、飄浮與渦流的符號
畫布前的大人為孩子講故事:
當一個女人與鳥站在一起
是兩個宇宙站在了一起
以上是胡安·米羅畫展廳里
被簡化的某一時刻
來自白日、一個白盒子和
畫作尚未完成的白色畫布
它的關聯詞有:
光 干燥 夢 行走 純粹
歌謠 夢 思考 仰頭
我做速寫的人
編造這一刻尚未發生的
并也取名為《藍》
蘋果樹①標題引用自貝爾特·莫里索的油畫作品《蘋果樹上》。
是夢境,風吹動的小憩時刻
綠色重復于尚且潮濕的曖昧
白色喻為光、身體、充沛
比起虛構的迷戀與枝頭
油彩更像沼澤
在模糊的疊加間徘徊
刮刀下的藍令人想到海浪
畫中的少女側對著觀看者
她的臉上迎著白色的夢
并不企圖表達共情
當我走進觀看時
色彩覆蓋了玻璃
就像鳶尾花開滿河岸
蜚動著無骨的留言
我想起新學來的比喻:
綠色藥形容無疾而終的愛情
或是蘋果樹上的少女
布里埃舞場②《布利埃舞場》是索尼婭·德勞內于1913年創作的床墊布面油彩畫。
深幕在跳舞
光裸的腳趾在跳舞
沐浴者在跳舞
布帛與赤馬在跳舞
所有的黑與鏡子跳舞
無聲的面孔跳舞,手心探出火焰
詞語跳舞,而你站立著
你站立著
褶皺的掌紋站立著
長夜站立著
青年的焦灼與爛漫站立著
謊言與時間的影子站立著
你看不清
靜止與運動是一對尖銳的耳朵
永恒不過是短暫
想起被縫補過的曾經
你蹲下,臂彎化作龜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