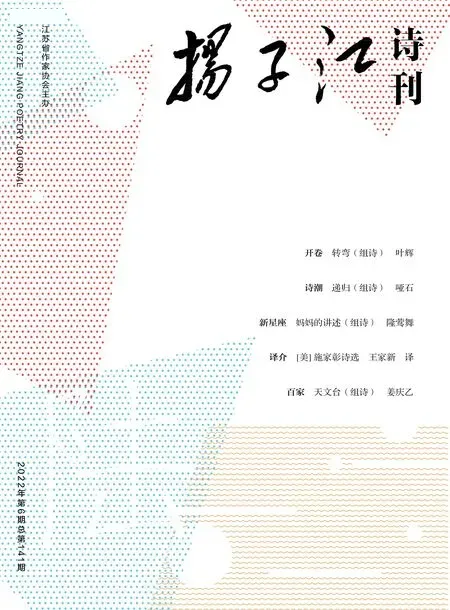樓蘭樹葉(組詩)
王自亮
兔子之歌
兔子,我歌頌你
拋棄雪的詞藻、高原的句法
舍卻光芒的語匯、迷宮的修辭
你是與巖畫一樣拙樸的寓言
你是精靈,與飛鳥同等的隱喻
龜隱忍地背負歷史,而你踏著哲學
以閃電的速度抵達形而上高地
如此迅疾的慢,黑暗中的白色身影
至今落在人們思想的低洼處
布滿血絲的眼睛是網狀世界的倒影
而溫順只是征服時間后的謙遜
你是攥緊的拳頭,低頭一剎那的愛意
如仙人掌開在漠野:緊張的自在
聽到你的叫聲,我的神經收縮著
然后大片地、史無前例地張開
像原野上雨后無名的花草
看到你吞咽草料的樣子
憶及多少人和事,我們就這樣嚼下
從不儲存和反芻,也不沉思
兔子,把聽到的和看到的你攪拌在一起
這個世界就成立了,人們
就有理由活下去,堅強地活著
含淚注視著飛禽、原野和玻璃
和箭一般飛過的時間
以及被同一支箭穿透的世界
兔子,早安
老樹,大樹——懷念我的先師
我曾經盯著一棵老樹看了半天,
在想:它為何能長出新枝,繁花似錦?
身體里究竟有一種什么樣的力量,
戰勝死亡同時,去勾勒新的天空?
樹還是樹。枝葉是新的,花瓣如此唯美,
就像浮世繪中探出屏風的虞美人,
以芬芳托舉美的信念,至高的善
傳遍每一個角落,每個毛孔。
多年來,我一直在想:
老樹與新枝是否就是一個整體?
不可分離的整體,還有花瓣。
也許力量源自《楚辭》,中式棉襖下的
心跳,深度近視眼中的洞察。
傳承的文明才叫文明,氣勢若虹,
先生們是老樹,更是大樹。
作為枝葉,我們的綻放意味著
不敗的敬意,永久的凝視。
西溪路五十六號垂柳紛披,塊石互拱,
一只翠鳥的鳴囀來自那部《竹枝詞》。
是的,我們構成一棵樹,一片樹林,一個原野,
這個“神圣家族”,自帶光芒。
樓蘭樹葉
樓蘭,在一千五百年前就開始凋零了,
一座被遺棄的城,猶如枯葉。
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縣北境,
羅布泊的西北角,
孔雀河道南岸的七公里處,
有一片落葉叫“樓蘭”。
一陣大風刮過這地方,
瓦礫與瓷片聲色不動。
流沙掩埋了城郭,
古運河輪廓、官署依稀可見。
一座八角形的圓頂土坯佛塔,
尚立風中。
樹葉與城墻一起枯萎,
佉盧文文書抽芽,文獻拔節。
五銖錢、絲毛織品、日常用具,
被斯文·赫定他們取走;
我只得到一片樓蘭樹葉,
得到一處被遺棄的城址。
一個叫“樓”的人質王子,
一個叫“蘭”的絕代佳人。
一片凋零了一千五百年的樹葉,
一座委身時間的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