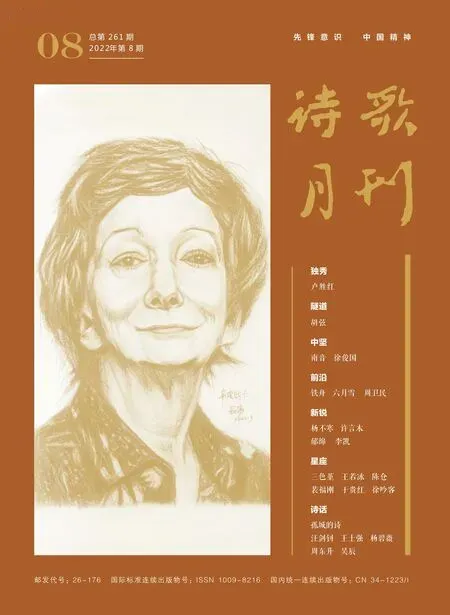郁綿的詩
郁綿
藍色上衣
春天太盛,敗了一夜的花
我添了新的郁金香、水仙、鈴蘭
看它們在清水里依偎著盛開
那街角花店的名字總令我想到量子糾纏
但論及人與人的糾葛,總感覺是前世的事
今世我只是在灰藍天空下,等待
小店熱騰騰的食物,對著樹下走來走去
腳步輕快的麻雀兒發了會兒呆
太陽明晃晃地懸吊,撲通一聲
掉下來,砸入有些渾濁的玻璃杯
我飲微溫的水,飲落日的余暉
身后推土機高高舉起曖昧的紅燈,城市
滑入直覺般危險的深晚,看她從煙塵里
剝出。穿藍色上衣,向我走來
浣花溪
走,向每一株樹的來處,
尋訪潭影的交錯,水波的消融。
殘荷,立在濕漉漉的鷺鳥頂端,緩慢舒展,
沉甸甸的,青黃與白,愈發襯得溪水通幽。
千回百轉。他日夜磨折流寓的經歷,
陡峭如崖刻,頓挫如斧斫。
卻又,在晴和的午后俯首,
呼喚松枝的名姓,呼喚每一座,
露水結成的茅廬。
于盈盈處,望見世人的誕生。
立春
“這要是開往巴黎的列車就好了。”
那年我廿四歲,已受摧折,
這座城太美,好的故事再難發生。
人的凋零和葉的軌跡類似,
愛的擁躉更像玩笑,曇花一現地,
透支了余生的月明。
現在穿上藍色緞面裙,迎接我。
伺候在下的棘叢,高——高
低——低
分食圓潤的嗓音。我不再唱,只向前走,
走到每段骨肉勻停地,溢出了銹。
又一年立春,母親用黃絲巾盛雪,
眼看都歸于透明,
所有驕傲的,都厭棄攬鏡。
天空清澈得含混,有關裙上的皺褶,
我又記起一處細節。
將暮
他們畢竟老了,想要忘記
從前的人,也不再是,
吞服一粒阿司匹林能做到的事。
正對著三層居民樓的病房,談談烏衣巷口,
這些露出線腳的往事。看看云,
厚厚的舊棉絮,壓住新抽的枝條。
太陽落山前,他們不再飲茶、下棋,
停止一切,形而上與形而下的搏斗。
轉瞬到來的潰爛可以吞沒一切,
當暮色降臨,人向內在溶解。
面向墻壁的無焰之燭,合攏了燈芯。
冬月
像是寒氣棲居在十二月的枝頭,充潤一切,
郁熱日益消減,形容憔悴地躲進毛衣。
像是反復研磨破繭前后,深刻的折痕,
內陷的鼓膜里,找不回丟失的鳥鳴。
像是有時在角落坐下,假想,退回臍帶,
這安全,引人滑向酩酊散盡的平庸。
像是世界漫不經心的眼淚,
又在悲憫完全凋亡前,向下,遞出匆匆一瞥。
像是站在旋轉樓梯的入口,填滿了厭倦。
盡頭隱約可見,勻停的日光。
離思
各自摘下芍藥別在腰間,樹蔭濃得
望不出深淺,眼底的離愁一抹,
禁不起把玩。你順著青蓮上街往南走,
風聲愈烈,人的底色反倒清淡。
隨手購得一塊芽糖,久違的甘甜,
難以抵擋思念的圍剿。這新發的病癥,
又使藥房的瓦罐,添了幾段木香。
你依稀記得今晨,日光尚停息于旸谷,
喏喏的幾聲珍重,軟而黏,
如坊間燕子的呢喃。須臾人已隔水隔山,
你閉了門窗,匆匆燒卻閑言閑語的紙團。
此后每于遙想水仙零丁的深晚,
便起身挑了燭火,曳尾徘徊。
七月九日雨中漫步
因循的日子,低頭看海
只窺見表層浮沫,輕的灰藍
故而尋了微明的午后,棄傘
看金屬樂的旋律,從她耳后攀升
為著摒棄悲傷,青年恪守沉默
一絲不茍,為她看顧肩胛的蝴蝶
途經三處轉圜,撥開
卡夫卡們行經之所的迷霧
轉過街角,初夏忽地迸發
生鮮的翠綠,被呈遞
眼見小暑步調漸緩,他包里的香煙
失去點燃的意義
在疏朗的時間里,只有她的脖頸
依然勝雪,足以停歇一盞,白茶的甘甜
此時移去心臟密集的鼓點,南風天
增了雨水,減了鳥鳴
他只需望著她,就消解了語言
他只輕輕望著她
在臆想的黃昏,共枕一顆燦燦的金,長眠
望她海倫的妖嬈,飾以博山的淡香
具象的人
回暖后我總惦念,你會不會過得好些
這真是奇妙的緣分:你看啊
多年后我想起你,空氣開始向一側傾斜
顫動的不知是不是光線,而塌陷的
一定是我日益減損的慈悲心
練習與虛空搏斗,再一次次
被恐懼的未知擊倒,即便啊
現在我可以坦然地面對你,交付
馴化后的目光,但再也不能
為生命的降臨和離去,毫無保留地痛哭
醫院對面的高樓,總在傍晚六點零三分
吞噬日落,這時我才敢現形
你會不會覺得可惜:我最終愛上并失去了
千百個具象的人
感音神經性聽力損失
“我還是沒能習慣退化,我看著
漫長梅雨季后,浸在水里的手足慢慢長出了蹼
盡管我已足夠蒼老,皺紋深得足夠容納
更多在年少時失去的時間
曾令我面紅耳赤或潸然淚下的,噪聲或低語
如今都蘇醒,成為二十四小時旋轉的嗡鳴
當我愈是沉默,愈是聽見內里興盛的潮聲
我懷念晴朗干燥的時節,鼓膜完整、清澈
在湖上她寫下:欲望受到侵蝕,行動定要受阻
彼時氣流與蟬鳴,無故地僵持
我折斷了翅膀,碾著神經的枝葉脫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