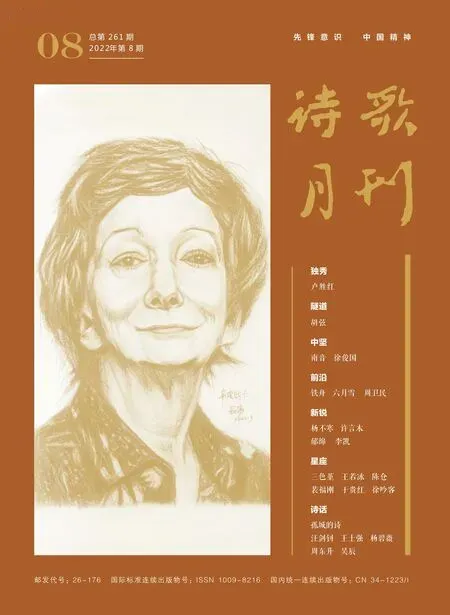新詩的發現
楊碧薇
抒情是古典漢詩重要的發生機制,也是其主要成分。古人作詩,大多因為心中有情,不吐不快。漢語新詩中也有抒情配方,但在不少情況下,抒情只是一個基礎,是踏入新詩殿堂的第一道門檻。跨過了這道門檻,還有無數道階梯等待著詩人們。
“發現”就是一道階梯。新詩更強調發現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進行文體自辯時,發現事物的另一面,發現某種新的感受,常常被指認為新詩最基本的素質之一。如今,人類的生活越來越趨同,諸多有意思的習俗和地域特征在消失,與此相對的是信息繭房的加強。在這種生存現實下,人要繼續保持對生活的敏感度是很難的,而新詩的發現,正好可以喚起新鮮感,修復人們的感知力。
孤城的這組詩就是發現的產物,詩人在構思時便把發現作為詩的基本倫理。《養魚經》 是一首簡潔傳神的小詩。全詩以“一條魚”“兩條魚”“三條魚”為結構,設置了三個段落,分別寫三種情況給人帶來的感受。“一條魚孤單”,“兩條魚乏味”,而“三條魚/剛好/救活一缸清水”。三條魚真的能“救活”一缸清水嗎?當然不是,它們只是給人以富有生機的視覺快感,由此引發的心理愉悅感又投射到水上,似乎水也被游動的魚救活了。由此可見,詩人發現了不同的數量具有不同的趣味,也發現了“救活”這個詞能救活這首詩。
我們再來看一首更復雜一些的。《讀春天》既寫春日景致,亦寫人的心理感受。開篇兩句就很驚艷:“陽光一天天指出雪的膚淺/青稞向高處的山坡站了站。”第一句是說在太陽照耀下,雪一天天融化;第二句轉向植物,青稞也開始出現。這兩句詩提示讀者:春天來啦。接下來的兩段,都是“春天來了”這一主題的變奏,景物描寫與人的心情彼此交織,不斷有新的詩意冒出。例如,“莊稼一節一節拔高春天的涵義”,是寫莊稼開始生長;“劫持一頭耕牛/打開泥土深處的收藏”是寫牛也開始了春耕。這些句子都不難理解,妙在作者沒有平鋪直敘,而是使用了修辭,突出了表述的美感。它們告訴我們:詩之妙,有時并不在于寫什么,而是在于怎么寫。發現了合適的書寫方式,就能把普通的事物寫得不普通,就能在日常經驗中激活審美的觸覺。
最后來看看《互為翅膀》。這首詩和其他幾首詩一樣,出現了不少自然物象。第一段的起意,在于“留一首詩不寫”,隨后勾帶出三種植物,“這是紫薇,這是海棠,這是合歡”。第二段的起意與第一段對應,是“停一杯酒不喝”,隨后寫的還是自然物象。蛐蛐本是再普通不過的昆蟲,詩人卻發現了它和秋夜的關系,“細聽蛐蛐兒用小牙齒/沾月光/將別后的秋夜,磨得日漸薄涼”。蛐蛐的牙齒沾上月光,就真的能把秋夜“磨得日漸薄涼”嗎?肯定不是。但是詩人通過詩的連接,制造了這種奇效。再結合題目《互為翅膀》來看,我們可揣測,這首詩寫的正是一種相互關系,這種相互關系普遍存在于萬物與人心之間,而詩人的工作就是發現并表現關系的交互性。
“云朵,一天天區分開頭頂的風箏以及藍”,在孤城的詩里,發現性的眼光與細膩的筆觸總是緊密相連,一如詩人始終將自身存在與自然世界、精神空間相連。在萬物的聯系中,一次次鮮美的發現所揭示的,正是新詩這一文體的獨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