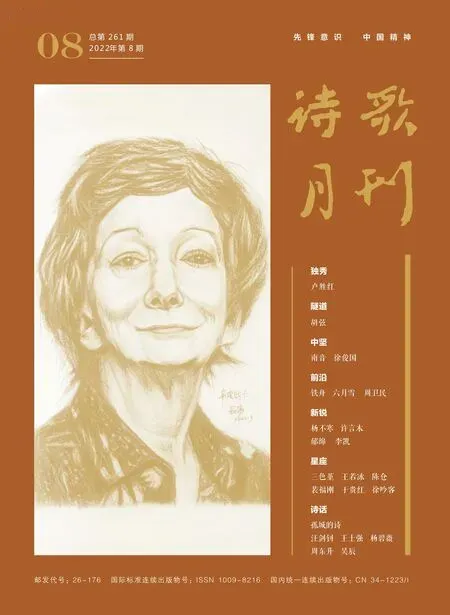一個唐朝剩下的詩人
周東升
讀其詩,想見其為人。我讀孤城詩雖不多,但還是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位有情懷的詩人,一位體察萬物又不拘于物,對現代性有深入體驗卻追慕古典精神的詩人。在《花蕾一層層打開春天》中,孤城既謙遜又自信地寫道“沒有被形容詞破壞過的細蕾,在稿紙上,/直接把我喊成——一個唐朝剩下的詩人”,顯然,這是詩人的自我定位。“剩下”帶有遺民的傷感,也有秉承唐人遺風的志趣。相對于那些高唱復興傳統的詩人,孤城的寫作姿態顯得審慎、節制、恰當。但不得不說,這樣的自我定位也隱含著較大的封閉性,“剩下的詩人”就像前朝的遺民,拒絕順應新朝,既有消極的對抗性,又有主動的排他性。正因此,它限制了詩人當代經驗書寫的廣度和深度,也才有了這類與時代生存甚為隔膜的句子:“眾云已扮成民間的布衣,逢單/趕集幽會,雙日荷犁下田……”(《花蕾一層層打開春天》)
《讀春天》寫的也是一個鄉村場景。起句格調不凡:“陽光一天天指出雪的膚淺”,拋給讀者一個巨大的期待,但讀到結尾才發現,這首詩不過是古人“喜柔條于芳春”和感春光之易逝的另一種精致化表達,似乎萬物并沒有隨著人類進入殘酷的現代社會。“雪的浮淺”“拔高春天的涵義”“劫持一頭耕牛”等驚人之語也隨之落入了慣性語境,止步于修辭層面,顯得十分可惜,甚至,還有虛張聲勢之嫌。在孤城的筆下,不論“讀懂”春天的陽光、青稞、羊群、莊稼、蜜蜂、冰、大海、耕牛,還是讀不懂的雪和風,都成為詩人命名春天的詩性元素,但農耕文明行將消失的今天,如此多的農耕意象又如何能有效命名現代人的“春天”?
現代人的“春天”,不同于古典時代的“春天”,“唐朝剩下的詩人”當然清楚。但“剩下”的情懷使詩人甘心沉浸于唐人的視角,而拒絕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在古典社會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人以及人賴以存在的文化和自然,都經歷了一場沉痛又決絕的理性啟蒙。日常生活的神性基礎被瓦解了,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也遭到祛魅,自然萬物被逼進各自的客觀生命狀態中。這事實昭示了現代人面臨的巨大困境:即便古典的自然山水田園依然存在,人們戴著這雙無法摘除的理性眼鏡也難以看得見。更何況,自然確已消亡,無處不在的,只是經過精心算計、投其所好的風景;農耕文明也失去詩性根基。今天的農民和耕牛,像古典時代一樣入詩,實則是非常殘忍的。牛犁耕田的場景實已成為貧窮、落后和苦難的符號。身處現代性的困境中,人既無法返古也無法超越,這是殘酷的又是真實的。因此,現代詩,不論西方還是東方,皆有一種共同的傾向,即偏于知性和批判性——就是要破除幻想,破除文人的偽浪漫,真誠地面對這一生存的實境。
孤城詩歌常有令人驚嘆的造語,除前文所列,還可以舉出許多:“那些被歲月動過手腳的人/像一株株老寒柳”(《中秋賦》)“秋風在草葉的/遮掩下,翻過山岡就不見了。”(《秋》)“與八百里弓背的波浪一起,練習恢復平靜與/歸隱”(《剩下來的時光,我打算這樣度過》)“春天在窗外喊啞多少回嗓子了?/那把木椅/再沒能回到山林”(《絕望》)等等。這樣敏銳的感受力足以證明孤城的詩歌才華。然而,詩人的觀念就像一個裝置,始終框范詩人對生活的體驗方式以及表達體驗的可能。一旦觀念固化,詩的偏見隨之形成,優點將為缺點所累,缺點也將演化為致命的缺陷,這種情況即便當代名家中也不乏見。就我個人的閱讀感受,孤城的寫作也潛在著觀念固化的危險。讀他近些年的作品,風格越趨個性化,寫作也日漸顯出難以克服的模式化。古典主義的理想和趣味在限制著他的感受方式、寫作路徑和想象力,使他對現代人悖論式、失語化的生存困境,視若無睹或避之不及。尤其是在轉型期的中國,人心內在的巨大波瀾和曲折隱憂,絕非單向度的古典情懷所能表達或命名的。這一點,我相信孤城也心知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