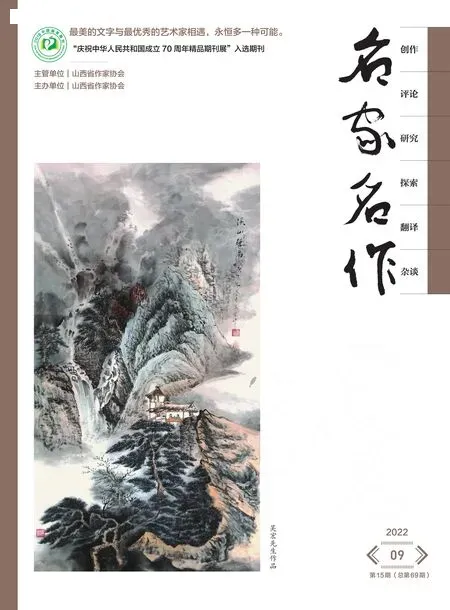簡(jiǎn)析海子長(zhǎng)詩(shī)《太陽(yáng)·土地篇》的創(chuàng)作特色
劉新宇
海子是我國(guó)當(dāng)代著名的詩(shī)人。在他短暫的詩(shī)歌生涯中,他的短詩(shī)最為人熟知,但真正使海子的詩(shī)歌地位得以確立的卻是他后期創(chuàng)作的,包括《河流》《傳說(shuō)》《但是水、水》以及《太陽(yáng)》七部書(shū)等在內(nèi)的長(zhǎng)詩(shī)。燎原曾說(shuō):“海子以他卓越的抒情短詩(shī),以他脫離于一個(gè)時(shí)代群體詩(shī)歌方式之外的卓越的抒情短詩(shī),活在一個(gè)時(shí)代的詩(shī)歌記憶之中。如果沒(méi)有《太陽(yáng)》七部書(shū),他雖然仍是一個(gè)天才性的抒情詩(shī)人,但卻是一個(gè)天才性的少年抒情詩(shī)人。他將缺乏那種堅(jiān)實(shí)宏大的大盤(pán)底座的支撐,缺乏那種從一個(gè)成長(zhǎng)性的少年抒情詩(shī)人到一個(gè)具有恢宏胸廓的集成性詩(shī)人的輝煌氣象,他將只能使人驚奇而難以使人震撼。”《太陽(yáng)》七部書(shū)由七首長(zhǎng)詩(shī)組成,分別是《太陽(yáng)·斷頭篇》、《太陽(yáng)·土地篇》、《太陽(yáng)·大札撒》(殘稿)、《太陽(yáng)·你是父親的好女兒 》、《太陽(yáng)·弒》、《太陽(yáng)·詩(shī)劇》以及《太陽(yáng)·彌賽亞》, 而本文所要探索的就是在《太陽(yáng)》七部書(shū)中位列第二的《太陽(yáng)·土地篇》。
一、《太陽(yáng)·土地篇》的構(gòu)成
長(zhǎng)詩(shī)分為十二章,依照順序分別為第一章“老人攔劫少女”(1月,冬),這里的“老人”指的是“情欲”和“死亡”,“少女”指向“人類(lèi)”;第二章“神秘的合唱隊(duì)”(2月,冬春之交),這個(gè)“神秘的合唱隊(duì)”的成員包括“雪萊”“梭羅”“陶淵明”“韓波”“馬洛”“莊子”等人,詩(shī)人認(rèn)為這些人活在原始力量的周?chē)麄兌紝?duì)“抽象之道”和“深層陰影”有著共同的向往;第三章“土地固有的欲望和死亡”(3月,春);第四章“饑餓儀式在本世紀(jì)”(4月,春),這里的“饑餓”指向人的物質(zhì)和精神欲望的缺失;第五章“原始力”(5月,春夏之交),這里的“原始力”指的是“對(duì)生命力(原始力在人身上的一種變異投射)的一種極端體驗(yàn)的大抒發(fā)即人的一種極端心理情景的大抒發(fā)”;第六章“王”(6月,夏);第七章“巨石”(7月,夏);第八章“紅月亮……女人的腐敗或豐收”(8月,春秋之交);第九章“家園”(9月,秋);第十章“迷途不返的人……酒”(10月,秋);第十一章“土地的處境與宿命”(11月,秋冬之交);第十二章“眾神的黃昏”(12月,冬),喻指神性消逝,人類(lèi)自我意識(shí)覺(jué)醒后精神卻進(jìn)入困境的狀態(tài)。
自然界的一年分為十二個(gè)月,十二個(gè)月又被春、夏、秋、冬四個(gè)季節(jié)分配。詩(shī)人在詩(shī)歌的每個(gè)章節(jié)后面標(biāo)注著月份和季節(jié),有意識(shí)地自冬季出發(fā)又在冬季結(jié)束,形成一個(gè)完整的圓,體現(xiàn)出了四季周而復(fù)始的輪回規(guī)律。而每一個(gè)章節(jié)討論的內(nèi)容又是生存于其間的人類(lèi)的生命和精神狀態(tài),因而這個(gè)圓又在喻指人類(lèi)的生死轉(zhuǎn)化。這些詩(shī)歌章節(jié)向我們展示了自然生命與人類(lèi)生命的隱秘聯(lián)系。詩(shī)人曾在《〈詩(shī)學(xué):一份提綱〉·〈辯解〉》中這樣說(shuō)道:“四季的循環(huán)不僅是一種外在的景色,土地景色和故鄉(xiāng)景色。更主要是一種內(nèi)心沖突、對(duì)話(huà)與和解。”這段話(huà)又揭示了自然規(guī)律除了與人的生命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之外,還與人的內(nèi)在精神相互交織。可以看出,這部作品試圖對(duì)人類(lèi)生存本質(zhì)進(jìn)行探索。胡書(shū)慶認(rèn)為,“這絕非一部傳統(tǒng)的借景抒情性的作品。這是一部具有濃厚象征主義色彩的作品,充斥詩(shī)中的各種物象或可說(shuō)都象征或暗喻著在世界中起作用的某種力量。”而這些極具象征主義色彩的物象正是探索《太陽(yáng)·土地篇》創(chuàng)作特色時(shí)的研究重點(diǎn)。
二、創(chuàng)作特色
(一)動(dòng)物意象的運(yùn)用
“在《美學(xué)》第二卷中,黑格爾認(rèn)為象征作為一種特殊的表征符號(hào),它所要使人意識(shí)到的并不是它本身那樣一個(gè)具體的個(gè)別事物,而是它所暗示的普遍性的意義。”也就是說(shuō),象征這種表征符號(hào)側(cè)重的不是它本身,而是其內(nèi)在隱含的指向更大范圍的意義。這一點(diǎn)在詩(shī)歌的意象中最能體現(xiàn)。詩(shī)歌中象征手法的運(yùn)用自古就有。然而傳統(tǒng)詩(shī)歌中的意象較為單一,且詩(shī)人之間重復(fù)使用的情況比較常見(jiàn),久而久之,意象隱含的意義逐漸被固定下來(lái),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讀者理解詩(shī)歌,但也使得詩(shī)歌的內(nèi)涵變得淺顯,而且被固定的含義附著了先入為主的情感色彩,這樣容易導(dǎo)致讀者的審美體驗(yàn)被破壞。在這部詩(shī)歌中,詩(shī)人繼承了我國(guó)古典詩(shī)歌的象征傳統(tǒng),并在其中注入了新的時(shí)代精神,即使用了不同于以往的動(dòng)物意象以及將這些意象賦予生存本質(zhì)的內(nèi)涵,使讀者從已有的審美經(jīng)驗(yàn)中解放出來(lái)。
從第二章“神秘的歌詠隊(duì)”之“第一歌詠”開(kāi)始,詩(shī)歌中開(kāi)始陸續(xù)出現(xiàn)“豹子”“鷹”“馬”“羔羊”“駱駝”“公牛”等動(dòng)物意象。詩(shī)人在《〈詩(shī)學(xué):一份提綱〉·〈辯解〉》中這樣解釋道:“豹子的粗糙的感情生命是一種原生的欲望和蛻化的欲望雜陳。獅子是詩(shī)。駱駝是穿越內(nèi)心地獄和沙漠的負(fù)重的天才現(xiàn)象。公牛是虛假和饑餓的外殼。馬是人類(lèi)、女人和大地的基本表情。玫瑰與羔羊是赤子、赤子之心和天堂的選民──是救贖和感情的導(dǎo)師。鷹是一種原始生動(dòng)的詩(shī)──詩(shī)人與鷹合一時(shí)代的詩(shī)。”詩(shī)人結(jié)合動(dòng)物本身的特點(diǎn),用其來(lái)指代抽象化的詞,這在詩(shī)人前期的抒情詩(shī)中也是很少見(jiàn)的。動(dòng)物存在于地球的時(shí)間遠(yuǎn)長(zhǎng)于人類(lèi),進(jìn)化論認(rèn)為,人類(lèi)是由動(dòng)物進(jìn)化而來(lái)。人的身體以及精神內(nèi)部還保留著尚未進(jìn)化完全的動(dòng)物性質(zhì)。拋開(kāi)文明道德和精神追求,人與動(dòng)物在本質(zhì)欲望上存在共同點(diǎn)。因而用動(dòng)物意象來(lái)指稱(chēng)人類(lèi)的欲望,是觸及本質(zhì)的做法。詩(shī)人想要寫(xiě)出“真正的史詩(shī)”,就像黑格爾說(shuō)的“象征”要暗示普遍意義一樣,“史詩(shī)”當(dāng)中意象的選擇要帶有回歸本質(zhì)的特性,要有不同以往的普遍性?xún)?nèi)涵。
使用這些非常規(guī)的動(dòng)物意象,除了內(nèi)涵有耐人尋味的特質(zhì)外,從詩(shī)歌語(yǔ)言來(lái)看,其陌生化效果也是驚人的。與詩(shī)人前期詩(shī)歌中的“風(fēng)”“云”“麥地”等意象不同,這些動(dòng)物意象在以往的詩(shī)歌中很少被人使用,因而含有的先入為主的情感色彩不多。一個(gè)意象離人們的常規(guī)詩(shī)歌閱讀經(jīng)驗(yàn)越遠(yuǎn),也就越能使人獲得更加強(qiáng)烈的審美感受。
動(dòng)物意象的使用契合詩(shī)人的“史詩(shī)”追求,蘊(yùn)含著“世界詩(shī)”的文化內(nèi)涵,也在詩(shī)歌藝術(shù)表現(xiàn)上別具一格,是詩(shī)人值得重視的創(chuàng)作特色。
(二)在詩(shī)歌中吐露生存真相
首先,在第一章“老人攔劫少女”中,詩(shī)人提到生存要面臨的重要問(wèn)題──“情欲”和“死亡”。“情欲老人,死亡老人 一條超于人類(lèi)的河流”,這一句指出了“情欲”與“死亡”是先驗(yàn)性地存在于人類(lèi)的生命中。而他們“攔住了”并最終“占有了”人類(lèi)少女,“人類(lèi)少女”只能“欲哭無(wú)淚”,毫無(wú)辦法。這體現(xiàn)了人類(lèi)在生存的過(guò)程中,在面對(duì)情欲和死亡的降臨時(shí),無(wú)辜又無(wú)奈的處境。
其次,在第二章“神秘的合唱隊(duì)”之第五歌“詠雪萊”中,詩(shī)人通過(guò)“天”與“雪萊”的對(duì)話(huà)向我們隱秘地傳達(dá)了生存過(guò)程中要面臨的肉體困境,以及精神追求的意義。“天”這樣說(shuō)道:“……生存是人類(lèi)隨身攜帶的無(wú)用的行李/無(wú)法展開(kāi)的行李 ──行李片刻消散于現(xiàn)象之中/一片寂靜/代代延續(xù)。”相較于天的恒定而言,人類(lèi)的生存著實(shí)短暫,甚至到了片刻就會(huì)消逝于現(xiàn)象之中的地步。這種狀況始終伴隨著人類(lèi)歷史的發(fā)展。肉體如此脆弱無(wú)用,人只能重新尋找另外一種物質(zhì)來(lái)使自己的生存價(jià)值在時(shí)間浪潮的淘洗中盡可能地保留下來(lái)。于是“雪萊”說(shuō)道:“只有言說(shuō)和詩(shī)歌/坐在圍困和饑饉的山上/攜帶所有無(wú)用的外殼和居民/谷物和她的外殼啊/只有言語(yǔ)和詩(shī)歌/拋下了我們/直入核心/一首陌生的詩(shī)鳴叫又寂靜。”這個(gè)物質(zhì)就是詩(shī)歌。在“肉體的人”消亡以后,“精神的人”即人的精神思想還能夠通過(guò)詩(shī)歌等在內(nèi)的藝術(shù)形式保存下來(lái),代替“肉體的人”在時(shí)間洪流中存在得更久。
接著,在第四章“饑餓儀式在本世紀(jì)”中,詩(shī)人談到了“饑餓”即人的肉體欲望和精神追求之間存在的抗衡,這是人的原欲在現(xiàn)代社會(huì)的異化,也是人類(lèi)生存過(guò)程中的本質(zhì)矛盾。詩(shī)人將人的生命比作車(chē)子,他說(shuō):“……駕車(chē)人他叫故鄉(xiāng)/囚犯就是饑餓/前后左右擁著綠色的豹子/渾濁/悲痛而平靜/奔向遠(yuǎn)方的道路上/羊毛悲痛地燃燒/那輛車(chē)子仿佛羔羊在盲目行走……”“羊毛燃燒”喻指神性的不斷消逝,人類(lèi)在欲望的困境中盲目前行,指明了題目中的“本世紀(jì)”人類(lèi)的一種生存狀態(tài)。
最后,在第十一章“土地的處境與宿命”中,詩(shī)人又以敘事詩(shī)的形式寫(xiě)出了人所在的生存環(huán)境——土地的處境。婆羅門(mén)的女兒經(jīng)歷了喪失全部親人、改嫁、暴力、野蠻習(xí)俗等種種殘酷的迫害,最后在機(jī)緣巧合下,通過(guò)野狗的幫助從墳?zāi)怪胤档孛妗T?shī)人在詩(shī)歌結(jié)尾點(diǎn)明主旨:“這女人就是大地的處境”,意在揭示在神秘的生存規(guī)律面前,生存環(huán)境同生存者一樣,都是無(wú)助而又脆弱的。
詩(shī)人通過(guò)詩(shī)歌將人類(lèi)在生存過(guò)程中遇到的困境一一展現(xiàn),使人類(lèi)更加靠近生存本質(zhì),更進(jìn)一步看清生存真相。
(三)東西方文化的融合
海子作為一位在歷史悠久的華夏文明中成長(zhǎng)起來(lái)的詩(shī)人,他的詩(shī)歌精神中蘊(yùn)含中國(guó)的文化內(nèi)涵。而他的詩(shī)歌成長(zhǎng)環(huán)境處于20世紀(jì)80年代,這一時(shí)期各種思潮十分活躍,外來(lái)的新思想如存在主義等又給詩(shī)人的詩(shī)歌精神添加了不同的色彩。如金松林所言:“……前者使他的詩(shī)歌始終流泛著農(nóng)耕文明的光芒,而正是后者,將海子的詩(shī)歌引向了一個(gè)更高的普世主義的維度,即對(duì)理性化世界的批判以及對(duì)生存意義的訴求。”后者顯然程度更深,因?yàn)檫@不僅是海子個(gè)人的詩(shī)歌理想,也為中國(guó)當(dāng)代新詩(shī)“打通了與國(guó)際詩(shī)壇的聯(lián)系”。
詩(shī)人在第二章“神秘合唱隊(duì)”之“第六歌詠”的標(biāo)題下方又標(biāo)注了一個(gè)副標(biāo)題:“種豆南山——給梭羅和陶淵明”,這里的“梭羅”就是寫(xiě)《瓦爾登湖》的美國(guó)作家梭羅。之所以將兩者放在一起來(lái)談,是因?yàn)槎叨荚苁蓝[于山水。不過(guò),詩(shī)人對(duì)二者相似的行為卻有著不同的看法:“陶淵明和梭羅同時(shí)歸隱山水,但陶重趣味,梭羅卻要對(duì)自己的生命和存在本身表示極大的珍惜和關(guān)注。”詩(shī)人表示后者的態(tài)度就是自己的詩(shī)歌理想。而縱觀整部《太陽(yáng)·土地篇》,詩(shī)人也確實(shí)將自己的詩(shī)歌理想付諸行動(dòng),在字里行間表現(xiàn)對(duì)人類(lèi)生存的關(guān)切。
在這部分中,詩(shī)人寫(xiě)道:“……梭羅和陶淵明破鏡重圓/土地測(cè)量員和文人/攜手奔向神秘谷倉(cāng)……”。這里的“破鏡重圓”表明了詩(shī)人內(nèi)心隱秘的詩(shī)歌情懷。詩(shī)人曾在自己的詩(shī)歌中大量書(shū)寫(xiě)“麥地”,這個(gè)“麥地”于詩(shī)人而言,就像是陶淵明的“世外桃源”,詩(shī)人是以此為基礎(chǔ)成長(zhǎng)起來(lái)的,因而它始終存在于詩(shī)人的詩(shī)歌情懷之中。而與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里人人怡然自樂(lè)的狀態(tài)不同,詩(shī)人的“麥地”始終籠罩在一種生存性的悲愴氛圍之下。而這又是其與梭羅相契合的地方:反思生命和生存,而不是為娛情悅目。因而這個(gè)“破鏡重圓”說(shuō)的就是來(lái)自東西兩個(gè)世界的文明,在海子本人的詩(shī)歌生涯中相互交織的表現(xiàn)。胡書(shū)慶說(shuō):“縱觀海子的詩(shī)歌創(chuàng)作,可以發(fā)現(xiàn)其所有意象群都集結(jié)在麥地——太陽(yáng)這條中軸線(xiàn)上。這條縹緲鴻蒙的意象帶在精神訴求上體現(xiàn)為東方回歸自然的‘桃源情結(jié)’與西方終極關(guān)懷的宗教情結(jié)兩條人類(lèi)精神之軸的反向延伸與會(huì)合。”
受東方文明哺育的詩(shī)人又穿梭在西方文明的天空中,兩種文明在海子的詩(shī)歌中交匯、融合,因而他既是一位民族性的詩(shī)人,也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詩(shī)人。
三、結(jié)語(yǔ)
后期,因?yàn)樵?shī)歌觀念的轉(zhuǎn)變,海子開(kāi)始考慮“真正的史詩(shī)”,其詩(shī)歌創(chuàng)作逐漸呈現(xiàn)出不同以往的特色。他以詩(shī)歌為筆,以自然界的動(dòng)物為意象,以東西方文化為詩(shī)歌資源,在《太陽(yáng)·土地篇》中書(shū)寫(xiě)著人類(lèi)生存之謎。時(shí)至今日,整個(gè)時(shí)代處在一種躁動(dòng)不安的氛圍當(dāng)中,詩(shī)歌這種凝結(jié)了人類(lèi)思想的藝術(shù),既展現(xiàn)了生存真諦又具有安撫人心的力量,這又使得探索海子的長(zhǎng)詩(shī)《太陽(yáng)·土地篇》具有了重要的時(shí)代價(ji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