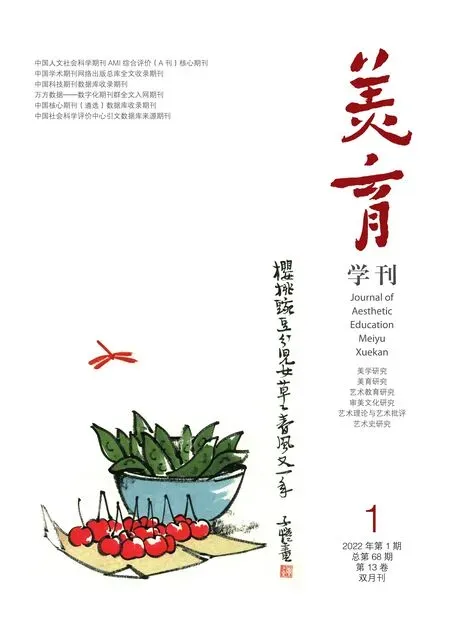中國山水畫的自然與真實
——重估貢布里希對邁珂·蘇立文《山川悠遠》的批評
王一楠
(中國藝術研究院 藝術學研究所,北京100029)
一、《山川悠遠》的價值與追問
《山川悠遠》寫于1979年,它的作者邁珂·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2013)是英國著名的中國藝術史家,1940年從劍橋大學畢業后來到中國,作為后方志愿者參與了抗日戰爭。他是第一個系統地向西方世界介紹20世紀中國現代美術的英國人,并對中國傳統繪畫有著較為體系化的考察。
作為一本面向西方讀者的中國繪畫科普性讀物,《山川悠遠》進行了非考據式的概述,將中國山水畫的歷史作了生動簡潔的梳理,按照朝代的敘史結構和風格學的分期特質勾勒出山水畫形成、成熟、革新、復古、危機的脈絡,其中還穿插引人入勝的傳奇故事和人物生平,深具可讀性。雖然僅是一本入門級讀物,卻在海外和中國一版再版,這說明該書具有一些特別而有待細究的價值。雖然作者謙虛地說“這部書并不在于給中國讀者添加有關山水畫的具體知識”,但巧妙地提供了一條回顧中國人文歷史的線索,有代表性地展現出20世紀海外中國藝術史研究所遵循的脈絡及視點,也暴露出來自不同文化視域的藝術觀念的爭執——這正是這本書的特殊價值所在。
出于這種考量,西方藝術史學家貢布里希(E.H.Gombrich,1909—2001)對此書的評論便顯得尤為重要。1980年,《西方人的眼光》一文發表在《泰晤士報文學增刊》上,其中對于《山川悠遠》的意義與缺漏提出了批判性的看法。盡管《山川悠遠》交融著地理學、歷史學、人類學、風格學的敘述方式同貢布里希作品中流傳最廣的《藝術的故事》十分相似,貢氏的批評仍然非常尖銳。他先是含蓄地提出受眾面對文本時所要面對的永恒責難:“如果我們說自己能‘理解’,又怎么才能確信我們肯定沒錯呢?”這看似是在質疑面對東方藝術的西方讀者,實則將矛頭指向了中國畫本身:
……東方繪畫的批評家……面對著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他們必須斷定什么時候它是“空洞的”,什么時候它充滿了精神的力量,因為它有時確實如此。難怪他們時常要求助于主觀印象或使用一些套語。使用所有這些套語是表示某種神秘的靈素的存在與否。
在貢氏看來,中國繪畫難逃神秘主義的窠臼。對西方受眾來說,“陳陳相因、缺乏獨創性”的中國山水畫也因為品評標準的模糊與多義而魚龍混雜,所謂的一流作品與三流作品間的差別使人困惑。貢布里希質疑的,還有使用風格學方法來界定缺乏變化的中國山水畫本身——僅借助風格學來解釋《山川悠遠》開篇提出的“為何中國山水畫充滿了重復的題材和風格”的問題,在貢氏看來,只是“將孤立的事實轉化為連貫、易記的故事”,這“會掩蓋生活的復雜性”。
在繪畫的創作與鑒賞層面,貢布里希的批評指向了中國山水畫與自然和真實之間模糊的對應關系,實際上也正是對這兩個核心藝術觀念的討論串聯起了《山川悠遠》的篇章布局。《山川悠遠》觸及了問題的答案,但按照蘇立文所提供的思路與論證,顯然無法在既有敘述中打消貢氏的質疑(據筆者所見資料,也未發現蘇立文在這篇銳利書評后與貢布里希展開公開的辯論)。借助他者的眼光,人們能更好地認識自我——盡管這一眼光可能有著偏見與誤讀,卻無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框架和達成共識的基礎。我們不妨延續貢布里希對蘇立文的批評,將中國藝術史置于文化主體的角度予以對照、補綴與辨析,以期重回中國藝術傳統中對山水畫中的自然與真實問題作出回應。
二、山水畫中的整全自然:駁蘇立文的“抽象論”
對于山水畫與自然的關系,蘇立文首先指出山水畫的現實起源是上古時期的高山峻嶺給人們帶來的恐懼感,“對于只想怡情悅性的藝術家,用筆墨在紙素上游歷倒是平安無事的”。他在書中這樣介紹中國最早的山水畫論《畫山水序》:
孫綽4世紀的同伴,佛教徒、詩人和畫家宗炳,在一篇關于山水畫的短文中說:他在山中度過了許多時日,不知老之將至,他想用道術練氣功沒成(他承認他對此不很精通),做一個有責任心的賢儒也失敗了,所以他迷上了山水畫,認為它就像悟道一樣,是理解事物最有效的途徑。……中國那么多山水景色竟把其險峻壯觀的氣象托付給一批膽小的藝術家,實在令人驚訝!
將山水畫視作一種退而求其次的替代選擇,與蘇立文強調中國裝飾藝術的抽象性是相輔相成的。蘇立文認為,山水畫的基本形式來源是自新石器時代到漢代裝飾藝術中的線條,它們在不同時代的藝術作品中有著一以貫之的律動感,因此從波紋和漩渦的形式語言中發展而來的山水畫從誕生之初就具有抽象性。在此基礎上,蘇立文進一步將山水畫指認為對自然的微縮與凝練:“它(繪畫)是神妙的東西,好像小小的園林,包含了自然界的精華。這一觀念正在給中國的山水畫以特別凝練的意義和內容,而不管它的技巧有多么原始。”
然而,蘇立文此處的看法值得商榷。中國山水畫并非由于缺乏勇氣和熱忱去親歷山川、求仙問道而產生的替代品,中國傳統藝術觀念也并不把山水畫視作微縮的自然。在《山川悠遠》一書中,蘇立文其實已經指出了,“山水不僅是道家的象,而且就體現了道的實體”。“漢代崩潰后的動蕩歲月中,‘山水經驗’在畫家、詩人身上突然生發出來,這和他們發現自己作為一個創造的實體是密切相連的。”但令人遺憾的是,他未對這背后的深層見解予以說明,而他將山水畫視作微縮自然的觀點顯示了柏拉圖“分有”與“被分有”的理念論思維定勢。事實上,視山水畫與整全的自然、絕對的真實直接相通的觀念在蘇立文沒有予以充分重視的《畫山水序》中便已表露無遺,并且宗炳的這一文本對后世繪畫的創作與評鑒有著深遠的影響。我們從三個層面予以說明。
第一個層面,宗炳認為山水有“神”,而與道相通。《畫山水序》云:“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雖然山水已被視作是普遍自然的象征,但是宗炳筆下的山水特指一類特殊的、有“神”存駐的山水。宗炳的這一看法在《明佛論》中有過清晰的表述:“夫五岳四瀆,謂無靈也,則未可斷矣,若許其神,則岳唯積土之多,瀆唯積水而已矣。得一之靈,何生水土之粗哉?而感托巖流,肅成一體,設使山崩川竭,必不與水土俱亡矣。”“神”是山水“質有而趣靈”的本因,正因為名山大川中有不滅的“神”在,五岳四瀆這樣的自然物才不只是“水土之積”且不與“水土俱亡”,并具有獨特的形態和韻味。由于山水已被提升至本體論的地位,因此游山水足以稱得上是仁智之樂,是領悟“道”的行動與方式,“如是,則嵩、華之秀,玄牝之靈,皆可得之于一圖矣”。
第二個層面,宗炳認為畫山水與游山水一樣,均能感通于“神”。作為凈土宗始祖慧遠的高足,宗炳的形神觀直接繼承自慧遠。慧遠在《沙門不敬王者論》中認為,“神”非氣、非物而與物感通;物是有形有滅的,但“神”不會和形一起散滅,“神也者,圓應無生,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宗炳則發揮了這一觀念,指出:“神本無端,析形感類,理入影跡。誠能妙寫,亦誠盡矣。”“神”本來是沒有常駐之處的,但因為其可感物,所以能寄棲在山水之形中;“神”又感通于所繪的山水,于是在山水畫中也得以呈現。如果能對山水進行精妙的描繪,就能展現其內在的、與道相通的“神”。因此,不單是有神存駐的自然山水能給人們帶來美感體驗,描繪這一類神山圣水的繪畫也因為“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感神,神超理得”而帶有同樣的審美功能。
第三個層面,宗炳對創作方法論進行了規定,要求畫山水應當“以形寫形,以色貌色”。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被蘇立文理解為寫實主義技法要求的表述,其實并不在經驗層次立論。與顧愷之對人物畫“以形寫神”的要求不同,宗炳此論建立在“山水不是一般的自然物”的認識基礎上,他認為神圣山水之形色自然而然地揭露、昭示著“神”,無需額外的闡發乃至歪曲。與“夫以應目會心為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感神,神超理得”一句聯系起來看,心、眼與山水之“神”通感,在宗炳的觀念中是自然而然的事。“以形寫形,以色貌色”與其說是談論技法,不如說是談論畫山水之“無法”,隱藏在它背后的依然是關于繪畫真實性的深意:畫家通感的是山水之“神”,表現的是渾全的自然與生命的真實,而不僅僅是割裂的、外在的、形象的真實。
總之,在宗炳看來,自然山水與山水畫都能夠“怡身”“暢神”,因為它們都是道的顯現,“神”在二者之間的存在是無差等的。在這一前提下,山水不被視作是“道”的模仿,山水畫更不是“模仿之模仿”,山水畫、山水與道三者是相通的,沒有層級的分別。所以,創作山水畫,不但能夠把握那些“質有而趣靈”的山水,而且不會折損它們的神趣;觀賞山水畫,則能夠直接地體悟到山水之精神、天地之大道。
唐代畫論普遍繼承了宗炳的看法,如王維的《山水訣》認為繪畫乃是“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秉承了創生的靈韻;朱景玄于《唐朝名畫錄》中寫道,“伏聞古人云:畫者,圣也。蓋以窮天地之不至,顯日月之不照。揮纖毫之筆,則萬類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至于移神定質,輕墨落素,有象因之以立,無形因之以生”,認為自然通過繪畫得到了更充分和完整的展現;符載《觀張員外畫松石序》中說,“觀夫張公之藝,非畫也,真道也。……故得于心,應于手,孤姿絕狀,觸毫而出,氣交沖漠,與神為徒”,將畫與道對等而談。后世類似的表述更不勝枚舉,可見蘇立文以《畫山水序》為發端的“抽象論”是一種對繪畫與自然關系的誤解。
三、山水畫中的絕對真實:現實主義之外的考量
蘇立文對山水畫與自然的看法,使他必然以對真實的刻畫為衡量晚出山水畫的尺度,《山川悠遠》接下來的論述也因此圍繞現實主義的興衰展開。他旗幟鮮明地認為,中國山水畫中的現實主義風格在11世紀便已達到頂點。以北宋畫家范寬為例,蘇立文寫道:
他要讓觀者感到自己不是在看畫,而是真實地站在峭壁之下,凝神注視著大自然,直到塵世的喧囂在身邊消逝,耳邊響起林間的風聲,落瀑的轟鳴和山徑上嗒嗒而來的驢蹄聲為止。
接踵高峰而來的是衰落:如范寬這般具有代表性的細致入微的描繪,在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之后的山水畫史中就宣告終結。在蘇立文看來,現實主義在宋代式微有兩個原因:一是當時盛行的理學將求知欲限制在關于人自身的學問中,對面向外部世界的科學方法缺乏信心,一旦知識性的探索實驗所記錄到的自然結果違背中國人既成的世界觀,這種科學的萌芽便會停止生長;二是在蘇軾等北宋文人的影響下,文人階層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他們標榜個性、不重形象而追求“墨戲”,強調文人畫家與職業畫家在“重意”與“重技”方面的區別,這使文人畫有意識地放棄了過于精細的現實主義風格。顯然,這種分析范式也是以西方文明和藝術史的發展邏輯為圭臬的。
蘇立文還意識到,現實主義的過早隱沒帶來了兩個后果,一方面使中國山水畫由“再現自然”早早地轉向了“表現自我”:
再進一步來看,中國山水畫除了同一時期有面目各異的風格,而且畫家的審美意趣和表現手法也在近千年時間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可以說,幾乎到了19世紀末,西方風景畫仍然朝藝術家所觀察到的更為真實的自然發展,與此相反,早在若干世紀前,中國畫家就把創作意圖由再現轉化為表現,或轉向對傳統手法進行再創造。
另一方面,由于自然不再重要,作為人文資源的藝術史傳統便凸顯出來。明清時期的畫家對于過去的特別是宋元名家的風格熟稔在心,“對畫的感受遠遠超過他對自然的感受”,因此他們的山水作品難以避開復古的風潮,日漸成為一種詮釋藝術史自身的抽象繪畫種類。現實主義的衰落同時意味著山水畫不再追求自然的真實,轉而追求選擇風格的自由。“在特殊情況下,風格就是人。”換句話說,風格的選定就是人格的選定,選擇沉浸在哪位大師的創造中,同樣內化為后代畫家的自我,并融會貫通于他們對自我的表達中。
蘇立文先導性地發現在現實主義與復古傾向此消彼長的這一過程中,董其昌的作用不可忽視。他的“南北宗”說追溯并建構了文人畫派的傳統,并以之為畫山水的不二法門。蘇立文因此批評董其昌道:“在某些方面,他給清代畫家以災難性的影響。他提出的‘宗派’,影響了所有畫家,而且完全盲目服從某家某派,以強化他們心中的優越感。更糟糕的是,他們更難憑自己的眼睛去看待自然,除非是通過他指定的幾個大師或實際上是董其昌本人的眼睛去認識自然。”蘇立文的看法與他稍后的海外漢學家們不謀而合。如久負盛名的美國漢學家高居翰(James Cahill)聲稱:“在我真正看來,我比較不能接受這種主觀的反應,我認為董其昌作品的結構完全背離自然。”他認為董其昌對文人畫壓倒性的看法甚至接近一種泛道德裹挾,因為他“獨斷地強調元畫和業余文人主義的優越性”,打破了此前各觀念、流派間的多元和平衡的關系,造成了表現力的僵化。德國的藝術史學者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也以相對機械的“模件”理論為認識文人畫的工具:“盡管自詡輕蔑模件化的制品,文人畫家們在組織構圖與布置景物之時,仍然遵循模件化的原則行事。”事實上,20世紀海外漢學界對文人畫的共識之一,便是認為對傳統的過分強調使文人畫走入了普遍的程式化,同時遠離了真實。一旦承認了這一前提,董其昌無疑使不可抵擋的程式化浪潮變本加厲了。按照風格學的認識線索,文人畫的程式化意味著僵化,那么也就只有最具創造力的畫家才能在這枷鎖中發揮自己的天資,同時他們不得不面對“表現和再現之間、刻意求工和自然流露之間、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間,以及用古代大師眼光認識自然和藝術家自己看待自然之間的矛盾”。這種天才史觀難免將宋代以后的繪畫杰作視為卜數只偶的巧合,正如貢布里希在《藝術的故事》開頭所說的——“實際上沒有藝術這種東西,只有藝術家而已”。
不得不承認,蘇立文對中國繪畫“表現自我”的論述來自其洞幽燭微的體認與觀察,但這一觀察結果與“表現真實”之間并非水火不容的關系,后者的“缺席”更非前者的誘因。如果我們回到《山川悠遠》一書的語境,便不難發現蘇立文反復強調的山水畫之真實,始終未離開具象的限制。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他認為唐代荊浩的《筆法記》尚在探究表現“自然的絕對真實”的程式為何,試圖“把描繪樹干、枝葉、巖石等等視覺經驗提煉成某種語匯,如通常所說的‘畫法’”。盡管這種探索有益于把握自然的真實,但按照他的邏輯,一旦繪畫的程式被定型下來,衰落便是必然的結果:“只要人們發現和概括出‘真’的形體,就埋下了山水畫程式化的種子,現實主義也就開始逐漸地衰退。”只是,蘇立文所謂尋獲“‘真’的形體”,很難不使人聯想到《芥子園畫譜》那般能使初學者最快掌握傳統技法、抓住物象特點的技巧類書籍,而它與“自然的絕對真實”的關系顯然是值得懷疑的。事實上,程式化的山水正是《筆法記》所批判的對象。在這篇雋永的短文中,當荊浩借老叟之口道出“似”與“真”的區別時(“似者,得其形遺其氣”與“真者,氣質俱盛”),便對前文中“我”對“畫者,華也,但貴似得真”的粗淺認識進行了直接的駁斥。否定“貴似得真”意味著只追求形似反而會失去真實,因為圖畫不是在外表上追求與自然物的相似,而是在表現事物的本質與氣韻,試圖在繪畫中復原外在世界給執筆者所帶來的原真體驗。
正如貢布里希在《山川悠遠》書評中的質疑所彰顯出的中西文化間的隔閡一樣,蘇立文的對中國繪畫與真實的看法或許同樣源于一種不證自明的再現式藝術眼光,一種視古希臘和文藝復興時期藝術為正統的美術史研究視角,以及預設西方文明為更高等的文化對照方的執念。有關所謂“現實主義”消退以后的程式化繪畫,現當代的中國學者在這種問題意識的驅使下,已經從多方面給出了不同的見解和回答,如錢穆將寫形與寫意的區別理解為創作層面上的淺與深、易與難的差異:
米友仁《畫史》云:“大抵牛馬人物,一模便似。山水摹皆不成。山水心近自得處高也。”造化自然,亦有深淺。牛馬人物易模,乃其淺處,山水難模,始是造化之深處。人心亦出造化,而更是造化之深處。故曰“山水心近自得處高”,此亦就畫窮理之語。故曰“繪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兒童于人生為淺涉,作畫求形似亦淺涉也。
又如宗白華曾列舉史料說明中國并非缺少寫實的精神與傳統,但具象的追求只是中國藝術三重境界中的第一層而已:
寫實終只是繪畫藝術的出發點,以寫實到傳達生命及人格之神味,從傳神到創造意境,以窺探宇宙人生之秘,是藝術家最后最高的使命。
朱良志則認為,程式化恰為文人畫提供了一種支撐自由書寫的框架:
文人畫越來越明顯的程式化特點,并非文人畫家技窮之表現,也非出于題材的局限性,以簡單的復古論來概括它也不恰當。文人畫家利用這樣的程式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思想,表現自己的生命智慧。……程式化……其突出特點是虛擬性。……文人畫中的程式化,就如京劇中永遠的一桌二椅一樣,其中的關鍵不在組合,而在于畫家在這程式中的活的“表演”。
我們不妨進一步闡發這些回答中能與《山川悠遠》建立對話的部分。在中國傳統藝術話語體系下,蘇立文通篇所謂的“自然的絕對真實”其實僅被認為是表象的真實,遠未達到絕對的真實。文人畫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種呈現心靈境界的藝術,而這在20世紀西方漢學中缺乏真正的體悟。在本質上,文人畫與新儒家的心學和宇宙發生論有著同音共律的關系。個人的心靈被認為能與宇宙息息相通,如陸九淵說“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陽明說“天下無心外之物”,“‘人是天地的心’……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個靈明,人只為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基于這樣的認知背景,對絕對真實的探索被認為可以在表現心靈境界的藝術中完成。這樣的“絕對真實”,才是文人畫創作與評鑒的最高目標。這也解釋了為何與外在的自然物相比,文人畫會更關注“人”的因素,而蘇立文所謂“在宋代以后凸顯的作為人文資源的藝術史傳統”便發生在這一維度。但這僅是極初步的表現,文人畫對“人”的關注共有三方面的呈現:它既要留心過去的名家所創造的程式與風格,又強調將自我置于源遠流長的人文歷史脈絡中回應傳統,還要求表達出獨特的主體意志與精神,以期實現個體同浩瀚歷史與宇宙間的平等對話。對精神世界的執著追求呈現在中國山水畫中,與對永恒時空和真理的思索息息相通,宗炳在《畫山水序》中對“繪畫—山水—道”的見解依舊如暗河一般蜿蜒在山水畫的歷史中。當然,這并非否定摹寫自然在中國畫史中的重要價值,但摹寫自然也總是離不開心靈創造,如張璪說繪畫是“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王履說創作是“吾師心,心師目,目師華山”,便在傳統藝術創作中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無論如何,以現實主義消長為線索的敘述及在此基礎上展開的批評,一定程度上抹殺了中國山水畫的根本特質。
四、結語
盡管本文是一種建構在批評文本上的批評,我們仍能看到蘇立文先生的努力。他在《山川悠遠》中對中國山水藝術作出了許多切中肯綮的解釋,在紛繁漫長的歷史中梳理山水畫的發展脈絡,并使用了大量當時新出的考古材料,展現了全面、立體的敘事風格。蘇立文的寫作是一種將中國傳統美術納入西方現代學科與知識體系的嘗試,有其時代必然性;貢布里希的質疑則猶如一片棱鏡,折射出了20世紀海外學者以擴張性的西方藝術史視角律之于全球藝術領域的傾向。這本四十年前的著作依然啟發著后來學者的尋味與跟進,引發了對中國山水藝術的更多討論,它的意義是遠大于缺陷的。
當然,《山川悠遠》也使我們掩卷沉思:中國藝術的歷史不是西方藝術鏡像般的背反,而是有著自身特殊的思想情境和話語體系。盡管他者的目光仿若先驗秩序一般促使我們審視自身文化的條理與脈絡,但框架填充式的文化闡釋究竟在何種層次發揮其功用?在此書完成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們又應當如何擺脫他者的尷尬地位,基于中華民族歷史與藝術特性探索獨立的學科與學術體系?這是該書留給國內學界的未盡之題,也是需要面對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