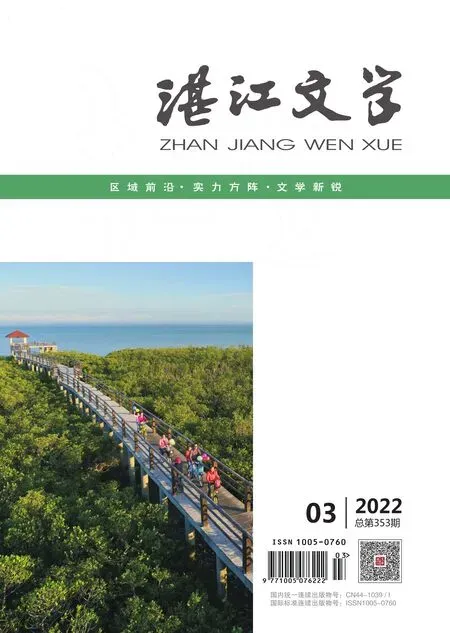燈塔與航標
◎ 譚功才
大凡去過湛江徐聞的,一定不會對海邊那座矗立的燈塔陌生。我不確定所有去過的,回來都會將那個燈塔銘心于記憶深處,但我敢確定對于一個寫作者而言,看到那座塔內心一定會有所觸動。
好幾年前,我在一個聚會上認識了來自徐聞的韓聰光,只是那時的他尚屬圈外人,而寫作者身份的確認,則是后來的事情了。后來的某一天,不知是誰組了個文友聚會的飯局,也有韓聰光參加。有備而來的他,趁了尚未上菜的空當,拿出打印好的詩作讓我們點評。作為多年前寫過幾十首爛詩還出版了詩集,且在協會混了個頭銜后的我,也人模狗樣地裝作懂詩,煞有介事儼然大師派頭地表揚了一通。再后來,小韓就加入了我們團隊,再再后來,我們時不時就泡在了一起。
韓聰光寫詩是有個筆名叫稻田的,只是后來就甚少出現在作品里了。年輕時我們幾乎都有這毛病,沒個筆名人家還真以為我們就是個碼子師傅,水不水平倒在其次。反正年紀稍長,我們都還原成了俗人。除非在文學上頗有成就,將筆名叫得太響亮而忘記本名的,一般都呼喚著彼此大名。當然,以我辛辛苦苦活了那么多年的功勞,將那些晚輩們的姓氏省略,也是極其正常的一件事。
忽一日,聰光微信我,說徐聞老家領導到了中山想我去當陪客,那時風韻土家酒樓正旺,吃著恩施富硒美食,喝著苞谷老燒,還有我這個土家漢子作陪,對于一班吃膩了海鮮的徐聞人而言,換換口味也的確是件相當美好的事情。記得那日以李明剛為首的徐聞作家詩人,坐了滿滿一桌,好幾位至今怎么都想不出姓氏名誰,卻絲毫不影響后來我們在祖國大陸最南端的徐聞再一次相聚。去徐聞自然是聰光挑起來的,他們來中山何嘗不是聰光的牽引?
無意中,聰光似乎就變成了徐聞和中山之間的航標。他在哪里,航行的方向就在哪里。當然,那時的聰光頂多也只能算得上一枚小小的航標,卻并不影響他立志成為更高更大航標的理想。這些年來,聰光在商業界可謂辛勤耕耘,忙里偷閑寫出了不少散文和詩歌,尤其是他還涉足文化產業,拍攝出了好幾部喜劇片子,在一定范圍里掀起了朵朵浪花。這些年的聰光多像我影子啊,各種場合都在竭力推銷自己的家鄉,仿若只有那塊土地上生長出來的,才是正宗的土特產。他心里認同的人,也只有品嘗到那塊土地上的果實,才算表達出了自己的一片赤誠之心。
而對于從故土那頭過來的家鄉人,往往又是慕名而來。為人本就爽朗的聰光,又豈能不費盡心思,將第二故鄉當做主戰場,來一次徹底的“掃蕩”行動?是故,每每我有接待老家過來的朋友要叫上他的時候,總是與他的日程安排相沖突。聰光似乎擔心我的不相信,還將日程安排截屏給我,一句句重復:下次我來安排,下次我來安排。
聰光的徐聞到中山,其實也就是四百多公里,相對于我的恩施到中山,才三分之一而已。距離有時候會成為鄉愁深淺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在聰光這里卻并不太管用。一年之中,再怎么忙,他至少都得回那么幾趟徐聞。那里有他年邁而故土難離的父母,更有他多年來不斷淤積而成的心結。一邊打拼自己的事業,一邊則想著如何為那塊土地做點事情。
那天在聰光出生地一個叫菠蘿的海的村莊,個頭矮小敦實的他,活像個圓圓的菠蘿,在那片紅土地上慌不迭地為我們照相,不停地介紹著那里的故事。他還拿出自己作詞的《菠蘿的海》,用手機播放給我們,然后在那片菠蘿的海洋里孩童一般,就要飛翔起來了。后來得知,聰光多年來對于故土的熱心和付出,家鄉人不僅銘記在心,每逢重大商業活動,都會第一時間力邀他參加。常年在外的聰光,心與故鄉在一起,身體也一樣從未走遠。這些年的聰光,一直在不斷成長。個人成長,企業成長,對于文化事業上的潛心投入也是與日俱增。直到次日去到海邊,見到那個高高矗立的燈塔后,再一次與我心中所理解的航標對上號了。
聰光所在的村莊與中國大陸最南端那座叫做“燈角樓”的燈塔并不太遠,我有理由相信自小的他就立志成為村人的標桿,與那座燈塔有著某種隱秘的關聯。就像1890年法國人在那里建造的這座燈塔,原本只為往來的船只指引方向,后來在不斷的演變過程中,這座燈塔既成了瓊州海峽、南海諸島和北部灣最重要的航標燈,也成了中國大陸最南端的標志建筑物。這種雙重意義上的指向,正是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一直追求的意義所在。
其實,在我看來,那座塔充其量不過是一種表象,或者說是一種顯像而已。如果沿著燈塔后面拖著的那條長長的引線,一直追溯而去,我們一定會追尋到它的始發地。“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座燈塔背后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宋朝的蘇東坡先生,當年這位滿腹詩書的大才子被貶謫海南,必須要經過這三面環海的角尾鄉,從一個叫放坡村的地方乘坐扁舟前往海南。那時的村莊自然不叫放坡村,當這個牛逼轟轟的大詩人曾經下榻過這里,于是就在這片紅土地上誕下了文化的基因,或者說埋下了文脈的種子。從此,中國大陸南極村這個隱秘的桃源之地,開始了她漫長的胚胎孕育過程,直到六百年后另一個叫做湯顯祖的大戲劇家到來,文化的燈塔才算正式被點亮。
由此,我們不得不假設,如果不是大戲劇家湯顯祖的及時到來,接上東坡先生留下的文脈,今日之徐聞恐怕又是另外一個模樣。據說湯顯祖被貶謫徐聞前,這里的人們普遍輕生,且不知禮儀,是故,湯顯祖與當地知縣捐資創建了貴生書院。一來教導人們“貴生”,二來宣揚“君子學道則愛人”,“天下之生皆貴重”的人文觀。
蘇東坡與湯顯祖之間看起來并無多大關聯,就像湯顯祖與后來的燈樓角,也找不到有何種直接的關系。他們之間那種若隱若現似有似無的關聯,實際上是一種文化氣息上的氤氳,她根本不像燈塔上的光線那么耀眼而直接,卻像暗夜里的朦朧天光,恍恍惚惚燭照著大地上的行人。
在徐聞的三天里,我們自然切身感受到了湯顯祖貴生文化的顯像。那里的人們不僅貴生,還將這種文化由表及里,深深滲入到生活的每個角落。他們不僅熱愛生命,熱愛生活,更是熱情好客。在徐聞縣城和鄉下,那種大圓桌圍起來可坐二三十個人的到處都是,僅僅從餐桌上的表象,就可見那里的人們對于生活是多么熱愛啊。我忽然意識到燈塔這個意象,有意無意燭照著這片紅土地上的人們,使得他們在簡單的日常勞動中,成為燈塔照射下的一群真實而溫潤的子民。但他們絕不僅僅熱衷于這種最接地氣的生活,他們還有詩和遠方。
這些詩與遠方的奠基者,便是徐聞紅色土地上那些泛著紅色火苗子一般的革命志士和共產黨人,是他們聯通了從歷史走來的徐聞;是他們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為這片土地注入了紅色基因,而成為一座詩意和遠方俱存的城市。一如從那片紅土地走出去的著名詩人黃禮孩,在省城廣州樹立起了另一座詩歌的燈塔。徐聞人每每談及詩歌,談及黃禮孩,他們每個人臉上都洋溢著興奮和驕傲。這是一座的確稱得上詩意滿滿的城市,他們都以黃禮孩作為遠方的燈塔,燭照著他們前進的方向。
于徐聞而言,中山這座充溢著人文氣息和工業氣息的城市,因了聰光這種文化與商業齊頭并進的徐聞之子,也因了更多聰光一般的徐聞之子,一座逐漸成長起來的燈塔,就要呼之欲出了。
燈塔里的燈光一旦被點亮,源源不斷的能量輸入,注定會越來越亮,直至最后成為另一條河流上的航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