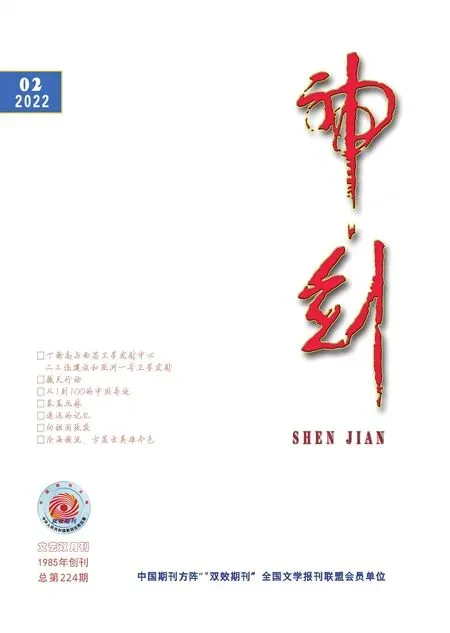春風待我如初戀
□王賢根
一
12 歲那年的一個夏日,我爹起早挑了幾只籮筐到集市上去賣,回來時頂著火辣的太陽背回一只箱子,對我說,這是為你上中學準備的。我即刻放下篾刀,過去欣賞。這是一只用厚實的馬糞紙制作的綠皮箱子,環周條形黑邊,八只角釘上硬生生的鐵皮。這讓我對爹刮目相視,肅然增添數分敬意。
我是1961年暑期接到錄取蘇溪初級中學通知的。那段時間,我和家人都在趕做籮筐,籌措學費。報到那天,我爹將我媽為我準備的幾件薄衣褲和被單等物件平整地放進皮箱,還有幾本書籍和筆記本;一袋大米,一罐咸菜,一把鋤頭和一領草席置入籮筐。我覺得挑只籮筐去上學,有礙面子,建議有的東西入箱子,其他捆好掛在鉤頭扁擔的另一頭就行了。我爹說,你樂斌表哥考上浙江大學,就是挑著籮筐去報到的。我一時無語。
鄉路彎彎。田野上翠綠的雙季晚稻,連成一畈畈,有層次地鋪張開去;路旁渠水嘩嘩,與樹梢上的蟬鳴呼應成歡快的樂曲。我的心像天上翱翔的鳥,有種道不明的要飛向遠方的神秘之感。
齊山樓村的兩棵高大蓬勃的榆樹,像座聳立的路標,遠遠地昭示著行人。樹下是齊山樓完小的操場,我從這里畢業,聽說我們六年級的兩個班,考上蘇溪初級中學的僅有三分之一,大多同學只能回家種田了。那時的學校少,義烏整個縣僅有一所高中。這樣的學校配置,更多的孩子就過早地失去繼續求學機會。我們經過后店村下方那個小廟前斜向的小道,越過溪流潺潺的灘涂,爬上山崗,便遠遠望見有片紅瓦白墻的房舍,在夕陽的余暉里閃爍光澤。我爹說那就是你們學校。我說爹您回吧。我爹將擔子卸給我,叮囑幾句,背影就在金色陽光斜照的山崗上漸行漸遠。
如果從蘇溪鎮的方向往學校走,越過浙贛鐵路線,首先望見的是山崗上那座頗有氣勢的中學禮堂。這座山崗與蘇溪鎮胡宅村有挑擔換三次肩的距離,人們俗稱“三柱頭”。三柱頭大多是開墾不久的貧瘠地塊,還有成堆的亂石和雜草叢生的墳墓。1956年在這片山崗上創辦義烏縣第五初級中學,她為日后義北地區的教育事業和人才培養,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
那時候,我國正處于三年嚴重困難時期,學生中有的是外地下放回鄉的干部、工人子女,有的是解散了的縣越劇團小演員,但大多是蘇溪區范圍的農家子弟,他們衣衫簡樸,忠厚勤奮。這些學子湊到一塊,就像溪灘里的魚,雖然沒啥吃的,但覺得青山輝映,清水長流,自由,快活。
與禮堂相距一段的是教職員工辦公室兼宿舍。業經數年的綠化,這座平房外的冬青,已經綠油油地閃動著瑩瑩的光亮;冬青旁的空地上,一顆顆碩大的南瓜躺在葉下;枝架藤蔓上開著鮮黃的絲瓜花,留存的幾根粗大的絲瓜種,皮色粗糙,有的已經枯黃;番薯葉密密的墨綠,我想它藤下已是豐碩的薯塊了。看得出,老師們也是勤快的好手。
那時候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老師與同學,一面教學,一面勞動,兩幢教室前四棵遮陽的梧桐,傾聽我們瑯瑯的讀書聲,又見證我們扛鋤勞作的身影。學校周邊山崗開墾的片片地塊,種上西紅柿、洋芋(土豆)、番薯,麥地里的麥苗長勢喜人,有年收成特別好,校方將自種的小麥磨成面,由廚房師傅烤成厚餅,分發給每位同學,我舍不得吃,星期六帶回,讓家人品嘗分享。
學校食堂設在山崗西側朝火車站方向,它連接男生通鋪樓。全校學生自帶米類蒸飯。記得食堂的職工,是位新四軍浙東縱隊金蕭支隊屬下堅勇隊的一名戰士,空暇時我們到食堂前的樟樹下,聽他講述抗戰的故事。他說他沒讀過書,不識字,解放后國家安排工作,只能做燒飯這類事。我說,你可到禮堂給我們全校師生講講過去你們抗擊日軍侵略者的故事,他哈哈一樂,然后嘆了口氣,說:“沒文化,上不了臺面,講亂了,對不起大家。”
學生大多住校,僅有鎮上和鄰村的同學走讀,但每天的早自習和晚上兩節自習課,他們不耽誤。住校生,主食食堂籠屜蒸,菜蔬自備。一罐自帶的咸菜,從星期一吃到星期六中午,冬天還好,夏天咸菜上后幾天就長出白絨絨的毛了,我從食堂端回飯罐,用竹筷撥開咸菜上的白毛,從下面挾幾片,吃得也是香噴噴的。少年不知苦滋味。那時,我并不覺得這就是苦,睡在雙層通鋪上的同學都是這樣。我們站著吃飯,說說笑笑,吃完,從布袋里抓幾把米入罐,再往食堂方向去,下頓的米飯就咸菜,依舊吃得樂呵呵的。
三
學校校舍,是傳統式的兩面斜坡蓋頂,整齊有序。三個年級九個班,安置在兩幢教學樓內,余下的幾間就作為老師備課、批改作業的場所。校舍簡易,但那時我們走進中學教室的感覺,宛如置身天堂。
老師是怎么授課?同學怎樣學習?六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來,覺得像六都山坑的溪水那樣源源流淌,自然,親切,可一時又難以名狀其中深層的感悟和蘊含的意味。在這過程中,我腦海中浮現的,有些是課外活動的生動情景。
記得讀一年級的時候,忘了為紀念或慶祝什么,學校組織文娛活動。我們自帶板凳,排隊陸續進禮堂,腳下帶有黃土的芳香。大家有序坐定,校領導一番話后,節目就一個接一個上演。那時,在我的心目中,高年級同學顯得老練、成熟。有位來自楂林那邊的男生,扮演老農,身扎腰巾,手捏竹質煙斗,彎腰弓背,臉上顯得些許幼稚,胡須隨著他沉重的步履抖動,上場開腔唱道:“我老漢今年五十五,耳聾眼花腰又酸……”我們這幫孩子氣息甚濃的同學,見到這等與生活有段距離的老農形象,不禁笑出聲來。時光流逝,生活上好的今天,五十五歲年齡,人們自詡還是青年。學生自編自演的節目,如同其他文學藝術作品一樣,留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就在這場演出中,我們看到代數老師俞萃能的武術表演。俞老師的代數教得很棒,但萬沒想到,他那小小的個頭,在舞臺上騰跳踢打,揮灑如風,有著那么強大的內在能量!他平時不顯山不露水,卻備受我們敬愛。還有一個節目記憶猶新,就是高年級同學演出的越劇《十八相送》。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梁山伯與祝英臺情意綿綿的藝術形象。人物還沒出場,就聽到了幕后深情的合唱:“三載同窗情如海,山伯難舍祝英臺,相依相伴送下山,又向錢塘道上來”。兩位女同學演得很投入,頎長、俊俏的梁山伯形象,還有那清麗的唱腔,至今還在耳旁回響。后來我在金華一中見到她,畢業后她考取了浙江大學。
校區的東北角是片體育場,有籃球場、排球場、百米跑道,除體育課外,每天下午自習課后,大多同學跑到場上自由活動。學校有男女生籃球隊,記得女子籃球隊在縣各中學的比賽中獲過名次。同學們關注的不是名次,而是活動放松心情,增強體質。學校的體育老師,用現在時尚的眼光審視,長得帥氣,他和幾位年輕教師再配有男生的籃球賽,是極其吸引青春芳華的男女同學眼球的。來自鄉村的同學大都穿條深色的短褲,而體育老師和有的青年教師穿的短褲就比較鮮亮,一群光著膀子的師生在場上追趕奔跑,搶球上籃,場外的男女生為他們的一次次上籃得分鼓掌。有次,那位帥氣的體育老師穿白色的薄褲衩,遠遠看他那塊地方有團鼓起的隱隱的黑影,身旁的幾位女同學邊看邊低頭輕輕地說什么,還發出嗤嗤的笑聲,她們是以欣賞的目光看待這群年輕老師的,從越劇團下來的那位女同學,她的微笑格外迷人。
學校每星期還有一節二十分鐘的書法課。我們讀三年級的時候,學校組織了一次書法比賽,三個年級每班選出五名寫得較好的同學到禮堂參與賽事。禮堂內擺好了一排排間隔一定距離的桌子,參賽者自帶筆墨,每人占據一桌,那時的墨水,都是自己預先磨好的。全校師生同場參觀,好像農貿市場上的集會。規定多少時間,已經忘記,只記得我的桌子周圍是密密麻麻走動的人群。那個時候,那個年紀,平時頑皮的我,卻心平如鏡,提筆蘸墨,在校方已備的格子紙上書寫起來。小學四年級前,我用鉛筆做作業,上五年級時我爹給我備了一支中間透明、看得見吸多少藍墨水的鋼筆,可毛筆字,在沒上學時我爹就讓我蘸墨亂涂了。從那時起,我是一直懸臂書寫的。我爹說握筆時手心可放個雞蛋,筆桿頂上可放一疊銅錢。就憑這點基礎,那場比賽張榜公布時,我的楷書張貼在三個年級優選作品的最前面。學校獎給我兩支毛筆和兩本書法練習簿,這是初中三年我獲得的最高獎項。
四
在班里,我年齡最小,個頭瘦小,座次往往在二三排。近年看到同學微信中傳來當年的畢業照,老師坐在第二排,我是站在第三排左側的最邊上。
那時的學習,我至今也沒記起有多用功,但有些事至今仍是羞愧。頭一個學期不知為什么與一位個頭比我大多的男同學爭吵,竟然把他打倒在桌子底下,嘴角流血。班主任是怎樣批評我的,記不得了,但被叫到校長室挨訓,刀刻一樣銘記在心,從此我老實了許多。后來我也反思,我們小山村的孩子,常常受下游大村孩子欺負,拋摔石塊驅趕我們的牛群進入兩村相鄰的草場,溪灘逮魚相遇,有時被他們倒了籠里的魚蝦。我們委屈。后來,我們這幫孩子決定與他們苦戰。再逢這類事,個個勇敢抗爭,幾場對峙,維護了我們放牧捕魚的權利。大村人說小村人野。如果不野,哪有我們在山野、水上的自由!也許從小養成的這股山里佬的野氣,帶到學校,便成禍害。我老老實實地站在校長面前,校長的氣勢像座山那樣壓著我,我默默點頭,承認錯誤,表示以后做個好學生。我們這個年齡段的學生,如同一棵棵樹苗,需要懂行并具善心的園丁收拾,扶植,整枝,澆水,上肥,方能長成粗壯、挺拔、有所期望的模樣。
一個人的成長,與他幼小的生活環境、家庭處境有著密切的關聯。我家兄弟姐妹七個,僅靠祖母、父母勞作養育,集體化的道路,也幫我們這個人口眾多、缺乏勞力的家庭,渡過生存的難關。多子女就讀,家庭負擔沉重。在我的心目中,書,有得讀就讀,沒得讀就下田種地,或破竹做籮,作為孩兒中的老大,自然承接我爹的擔頭。再則,讀好書是學生的本分,不該由老師催促。從小學到初中,學業如山澗水順勢流淌,其間我的頑皮勁,也似山澗水,跌宕起伏,時常濺起不光彩的浪花。
初中階段的學生,朦朧中有所生命情感的意識。男女間時有幾句逗笑,話如煙云,稍縱即過。有人說班里有位男生喜歡一位女生,其實誰也說不清。學校管理嚴格,三年間從沒聽有誰違反紀律。這位女生坐在我前面的位置,她面容白凈,兩眼亮亮的有神采,尤其是臉上的兩個酒窩,笑起來特別好看。有次自習課做完作業,我想逗逗她,舉筆捅了她的背,她回頭,眼神閃著疑問,我做了個怪臉,手指輕輕地撓了兩下自己的臉。在我的家鄉,這動作是說“沒臉皮”或“不害羞,”她微紅了臉,沒生氣,反而報以嫣然一笑。這笑至今還印在我的腦際。
晚上有兩節自習課。在這黃土山崗的曠野上,兩排教室透射的明亮燈光,給靜謐的夜色帶來一派祥和與希望。同學自覺地做作業或預習。做完作業,我將一本從同學處借得的連環畫悄悄地置于桌面旁翻看,正入神的時候,不覺身后有人嗖的一下將它抽走。“呀,班主任!”我驚愕地暗叫一聲。老師從課桌旁悄然走過,教室依然肅靜。我自知違反規定,馬上埋頭看書。幾天后,與同學到老師宿舍玩,在他的書架上看到這本小書,當其他同學與老師交流時,我在背后悄悄地將它藏入衣兜,回來即刻歸還。
有一次上語文課,老師讓我到講臺上用他遞給的粉筆在黑板上默寫什么,當我寫完回頭,老師還在面對同學講述。我的頑皮勁忽地又冒上來,在老師背后咧著嘴,抬起兩拳示意揮打老師的后腦勺。教室里頓時一片哄笑。老師回頭看我,我低頭走下講臺。
老師的胸懷是那么的廣闊,他們一面孜孜不倦的教書,一面又寬容我這樣有著許多缺陷與不足的學生。除了那次打架,老師再也沒有批評我,他們每句溫馨的提示,每個期望的目光,恰如春風,沐浴在我的身上。
五
我感覺,語文老師對我有些偏愛。
至今我不會拼音,那時的我土音更為凝重。讀二年級的時候,杭州大學中文系畢業的黃允金老師布置我參加學校的普通話比賽,我們班還有一位女同學參加,她父母在鐵路上工作,全家吃商品糧,家境優裕,穿戴鮮麗明快,口音純正清亮。黃老師讓我朗誦毛澤東的《清平樂·六盤山》。他一遍遍聲情并茂地示范,我一句句鸚鵡學舌,尤其是“何時縛住蒼龍”的“縛”字,糾正數遍。面對全校師生睽睽的眼神,我是照著老師輔導的聲腔、招式演繹的,下來時,額頭、鼻尖上似有微汗。評比公布時,我班那位女同學獲一等獎,我是二等獎。二等獎有三位,我是不是末位,記不得了。后在軍營幾十年,人家聽我口音就說你是江南人。我對我的普通話始終缺乏自信。
讀三年級時的語文老師是吳士洪,他又是我們的副班主任。吳老師中等偏上的個頭,面色滋潤,烏發后擺,眼神親和、明亮。他與俞萃能老師都算是歲數較大的,但也就四十歲上下吧。吳老師上作文課,我們常常看到他的同題作文貼在教室后面的板報上,同學們擁過去,像一群小豬擠著、拱著爭吸母奶。吳老師的鋼筆字體清秀,文章內容新奇,我們欽佩不已。我們是想從他的范文中尋得某種啟示的。吳老師的字,拐彎處不是棱角分明,而是有點弧度,這好似他的風格,懷柔間化解許多矛盾,談笑中修正我們的偏差。
一次,吳老師布置我們寫《我的理想》。頓時,我胸中有股熱血涌動,吳老師從我身旁走過,我悄聲對他說我想當作家。老師微微一笑,沒有說話。可我真正落筆時卻寫成當一名解放軍,因為當時中國青年報正在批“成名成家”思想。這篇作文,老師判給高分,張貼在教室門口,老師是否有意也讓其他兩個班的同學看看?其實我并不如意,我覺得我沒有吐露真情,老師為什么不問問我怎么不寫當作家了呢?當然,我也沒勇氣向老師訴說衷腸。
上一屆,我們蘇溪初中只有一名學生考上金華一中,我們64 屆考上五六個,這也許是因為以前金華一中是面向全省招生,從我們這屆開始只招金華衢州地區的考生。人們說考上金華一中,一只腳踏進了大學。我是進入金華一中后才改脫過往的毛病,真正把心思用在讀書上的。在金華一中期間,我雖是語文課代表,但到二年級時,我的數理化成績已高出語文一截。我不敢怠慢,山外青山樓外樓,更有強生在前頭。
天下的諸多事,往往不以個人意志轉移。1966年夏天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打破我們上大學的美夢。復課無望,我在學校所在地與部分同學于1968 年初應征入伍。“文革”結束,極“左”思潮有所退隱,“成名成家”思想在我心中如一團柴火那樣又燃燒起來,年歲超過三十五爭取上了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后又考入北京師范大學與魯迅文學院合辦的研究生班。這四年的離職讀書,將我帶入文學殿堂。在這期間,我總是回想起初中的那節作文課,冥冥之中應驗了人生極為珍貴的初衷。
在研究生班就讀時,偶聽一位來自金華的青年作家說,她在浙江師范學院就讀時,語文老師叫吳士洪。我驚疑,幾經盤問,果真是初中時的吳老師。我急切地給思念已久的老師寫信,不久就收到回信,老師要我寄張穿軍裝的照片,我將新近出版的幾本書和照片寄往,老師收到后滿心喜悅,給老伴兒孫傳看,分享作為老師的幸福。老師回寄的賀年卡上端莊地書寫著一聯:“掌筆從戎百世師經天緯地;出將入相一個官奮武撰文。”老師過獎,我存慚愧。老師還寄一聯:“新世紀新賢達新前程似錦繡美;老基礎老根柢老功底如磐石堅。”時光流逝幾十年,老師還念著學生讀初中時的情景,我感恩不盡啊!
六
話又回到文章的開頭。那位挑著籮筐進浙大的表哥,畢業后分配到北京工作,我從部隊基層調到北京的機關后,曾去拜訪,那時他已是解放軍報印刷廠的總工程師。他自豪地說,我們軍報是全北京首家開印彩色版的報紙。到他家,見到佩戴紅領巾的他的女兒,后她考上清華大學,又讀研究生,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氣質優雅的學子,數度主持清華大學大型文藝匯演,被譽為校花。那時,我才感悟我爹要我挑只籮筐上中學的良苦用心。
我曾數次回訪母校,蘇溪中學已遷至鎮旁牛頭山腳石渣礦舊址。原先黃土崗上的學校所在地,辦起了廣播器材廠,后又為紅旗電視機廠,生產出浙江省第一臺黑白電視機。2000 年10 月初的一天,我站在蘇溪中學簡陋的校門前,突然萌生請老作家魏巍題寫校名的想法。魏巍是北京軍區政治部顧問,是位正軍級的著名作家,在文學界、文化界都有很高的聲望。由于援越抗美題材作品的創作與出版,我與他相識,并由他介紹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我們之間始終保持著軍人與文人間的純正聯系。為了我們家鄉的事,為激勵教育事業,我想,他是不會拒絕的。陪同的校長原是語文老師,多年給學生講授《誰是最可愛的人》,對魏巍懷有崇高的敬意。聽我這么一說,他欣然贊同。回京后,我即與魏巍聯系,他真誠而又熱忱地答應,在宣紙上揮毫題寫兩幅“浙江義烏蘇溪中學”,讓我挑選。我用掛號將兩幅題字均寄給校長,請母校制作時選用。翌年年初,我又請軍委副主席、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遲浩田題寫了“蘇溪中學”四個大字。后我回家探親,校長、書記聞訊,專程來看望。我看到魏巍的題牌掛在學校正門的立柱上,醒目,大方,他們還將魏巍題寫的“蘇溪中學”四字制成校徽,佩戴在師生胸前。遲浩田的題字,制成碩大的金色字樣,閃爍在高高的教學樓上。
那幾年,我每次回去,學校老師和家鄉的人們總要提及這事,其實,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魏巍、遲浩田的成就與名望,在人們的心目中占據敬仰的地位。老師告訴我,他們的題名,對于家鄉學子的激勵,是難以用言語來表達的。
如今,我鄉音未改,鬢毛已衰,坐擁書房,面向故鄉,上學時的情景常常涌上心頭。中學的學習生涯,連接我的過去和未來。對于這個階段的回味與念想,近日微信中看到的幾句話,正好描摹出此刻我的心境:春風待我如初戀,我待春風似少年。莫嘆飛花顏易老,此心歸處是從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