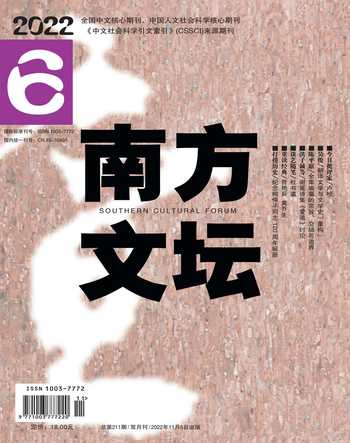異國體驗與文化行旅
揭示早期新詩人的異國文化行旅與新詩寫作的關系,當屬“新詩發生學”的研究范疇。近年來,圍繞新詩發生學的研究已具規模,形成“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共生的學術態勢。多數研究者注意到新詩人普遍具有的海外經驗,將其視為作家創作的背景資料,但較少從新詩誕生的推動性要素入手,圍繞海外體驗與新詩生成的關系展開深入探討。實際上,海外經歷不僅增長了詩人的學識,還磨煉了他們對多元文化樣態的感知能力,激發了行旅主體的思想演進和觀念更新。他們扮演著觀光客、旅行家抑或漫游者的角色,沉浸在異國的文化情調和文明氛圍之中,在追求新鮮理念、觀察海外風景的同時,也將觀景體驗與行旅感受作用于新詩觀念的生成過程,創作了大量描繪異國形象、記錄行旅游蹤、抒發文化感思的作品。可以說,早期新詩的創作實績與海外作家的行旅體驗密切相關,將“異國體驗”或“文化行旅”作為研究方法,持續觀照新詩域外抒寫的意義乃至走向,或許能夠串聯起百年新詩發展中的諸多問題,拓展我們對當下詩歌的認知視野。
一、旅行之能效:情境意識與想象力的
雙重提升
在域外旅行中,早期新詩人體驗到了現代意義上的時空轉換,獲得大量新銳的感覺經驗。如李怡所說,在詩人的域外體驗中,最為重要的是“自我空間意識的變化”“是自我與世界的‘關系的調整”①。誠如斯言,跨洲越洋的行旅,使詩人親身參與到世界性的時間與空間架構之中,他們對陌生的異域社會和文化產生了全新的體認。特別是在出行途中,詩人位于文化空間的疊合點上,新奇的思緒時常紛至沓來,由此誕生出一系列“道中所作”或是“寫于某某輪船”“寫于某某海上”的作品。郭沫若的《海舟中望日出》、康白情的《一個太平洋上的夢》《天樂》、孫大雨的《海上歌》、周無的《過印度洋》、邵洵美的《漂浮在海上的第三天》、徐志摩的《再別康橋》等作品,都是遠渡留洋或是歸國途中的即興之作。在充滿變動的行旅過程中,交通體驗給予詩人難得的契機,便于他們在與既往經驗拉開足夠的距離之后,利用相對封閉的環境盡情展開詩思。同時,現代交通體驗還提供給詩人全新的觀物視角。胡適曾寫有《飛行小贊》一詩,敘寫他乘坐飛機觀看城市風景的感受。雖然詩歌的寫作地點并非海外,但詩人的觀物方式在當時的旅行抒寫中非常具有代表性。乘飛機由高空觀景,人與風景便不再是以往那般平視的關系,而形成了人對風景縱向的、由上自下的俯瞰視角。人眼檢視到的風景成為地圖般的微縮景觀,瞬間就被觀察者收入眼中,這自然和前人那種動輒數日方能覽遍城市的體驗截然不同了。
觀察視角的改變,審美視野的延伸,導引新詩人步入全新的時空情境。他們的文化心理大都經歷了“鄉人—國人—世界人”的衍變,因而確立起超越前代文人的全球意識,進而觸發了想象思維的革新。不過,單就風景體驗而言,負笈異鄉的寫作者大都受傳統人文觀景旨趣浸染,他們最初的海外旅行仍以自然風光為目標。諸多詩人的交集聚合在“游湖”上,像王獨清和蘇雪林,都有游覽法國來夢湖的經歷。前者寫下詩歌《來夢湖的回憶》,后者則把游湖見聞在小說《棘心》中加以呈現。至于胡適、陳衡哲、任叔永等留美詩人頻繁的游湖之旅,尤其是“凱約嘉湖詩波”,更是成為引起新詩變革的催化性因素。留美期間,俞平伯與好友聞一多同在科多拉多學習,經常相約游覽仙園、曼尼圖山、七折瀑等景點,還曾選擇自駕游出行。留日期間,郭沫若、田漢、成仿吾、張資平等文人曾在房州海濱度假,同樣留學日本的穆木天、陳豹隱、鄭伯奇則寄情于鄉野情趣。他們游走在靜謐的夜空之下、山海之間,體悟著人與萬物的和諧相生,文字間也氤氳著幽婉清新的韻味。在早期新詩人的精神世界里,以自然審美為主導的域外游歷疏解了他們對海外環境的陌生感,使他們可以較為順暢地適應異國的氛圍,進而釋放想象的靈性,為觀察視野的進一步打開醞釀著可能。
伴隨著行旅體驗的加深,詩人們逐漸發現了風景的多重樣貌,并將這種體驗內化至新詩情境的打造過程。以郭沫若為例,游歷博多灣的風景激活了詩人“我的血和海浪同潮”②的生命體驗,1919年9月,詩人第一次遭遇“二百十日”大型臺風,目睹變化無窮的大海“猙獰”的一面,他對大自然的認識和觀察的視角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波濤翻滾的景象給予詩人力量的啟迪,悠閑寧靜的“如鏡的海面”“光海”“晴海”,還有“博多灣水碧琉璃,/銀帆片片隨風飛”③的“靜態”風景被《立在地球邊上放號》中恣情舒展、狂放不羈的流動風景所取代。詩人為此自釋:“沒有看過海的人或者是沒有看過大海的人,讀了我這首詩的,或者會嫌它過于狂爆。但是與我有同樣經驗的人,立在那樣的海邊上的時候,恐怕都要和我這樣的狂叫罷。這是海濤的節奏鼓舞了我,不能不這樣叫的。”④從日本的海與風中,詩人覓得“宇宙萬匯底印象”與“靈感”⑤的微妙聯絡,以情感的自然流露作為使新詩體相兼備的方法。可見,風景由靜到動的變化,改變了詩人述景遣情的速度感,為新詩情境植入了“動的文明”之特征。詩人找到了新詩的生成法則,并以其“壓不平的活動之欲”⑥,把靈感寄托于萬丈的光芒、新生的太陽、狂跑的天狗等意象上,詩風為之一變。
從真實的旅行觀察中,郭沫若發現了“變動”的風景,進而抓住了詩境提升的機遇。與這種源自視覺層面的體驗相比,還有一部分詩人汲取了域外文化中對風景業已形成的知識資源,以此作為認知世界的“裝置”,從心理和想象層面讀解現實、構筑詩境。例如,在歐洲的風景美學中,希臘與阿爾卑斯、北歐與南歐均具有穩定的象征意義,構成西方文學的風景想象傳統。前者代表典雅之美與雄壯之力,后者則對應著純粹的自然美和奔放的人性美。這種西方風景想象的固型化傳統與中國詩人發生精神聯系之后,一定意義上拓展了新詩人認知風景的視界,便于他們深入而具體地理解當地的文學與文化。在信函中,郭沫若曾與友人探討無錫惠泉山的風景是否具有“希臘的風味”⑦,還嘗試以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北歐美、南歐美觀照他所看到的日本風景。彼時,郭沫若并沒有到過歐洲,卻以歐洲的“風味”理解現實的風景,著實值得品味。再如徐志摩、王獨清、郭沫若等詩人尚未去過埃及,卻都留有言詠埃及文明的詩篇。1922年9月,徐志摩乘船經過地中海時,寫下《夢游埃及》和《地中海中夢埃及魂入夢》兩首。古埃及的精靈“點染我的夢境”,“尼羅河畔的月色/三角洲前的濤聲/金字塔光的微顫/人面獅身的幽影!/是我此日夢景之斷片,/是誰何時斷片的夢景?”⑧這首詩是典型的“神游”之作,切合了中國詩歌的傳統想象模式。詩人對埃及的深奧遐想,或者說專門針對埃及的“神游”,恰恰也是西方詩歌的想象母題,在濟慈、拜倫等詩人筆下已吟哦不絕。埃及的國家形象和歷史興衰,融匯了西方人對古典文明的神秘輝煌與頹敗蕭索的宏大聯想。以異國的埃及作為觀察的“裝置”,徐志摩捕捉到了西方詩歌維度中的這條線索。借助中國詩歌“神游”的方式,他構建起超驗性的情境。智性的思考與浪漫的幻想,都被詩人融入“文學夢”的內部空間,彰顯著他對西方風景美學和中國古典詩學兩種經驗的駕輕就熟。亦即說,詩性的旅行培養了詩人綜合性的想象能力,他們憑借對現實風景的凝視,對風景“知識”的攝取,重新編排語象元素,整合文化記憶,由此開啟了對民族文化心理和自我身份意識的反思,也鍛造出了嶄新的、屬于新詩的想象情境。
二、海外行旅抒寫之于新詩發生的意義
域外風景的洗禮,異邦文學的滋養,打開了詩人的文化視野,他們獲得了多重感官的體驗,并將這種體驗匯聚于文本,以詩歌的形式加以表現。像郭沫若、胡適、徐志摩、宗白華、聞一多、穆木天、李金發、王獨清、蔣光慈等早期新詩人,都把行旅視為重要的寫作資源,創作出一系列海外特質顯揚的作品。還有一些作家未將行旅抒寫視為重心,卻也留下了異域氣息濃重的詩篇。如冰心《倦旅》、陳豹隱《和東林定湖同游東京郊外》、陳衡哲《散伍歸來的“吉普色”》、成仿吾《海上吟》《歸東京時車上》、馮乃超《不忍池畔》《歲暮的Andante》、傅斯年《心悸》《心不悸了!》、傅彥長《回想》、康白情《舊金山上岸》、梁實秋《海嘯》、梁宗岱《白薇曲》、劉半農《巴黎的秋夜》《柏林》、劉廷芳《過落機山》、陸志韋《九年四月三十日侵晨渡Ohio河》、羅家倫《赫貞江上游的兩岸》、邵洵美《To Sappho》、孫大雨《紐約客》、田漢《銀座聞尺八》《咖啡店之一角》、王光祈《去國辭》、郁達夫《最后的慰安也被奪去》、俞平伯《東行記蹤寄環》《Baltimore的三部曲》、張資平《海濱》、鄭伯奇《落梅》、周太玄《過印度洋》、周作人《東京炮兵工廠同盟罷工》等文本,形成了域外抒寫的匯集效應。回望早期新詩人的域外寫作,它從海外文化的視角影響著新詩的發生與建構,為新詩賦予了別樣的文學氣質,其意義至少在三個層面有所體現:
一是在對風景的塑造中,發掘出“異國”意象的多維內涵,將“異國”從形象上升到詩學主題的層面。“異國”是詩人體驗現實行旅的具體場域,也是他們釋放現代意緒的客觀對應物。異國游歷的獨特經驗,使寫作者的世界認知實現了從抽象到具體的深層轉換,為其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作為詩學主題的“異國/異鄉”熔鑄了詩人對故土的懷戀、對游子身份的憂思、對新銳文化的好奇、對域外人文精神的渴望,以及對都市文化投合與疏離并存的悖論式認知態度。同時,無論是出于自覺還是無意識,他們都不約而同地立于美學層面,為“異國”意象傾注了大量心力。如李金發、王獨清那樣,作家把歐洲的城市意象引入象征主義詩歌,其文本色調的朦朧與文字的奇詭,均超越了傳統詩歌的修辭模式。從新詩歷史發展維度考量,早期新詩人發現了異國的奇異風景(尤其是第一次進入中國文學視域的國家意象),并根據他們各自的知識儲備與寫作習慣,在借鑒域外詩學資源的基礎上,普遍對異國形象進行了“本土化”的加工、改寫,既充盈了早期新詩的意象空間,又豐富了新詩的美學構成。
二是借助在異國游走的文化遷徙感受,建構起新詩中第一代“漂泊者”形象序列,觸發后繼詩人展開對“孤獨”情結的集中抒寫。置身陌生的文化環境,游子們脫離了對慣習中的時間和空間的依附感,他們受到異域文化的強勢沖擊,對生活的把控感愈發脆弱,便很有可能走向對現實乃至自我認知的迷茫。這種漂泊體驗,幾乎每一位出游的詩人都經歷過,他們往往寄情于詩,抒寫漂泊者的孤獨與空虛,眷戀自己的故土和母國,此類詩篇不勝枚舉。留美的聞一多便說自己是“不幸的失群的孤客”和“孤寂的流落者”⑨。留日的成仿吾則慨嘆“故鄉何處?/讓我回去了罷。/一個人行路無依,/我心凄慘,我愁我怕!”⑩。無論是“不幸”還是“凄慘”,均是出洋詩人的典型心理特征。他們的詩文里總會出現一個游走中的“漂泊者”形象,其抒情意緒大都指向“生之迷惘”帶來的冷漠與哀愁。在陌生的、與前文化結構斷裂的異國時空中,社會主流價值觀與倫理觀的巨變,使詩人的“本我”與“自我”發生沖撞,抒情主體因拘謹而倍感不安,于是他們通過內向性的自我言說,表達身處異鄉的迷惘和憂思,以及敏感的知識分子在異國城市中獨自徘徊的苦楚、疲勞與頹唐,其間多氤氳著感傷情調和“倦游”氣息。
透視域外文本中的“漂泊者”形象,他們的漂泊心緒大多于旅途中誕生,尚未從“迷失自我”的現象游移到它的本質,抵達存在主義意義上的人格寂寞。不過,也有一些詩人在漂泊者視角的引領下,找到了發現自我的有效途徑。如劉半農的《夜》11,便是一首注重將漂泊經驗轉化為正向價值的詩歌。1920年的一個夏夜,詩人從倫敦大學學院乘公交車歸家,抒情者在夜間“獨自占了個車頂”的時空體驗,使他遠離了嘈雜的日間人群經驗。他從“人群”之中抽身而出,在巴士上意外獲得了屬于自我的精神空間。海特公園的樹木、沉寂的市聲和漸次熄滅的街燈,與詩人的寂寥感形成同構。經由漂泊體驗,他竟發現了“偉大的夜的美”,從而將個人的孤獨引入宏大的審美境界。再如創作《沙揚娜拉》《再別康橋》等詩歌時,徐志摩以凝聚式的構思方式,品味著審美意義上的“孤獨”。在漂泊的行旅中,詩人沉入對自我的再次發現。以“孤獨”為起點,現代詩歌的精神主體有了多元的情感方向。后來者如戴望舒、廢名、林庚、馮至等人,皆沿襲了這一審美向度,使新詩對漂泊者的抒寫形成了穩定的脈絡。
三是在建構“體驗的現代性”之過程中,與域外詩學形成共時性的交流和對話。遠洋跨洲旅行條件的改善,將世界各地聯結成巨大的整體,中華傳統的地域文學由此獲得了融入世界文學(以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為主體)發展脈絡的機會。中國新詩人可以擁有與西方現代詩人相同的觀察視野,并通過詩文與之形成互文式的潛在對話。比如,當人們談及里爾克的名篇《豹》時,大都將巴黎植物園中的這頭困獸理解為詩人對人類命運的自謂。困獸與牢籠,人性與物質社會,達成了互喻的邏輯聯系。從旅行視角考察,我們會發現中國詩人竟然也擁有和里爾克一致的游歷體驗。1923年10月,劉半農游覽巴黎植物園后,寫下散文詩《熊》,詩中寫到一只向游人乞食的白熊,還有另一只正在生病的黃熊。抒情者同情這兩只處于困頓中的猛獸,但它們那“鐵鉤般的爪與牙”以及“火般紅的眼”12,又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懷有憐憫之心的觀眾——一旦這些病獸接近了人,無論它們是否處于饑餓和病困,都決不會像人同情它們一樣去親近人類。劉半農表達了對人性和獸性的反思,雖然與里爾克的觀察物象和思考角度殊異,但他們在猛獸籠前駐足停留的那一刻,便在同一個地標留下了空間疊合的印跡。詩人們對人性做出的不同維度的思考,使之在保持游歷行為同一性的過程中,又各自開啟了屬于他們的精神空間。無論是劉半農還是里爾克,巴黎之于他們皆為異鄉,他們都是跨越了母語的行旅者,在共同的觀看角度上獲得了對人類生存境遇的清醒認知。共同性視角的獲得,使王獨清、李金發與波德萊爾一樣遁入巴黎的都市,使徐志摩、邵洵美與拜倫、濟慈一道緬懷古羅馬的榮光,使郭沫若、穆木天、田漢和日本現代作家一起涌入大正時代“登山熱”的潮流。借助類近的“物觀”體驗,抒情主體進入異國風景的結構內部,形成旅行者的“凝視”眼光。他們沉醉在異國經驗之中,憑借對“震驚”感受的吸收與轉化,建立起足以標明存在感的精神形象。這種觀察異域的文化姿態始終存在于詩人的抒寫實踐中,并匯集成為他們讀解異域、認識自我的一個焦點,也為中西詩學的交流互滲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三、“新與舊”的并行和“詩與文”的互文
域外行旅之于新詩的激發意義,吸引人們主動關注行旅者的精神世界,細致洞察旅行文本的詩學空間。當我們從域外行旅角度考量新詩發展時,還應該注意保持一種客觀性,將現代中國新詩視作統一體,而不是把抒寫域外體驗的詩歌和其他產生于國內文化語境的文本作為相異的認知對象。在本文已經形成的一些結論之外,關于域外行旅與新詩乃至新文學發生的相關話題仍有繼續討論的空間,有些問題尚待深入掘進。比如,新詩在不斷發展自身的同時,接續古典文學的文言體詩歌并沒有完全告別歷史舞臺。尤其是舊體記游詩,它依然活躍在“五四”以降的新文學空間內,演繹出連貫的詩學線索。這正說明古體詩與新詩對行旅經驗的抒寫并非簡單的“以新易舊”,新詩不斷對行旅經驗進行著想象和表現的“現代性”轉換,這種轉換同樣存續于舊體記游詩中。在白話文學占據主流的新文學語境里,仍有一部分文人延續了晚清域外紀游文學的寫作傳統,在舊體記游詩的路徑上執著拓進。如20世紀二三十年代,詩壇涌現了吳宓的《歐游雜詩》、蘇雪林的《旅歐之什》、李思純的《巴黎雜詩》《柏林雜詩》、胡先骕的《旅途雜詩》、呂碧城的《信芳集》等紀游詩集,都以舊體寫成。以蘇雪林為例,1921年,詩人赴法留學,期間曾與友人一起旅行,“看盧丹赫山,訪古堡,觀石窟瀑布,詩興忽飚發,數日間為長短十余首”13。詩人將歐洲的奇山異景、名勝古跡乃至面包咖啡、公園噴泉都融入紀游詩作中,其文本脫胎于晚清域外記游詩“新材料入舊格律”的實驗傳統,又深受“五四”文化浪潮和異域體驗的影響,文本情感真摯,會通古今,具有深厚的文化和美學特質。像蘇雪林這樣兼用文言與白話進行寫作的新文學家并不少見,如郭沫若、俞平伯、郁達夫、劉半農等,都在從事新文學寫作之外,常以古體記游詩復歸傳統文人情懷,將異域風景化為中國情調,抒發懷古幽思,吐露惆悵鄉情。郭沫若曾說自己“在學生時代對著博多灣時常發些詩思”,“在用白話寫詩之外,也寫過一些文言詩”14。1914年8月,他第一次領到留學生的官費(獎學金),立即選擇去房州度假。在無風的天氣下,北條的鏡之浦如明鏡般清澈平靜,此般風景帶給詩人極大的喜悅,遂作《鏡浦真如鏡》《飛來何處峰》《白日照天地》三首五言絕句,以騁游歷欣悅之情。俞平伯乘船赴美經日本長崎時,作有新詩《長崎灣》(屬于組詩《東行記蹤寄環》第二首)和舊體詩《長崎灣泊舟》,這種新舊“并行”的現象,很值得仔細分析。
當新詩人運用白話材料構筑語言空間時,是何種因素促使他們不時回歸傳統的文言抒寫?或許正是獨在異鄉、愁緒難解的文化憂思,激活了詩人思想中的古典文人情懷。異邦的風吹草動、花鳥蟲鳴、一點一滴都足以撩動他們的情思,使其從舊體詩詞中找尋情感上的慰藉,即所謂“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15。胡適有過如此的感受,說他“一到了寫景的地方,駢文詩詞里的許多成語便自然涌上來,擠上來,擺脫也擺脫不開,趕也趕不去”16。穆木天也曾言及自己在京都的經歷,說他和鄭伯奇由石山順瀨田川奔南鄉時,看到沿途的瑰麗風光,大家一致認為“當地景致用絕句表為最妙”,因為“自由詩有自由詩的表現技能,七絕有七絕的表現技能,有的東西非用它表不可”17。這“有的東西”究竟為何物,或許正是潛隱在詩人心中的田園精神和懷鄉情結。當異邦的風物感染到詩人后,他們便情不自禁地將自然作為精神的寄托,把山水變成了另一重“自我”的載體,從異國的自然風景中,與古典中國的山水精神相逢。特別是當他們遭受到生活中的不如意,如感情的茫然無措抑或理想與現實的隔閡時,異域山水就成為他們愉悅身心、治愈創傷的一劑良藥。詩人紛紛以樂游山水的心態閱覽風光,追求輕盈灑脫的美學意境,延續了古典“游”文化的傳統。同時,他們的文本又納入了新鮮的視角和現代的情感,可謂用文言文寫作的“現代的新詩”18。由此看來,舊體詩與新詩之間并非截然對立,兩者有著共通的精神背景,也具有各自存續發展的空間和路徑。新文學中的舊體記游詩推動了古典詩學的現代衍變,也為新詩提供了有益的參照。
除了域外記游詩在白話與文言兩個向度上“新與舊”的并行,新詩人的域外行旅抒寫往往還存在“詩與文”的互文。像郭沫若、徐志摩等詩人,常常將一次旅程體驗用詩和散文的方式交織呈現。郭沫若曾寫有散文《自然底追懷》,詩人回憶了早年行旅作詩的經過,以及在房州北條洗海水浴、游歷岡山與東山、與成仿吾往東島旅行等經歷。散文文體的充裕體量,可以涵容詩人在新詩體式中難以述盡的情緒,全面闡釋行旅的具體背景乃至景物的微末細節。再如徐志摩的《雨后虹》《我所知道的康橋》,兩篇散文都寫到詩人從幼時起對自然的熱愛,并詳細記錄了他在康橋邊按照由遠及近的順序觀景的過程。文字中表露出的對自然之美的傾慕,對天邊云彩的迷戀,對康橋建筑的贊頌,與詩歌《康橋西野暮色》和《再別康橋》等名篇形成互文。只有讀了徐志摩的散文,才能理解他詩歌里描寫的乃是康橋實景,也能深切感受到文本內景物漸次排列的秩序,正是來源于寫作者在散文中描述的那種“實際觀測”的體驗。如果比照徐志摩在特定旅行中的散文和詩作,則可梳理出一系列形成對應的文本:如散文《歐游漫錄——西伯利亞游記》對應詩歌《西伯利亞》,散文《翡冷翠山居閑話》對應詩歌《翡冷翠的一夜》……比較這類作品,會發現詩人的“獨行”體驗正是借助了兩種體裁、雙向路徑,方才得以自足。從新詩初誕期開始,以“散文+詩歌”記錄旅行的寫作模式被越來越多的文人借鑒,形成了廣泛的示范效應。多數情況下,詩人側重通過詩歌抒發觀景時產生的瞬間思維感覺,在個體化的象征空間內打磨語詞,現代氣息濃重;而當他們試圖詳盡記述旅途中的交通和景物信息,乃至反思國民精神或文化差異等現實問題時,又會選擇散文的體式,以之承擔更多的信息功能和社會功能。我們往往要兼顧詩歌與散文(游記)文本,才有可能對詩人的行旅想象確立全面、立體的認識。
四、異國行旅:百年新詩的又一線索
新詩現代性的重要環節是體驗的現代性,通過異國體驗和文化行旅,詩人的知識結構、文化心態、身份認知、述景策略等要素,都作用于“體驗現代性”的成長過程,并進一步助力了他們的寫作,尤其是在作家的現代感受力生成、詩學精神主體形成、美學體系構成等方面表現尤甚。閱讀富含異國情調的新詩文本,我們不僅看到了紛繁多姿的異邦風景,也捕捉到兼具行旅者和文學家身份的詩人對域外行旅做出的差異性反應(包括心理的與文學的)。這些反應在不同代際的詩人筆下持續累積,不斷強化,向未來延伸,在現實主義、現代主義乃至先鋒性、現代性之外,形成了一條綿長清晰的線索,演繹出百年新詩的重要傳統。
縱覽新詩發展歷程,以行旅體驗為核心的異國文化要素對新詩的影響主要集中在五個時段。首先是本文著力探討的新詩發生期。現代詩人乍履他鄉,所觀多為陌生風景,嶄新的文化要素和知識因子滲入他們的認知空間,不斷滌蕩著陳舊的觀念積習,使作為實踐主體的抒情者具備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的觀察視角和情感體驗。伴隨著域外要素對新詩影響的深入,從20世紀20年代后期開始,如艾青、戴望舒、馮至、辛笛等詩人,也將游學海外的所見所感融入詩歌創作。他們大都承續了早期新詩人抒寫異國的思維路徑,其觀察風景、組織情感的方式也存有共通:或是捕捉對異域物質文明“歌頌”與“拒斥”并置的文化認識,抒發漫游者的孤獨意識和懷鄉情思,或是將觀察海外風景的旨歸定位于對故國文化的再次發現,文本中的風景結構和詩義結構大都可歸入“現實——記憶”相對照的組織模式,潛隱著海外游子對現代化國家應然形象的期待。
隨著戰時背景對域外行旅造成的阻滯,直到1949年后,詩人海外出行的規模才有所恢復。受限于內部條件和國際環境的種種限制,私人出游被官方機構主導安排的“集體出訪”取代,圍繞特定主題的群體創作,成為1949—1966年間詩人參與域外交流的主導形式,這也構成新詩域外行旅寫作的第三階段。如郭沫若、艾青、冰心、馮至、蕭三等詩人,都在參與國際會議或是集體訪問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流露出對個人立場和生命意識的潛在渴望,與現代文學中崇尚個體發現的思想傳統形成暗合呼應。這種意識主體與經驗主體的內在矛盾,在馮至、艾青等作家那里表現得更為明顯。如馮至利用再次赴德的機會反思里爾克對他的精神浸染,艾青也在出訪南美的旅行中,回歸了沉潛許久的“內面”自我。他寫下的《在智利的海岬上》《礁石》等詩篇,視野寬廣,洞察力強,兼具藝術和思想價值,成為“十七年”詩歌的文本典范。
新時期之初至20世紀90年代末,異國行旅文化在新詩中強勢復蘇。一方面,大量的復出作家以官方身份參與海外訪問,寫下一系列“海外風光詩”或“異域抒情詩”。如艾青出訪德國、奧地利、法國、美國、日本等國家,留有《特根恩湖的早晨》《維也納的鴿子》《威尼斯小夜曲》《紐約》《銀座》等數十篇作品。其述景、詠懷的方式,基本契合了詩人在當代文學初期的思維路徑,在“歸來”作家中具有很強的代表性。另一方面,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國際旅行政策日益完善,為私人的出行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像楊煉、北島、多多、嚴力、張棗、宋琳、翟永明、王家新、歐陽江河等詩人,都有長期旅居海外的經歷。一些人選擇了定居海外,或是以教師、駐校詩人等身份,頻繁穿梭于中西之間,獲得了與本土文化語境“互視”的跨文化視野。諸如多多的《阿姆斯特丹的河流》《在英格蘭》、楊煉的《面具》、北島的《旅行》《過節》《磨刀》等詩作,書寫下文化遷徙者漂泊孤懸的生命狀態,以及他們對母語的懷戀、對文化中國的緬想、對自我身份的持續辨認。潛藏在“異國風景”背后的,是國族、無根、戀地、在地、西方、東方這類話題。借助“海外”的文化鏡像,新詩的話語空間得以延展。
21世紀以來,域外行旅文化與新詩展開了新一輪的互動。今天,人們無須竹杖芒鞋,便能快捷地穿行在大洲之間,參與到世界旅行的大潮中。由地理位移帶來的文化遷徙,構成了文學寫作者必要經歷的共性體驗。“在一個號稱全球化的時代,文化、知識訊息急劇流轉,空間的位移,記憶的重組,族群的遷徙,以及網絡世界的游蕩,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經驗的重要面向。旅行——不論是具體的或是虛擬的,跨國的或是跨網絡的旅行——成為常態。”19“遠涉重洋”“背井離鄉”的“苦旅”意味疏淡了,“文化鄉愁”也逐漸退出了域外抒寫的情思空間。詩人們不再將旅行視若“揚棄舊我、再造新我”的唯一契機,他們多懷有一種面向未來的文化心態,更愿意從域外風景中汲取即時性的經驗,隨時展開移動的跨界想象,以便更為自由地調動記憶“文件”,進行極具開放性的編碼、合成,從而使詩歌情境的層次趨向立體多元,也在全球化語境中抵達了人類文明意識的多重樣態,為文本植入了世界主義的元素。
總之,作為早期新詩研究的一個視角,異國體驗與文化行旅是新詩發生的推動性要素,值得定向深入考察。從新詩歷史發展的角度審視這一要素,可見它與中國新詩的發生、發展形成同步,并在新詩運行的每一個重要節點上都留下了堅實的印記。通過串聯、辨析異國行旅要素在這些節點上的特征,可以揭示出各對應點之間組構、融合的內在邏輯,串聯起新詩發展史中的述景策略衍變、精神主體建構、風景美學延展、比較視野生成等一系列重要的問題,加深我們對新詩的理解。
【注釋】
①李怡:《日本體驗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第70-71頁。
②郭沫若:《浴海》,載《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70頁。
③14郭沫若:《追懷博多》,載《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第335、335頁。
④郭沫若:《論節奏》,載《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第357頁。
⑤郭沫若:《三葉集·郭沫若致宗白華》,1920年1月18日,載《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第14頁。
⑥聞一多:《〈女神〉之時代精神》,載《聞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第110-111頁。
⑦郭沫若:《創造十年》,載《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第125頁。
⑧徐志摩:《地中海中夢埃及魂入夢》,載韓石山編《徐志摩全集》第4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第75-76頁。
⑨聞一多:《孤雁》,載《聞一多全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第79頁。
⑩成仿吾:《故鄉(Religious emotion)》,《創造季刊》第1卷第1期,1922。
11劉半農:《夜》,載《劉半農文集》,線裝書局,2009,第228頁。
12劉半農:《熊》,載《劉半農文集》,線裝書局,2009,第281頁。
13蘇雪林:《燈前詩草·自序》,臺灣正中書局,1982,第2頁。
15張懷瑾:《鐘嶸詩品評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第96頁。
16胡適:《老殘游記·序》,載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584頁。
17穆木天:《譚詩——寄沫若的一封信》,載蔡清富、穆立立編《穆木天詩文集》,時代文藝出版社,1985,第262頁。
18周作人在評價沈尹默由新詩轉向舊體詩寫作時,指出他的舊體詩與普通的新詩只是“內涵的氣分(氛)略有差異”,實際上“他的詩詞還是現代的新詩”。參見周作人:《揚鞭集序》,《語絲》第82期,1926年6月7日。
19王德威:《文學行旅與世界想象》,載《懸崖邊的樹》,譯林出版社,2019,第155-156頁。
[盧楨,南開大學文學院。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當代作家域外出訪寫作研究(1949—1966)”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21BZW147;南開大學科研資助項目“域外行旅與中國新詩”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ZB2200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