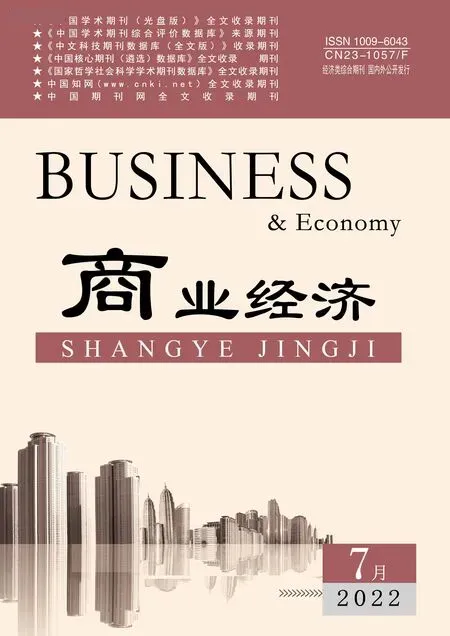數字資本的發生邏輯
季海波
(南京信息工程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江蘇 南京 210044)
數字資本誕生于資本邏輯和數字技術相互滲透、結合、強化的歷史演變軌跡之中,它的出現加快了資本的轉化與競爭,催生出“一般數據”成為資本家競相爭奪的資源。隨著科學技術的興起,數字資本已廣泛參與主體的日常生活,大資本家掌控著一般數據用來壓榨人的剩余價值,造成人的異化,比如亞馬遜、微信、淘寶、抖音等軟件平臺虛假自由宣傳下的隱性控制。對此,探究數字資本發展的內在邏輯,把握其產生的社會現實,有利于找到揚棄數字資本的新路徑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
一、數字資本產生的社會基礎
以生產力與生產技術為劃分標準,人類社會歷經數個發展階段,從最初的蒙昧期、野蠻期,到后來的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經過幾千年的發展當下則已經邁入信息時代,資本從誕生之日起便隨著社會變遷不斷轉換形態,技術創新和社會革命使得數字資本應運而生。
工業社會利用機器大生產改變自然環境,使自然符合人類發展利益需求,創造出輝煌的工業文明。此后,到20 世紀中葉,電子信息技術被廣泛應用于生產,以信息科技為基礎的技術范式重構著社會生產生活網絡,催生出新的社會形式與社會樣態——后工業社會。相較于以機器技術為生產基礎的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呈現“以信息為基礎的‘智能技術’同機械技術并駕齊驅”的時代特征。
隨著信息技術革命的進一步發展,當前社會已進入數字革命階段,這也正是克勞斯·施瓦布筆下不斷進行論述與分析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信息網絡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與規模重構生產生活,尼葛洛龐帝提出的“數字化生存”時代、大雄建村提出的“后信息社會”(數字社會)悄然降臨。相較于信息社會是以信息技術作為生產的輔助工具,依然遵循著物理世界的流程化思維;數字社會卻是通過信息技術和數字媒介建構社會生活的本體,形成以數據為基礎的數字化思維和秩序。因此,信息知識的內涵出現了一定改變與調整,它不再是生產過程中保持中立性質的技術網絡和資本要素,信息的生產、存儲、交換已然關系到個人生活、企業生產、國家發展的各個層面,“計算不再只和計算機有關,它決定我們的生存”,算法邏輯重構了數字社會的生產生活邏輯,數字資本形成并呈現出與前一個階段截然不同的新特征。
總之,資本的發展是生產力和技術水平變革的歷史必然,縱然資本運行形式有了質的變化、內容存在新的量變,但其始終遵循著資本邏輯的本質沒有變,資本的謀利本性在21 世紀的今天乃至未來都將以數字資本的形態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橫行。
二、數字資本產生的技術基礎
科技革命給社會帶來超大變革,這是因為,科技推動下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到達一定階段后卻又會與現存生產關系產生無法調和的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不再具有積極作用反而會形成桎梏生產力繼續發展的枷鎖,那么新的革命必然降臨。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化,上層建筑也必然會發生變革,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經歷了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沖擊,它們為資本的發展奠定了技術基礎。
第一次科技革命,形成了資本主義社會,機器大規模用于生產開啟人類工業化大門,產業資本取代“在歷史上最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的商業資本成為蒸汽革命時代的典型資本形態。機器的廣泛運用改變了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機器代替手工,人們雙手得以解放。在生產過程中,工業資本以物質生產力為社會存在基礎,構建了一個“貨幣-生產-商品”的資本形態循環,社會總資本由此具備了豐沛且暢通的流動性,完成資本增殖的“使命”。
第二次科技革命,近乎同時發生在幾個先進的資本主義強國,為占取世界市場和鞏固霸權地位,各國競爭發展新技術,其中以電的新發明最為顯著。資本主義強國為攫取巨額財富引爆殘酷戰爭,促使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階段轉向壟斷統治階段,工業資本發展成為金融資本。電氣拓展自然科學新發展,技術開始同工業生產緊密結合起來,生產力得到飛躍發展,使得世界交通更為發達、聯系更為緊密,構建了一套較為完善的世界交通網,金融資本順著網格滲透到全球各地,并在擴張的進程中逐漸具有了制定國際規則的操縱力,但由于其沒有底線的利益追求必然導致其輸出方式走向戰爭。西方壟斷組織及其更高形態的各個強國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其本質就是帝國主義的霸權和強權。
第三次科技革命,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和平與發展逐漸成為當時人們的共識,信息技術爆發式發展形成了數字資本,也決定著其走向何方。數字技術將客觀存在物包括人和物體及其運動的信息統統變成二進制的符號寫入數字平臺,成為能被資本家掌握的“一般數據”,這些數據在云計算中被進一步開發利用,壓榨出剩余價值。數字產業興起,資本主義占有著各種數字生產資料,包括計算機系統、網絡平臺等,并組織數字勞動者進行商品生產與售賣,且主要是以數字化產品或服務為主,過程中數字資本誕生。新科技革命突出表現為數字技術的廣泛運用,資本更是突破一般性原則,成功跨越時空限制,導致全球化趨勢日益加劇,社會交互水平空前提高,數字資本融入世界市場體系,數字經濟進入迅猛發展階段。
總之,科學技術的進步為生產力發展實現質的飛躍,數字資本借助互聯網技術在全世界、各地區、各領域大放異彩,網絡的互動性和開放性為數字資本施展野蠻效應提供了可能,如何防止數字資本無序擴張、野蠻生長,將其服務于我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是志在必行的考量。
三、數字資本產生的基本要素
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淘寶和京東等網絡商城逐漸成為人們日常交易的主流渠道,一些網絡社交軟件也逐漸架構著現實的人際交往活動。人們似乎被因特網帶入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殊不知,這是網絡和資本的陰謀,數字技術已經成為最高級的生產力,數據成為資本家爭奪的資本,資本剝削更加廣泛且苛刻。那么,數字如何形成資本,探究其生成要素就成為解析數字資本的前提。
(一)數字平臺
什么是平臺?我們一般意義上理解為數字的基礎設施,它可以使兩個以上的群組發生互動,以自身為中介,讓不同的用戶匯集在一起,建造屬于他們自己的產品、服務和市場。隨著互聯網、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的迅猛發展,以平臺企業為代表的數字經濟在我國蓬勃發展,互聯網平臺作為“新的社會生產場域”呈現出區別于其他平臺形式的典型特征,同時也成為數字資本投資與剝削的新場域。
丹·席勒的《數字資本主義》回顧了互聯網的發展史,它是冷戰和反主流文化的產物,早期為美國國防部建設和控制,服務于軍隊需求,多用于軍事用途,因此它最初的使用者只有軍事承包商和少數大學,到了20 世紀80年代以后大眾才開始使用計算機網絡。互聯網的民用貌似給人類社會帶來了新的曙光,人民的美好生活有了盼想,但實際上,互聯網單純的性質和用途正在資本的侵蝕下悄然改變,互聯網的建設、創新和發展迫切需要強大的金融資助,其建設力量和服務對象也因此發生變化。金融寡頭下的金融資本成為其強有力的支撐,金融資本家利用金融權力實現對國民經濟生活的操控并對外進行資本輸出,牽制和滲透于計算機網絡的發展歷程,互聯網平臺成為間接的工具加大資本剝削的范圍和力度。事實上,互聯網無論是服務于國家、銀行還是集團等,它都不是為了給公民提供信息而打造發展的。反而科技和社會的發展讓資本家看到了數字化背后的紅利,數字化使得商品的形式在傳播領域中的得到大范圍擴張,數據在流通過程中不斷累積使數據本身創造出價值。資本在商業力量不斷深化和拓展數字化的發展中,推動構建數字平臺,使得數字網絡技術成為數字資本的新型生產力,建立新的生產關系、經濟活動、社會特征、勞動形式等。正如,“網絡正在擴大資本主義經濟中社會與文化的范圍”,成為數字資本的重要媒介,互聯網的全面使用,使得資本滲透至信息技術產業,利用網絡化手段無處不在的特征謀求高利潤的“魔盒”就此打開。
其實在“魔盒”才打開之時,人們對于數字化尚有可逃避的空間,而如今,數字帶來的改變不再僅僅局限于某一層面或者說是某一方面。隨著數字化的層層滲透,人的生存方式被徹底顛覆,現實社會逐漸被數字平臺架構,平臺借助其財力、用戶群、技術經驗等多方優勢,實現萬物數據化并將之存儲在私人占有的空間中,對其進行再加工售賣獲得資本積累,利用算法進行個性化商品定制與內容投放,并以平臺組織完成跨界媾和,進行全球化擴張,展現出強大的操控力,而那些看似積極參與且具有主動意識的“受眾”實質上始終承受著無償剝削。資本秩序披上數字外衣,新的市場秩序建立,數字交易遍布大街小巷。
數字平臺實則是數字技術和資本聯姻的產物,是商業化和產業化的聯結,作為“中間人”承載著一個從資本的投注到新資本接盤的過程,借助最初的資本投入,吸引用戶完成對市場的圈定和擴張后,資本剝削逐利的本性不斷推動數字平臺轉化為盈利工具,實現新一輪資本增殖。至此,數字平臺不再成為人類的曙光,人們不僅無法遠離資本主義,相反地,深深處在“數字化生存”的困局之中,數字平臺更是使得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剝削更為殘酷且尖銳。
(二)數字工人
生產的主體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著不同的稱呼,數字工人是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特有的名詞,是數字資本進行剝削的主要對象。探究工人的歷史軌跡,可主要概括為三個發展階段:一是手工業時代,工人是生產的基礎勞動力;二是機器工業時代,工人被機器部分取代;三是信息革命時代,徹底淪為數字工人,在資本運動的本質下物化、異化。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傳統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靠出賣勞動力生活,長期處在被剝削和被壓迫地位,但此時生產資料與生產者是不相分離的。但其后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社會完成從工廠手工業到機器大工業的轉變,機器消滅以手工業為基礎的作坊,在這種情況下,最突出的特點是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生產者與生產資料被迫分離,雖然社會化程度加深,生產效率大大提高,但是這也同時導致大量過剩勞工,導致工人的主體性地位一再削弱。
隨著社會矛盾和社會需求的轉變,社會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現代工人的主力軍變成了那些掌握科學技術尤其是計算機技術的知識分子,數字資本憑借數字技術覆蓋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建立龐大的數字帝國。原本在馬克思看來工人階級與資本才是對立的雙方,但在當代社會之中,矛盾已演化成大眾與數字資本的對立,大眾成為該時代的政治主題。與此同時,互聯網技術使得人成為數字工人,全部納為“全景觀監獄”之下,數字霸權橫行,數字傳媒和信息技術將整個景觀社會進一步精致化和生動化,使人們或被動或主動的沉浸在數字社會之中,不斷創造出剩余價值,人的主體活動成為商品并反過來成為控制人的一種因素,數字化危機悄然而至。
(三)數字勞動
21 世紀是云計算、人工智能、5G 網絡等科技競相迸發的時代,人的生活習慣、生產方式、行為方式都發生了極大的轉變,數字平臺成為人們進行一切活動的場域,數字化、信息化、網絡化是時代專屬標志。以數字信息技術創新帶來的革命浪潮使得人類勞動形式不斷向著一種以數字技術為支撐、以互聯網為依托的勞動新范式靠近,這種新范式不同于以往的勞動形態和結構,它打破時空界限,模糊工作與生活的分線,更多的用來榨取剩余價值,進而稱之為“數字勞動”。
對于數字勞動的解釋路徑可從傳播政治經濟學、社會情感學、文化研究等多個維度分析。首先,數字勞動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到蒂奇亞納·泰拉諾瓦的后結構主義文化理論,她于2000年發表的《免費勞動:為數字經濟生產文化》中用“免費勞動”來指稱“數字勞動”,此文章借用自治主義的“非物質勞動”概念將數字勞動看作是在數字經濟社會條件下發生在互聯網領域的“免費勞動”的具體表現。其次,泰拉諾瓦的學說提醒我們注意“網奴”的身份轉移,人們淪為數字工人在數字平臺進行行為已經成為一種普遍常見的剝削生產性活動,而且這種數字勞動是免費的。最后,馬克思主義傳播學政治經濟批判學派的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于2013年著作的《數字勞動和卡爾馬克思》一書,認為“只要是涉及到了互聯網社交媒介范圍內的各種類別的數字信息內容的生產與加工、數字內容的分析創造與流通都付出了勞工們不同程度上的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因此,也可以稱作是數字勞動。”倘若對數字勞動的表現形式進行區分,學術界可總結為三點:第一點,雇傭形式下的有酬數字勞動即互聯網專業勞動,它是由具有專業性技能的人員從事技術性相關的工作,如編程、網頁設計和應用軟件開發等;第二種,非雇傭性質下的無酬數字勞動,為數字公司生產利潤但得不到報酬的在線用戶勞動,是社交媒體平臺上數字資本積累的核心力量,是商業公司剝削的主要對象;第三種,受眾勞動和玩勞動。受眾勞動也稱用戶內容生產勞動,它主要偏向于消費者,用戶在數字平臺上的任何活動都能夠留下大量數據和信息,而這些都為資本以低廉或無償的成本獨占,通過對這些用戶原始數據的再加工或直接售賣能夠獲得超額利潤。因此玩勞動實質上就是通過在線模式能獲得的一系列娛樂活動,如看電子書、聽音樂、在線購物、網上聊天等,這些活動皆利于資本家分析用戶需求并投其所好,更大限度的壓榨剩余價值。
科學技術的發展將對工人的剝削,對勞動剩余價值的壓榨蔓延到日常生活之中,生產和生活的界限模糊不清,勞動者無法區分自己的行為是否提供了價值,單一的生活方式被數字技術重新定義,所有人被無形的“操縱”成為信息數據傳播者,數字生活看似給了人們自由發揮的余地,但實際上進行的每一個行為都是為數字資本家提供了剝削工具。
由此可知,數字平臺保留、收集著數字工人的數據信息,將這海量數據與云計算技術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巨大的關聯體系,每一個人都納入這“全景式”體系之下,數字工人產生的一般數據成為時代的支配性力量。掌握平臺的資本家實現了對數字資源的壟斷,這時可以說數字平臺成為人存在現實世界的中介,一旦放棄接受它的服務就脫離世界之外。數字資本家對于數字工人的剝削和壓榨完全被隱藏在數字勞動中,隱藏在滿足自身需要的使用價值背后,數字工人無酬的生產出所有價值。數字技術的兩面性體現在,一方面促進生產力發展,另一方面勞動主體性被消解,其建構的過程被打斷或抑制,資本邏輯框架下,資本家利益追逐的重要手段與主要工具就變成了數字勞動,從而構建了一種新型的數字資本剝削形態與模式,數字勞動客觀上成為了數字資本積累的來源。
[注釋]
①[美]丹尼爾·貝爾/ 高铦等.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索[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134.
②[美]尼葛洛龐帝/ 胡泳、范海燕. 數字化生存[M]. 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7:61.
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2.
④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2.
⑤花鳳春.科技革命與資本形態演變論析[J].中共樂山市委黨校學報(新論),2020,22(6):49-56.
⑥藍江.交往資本主義、數字資本主義、加速主義——數字時代對資本主義的新思考[J].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4):10-19.
⑦王治東,葉圣華.數字·技術·資本:數字資本主義的生成邏輯[J]. 沈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20(6):681-685.
⑧[美]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 楊立平.[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2.
⑨汪懷君,張傳穎.數字資本主義的數字勞動異化及其揚棄[J].寧夏黨校學報,2021,23(3):48-56.
⑩孟憲平.數字時代的資本主義新變化[J].社會科學研究,2020(6):63-72.
?孟飛,程榕.如何理解數字勞動、數字剝削、數字資本?——當代數字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J].教學與研究,2021(1):67-80.
?Christian Fuchs and Marisol Sandoval.Digital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A Framework for Critically Theorising and Analysing Digital Labour [J].Communication,capitalism&critique, 2014(2):14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