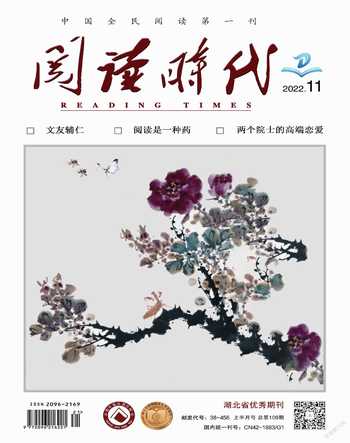從草木之文到草木文人
任芳
近年,中國社會有一股小小的“博物”熱潮,博物類圖書的出版也可算是層出不窮。而《文心雕草:中國植物人文小史》的出版,為博物書寫打開了另一種可能性。作者是學者,以嚴謹的學術態度,為了一草一木之歷史,上窮碧落下黃泉,東翻西翻找材料,爬梳文獻,考鏡源流,給中國草木一一寫傳。既考述草木在漫長歷史中的變遷,亦在歷史變遷中樹立起草木的文化形象。陳寅恪先生曾說,“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而《文心雕草》的追求可以說是:凡解釋一草一木,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草木,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
草木之文,在圖書市場常被歸為科普類作品,《文心雕草》在當當網也被列入“科普讀物”。這樣分類也沒什么不對,因為現代科學有三大領域: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文心雕草》的作者是人文學者,所作無關自然科學,應屬社會科學的人文科學。當然,人文科學也需要普及:《詩經·摽有梅》的梅是梅子樹,而非梅花樹;屈原《九歌》中,人向神獻上“桂酒椒漿”,而桂酒非是桂花酒,椒漿也非辣椒水。作者以人文關照草木,書寫也就草中見人,木上見文,將草木置于人之文化史中,遂有草木人文。
但是,草木之文,又何止于科普。美國自然文學的先驅和代表作家愛默生、梭羅、約翰·巴勒斯、約翰·繆爾,他們也寫植物,但其書寫可說是在科學精神指導下的自然筆記與思想筆記,其中有著生命的更高原則,其實很難“科普”。
近年,雖有大量草木之文問世,但不管是出版推介,還是讀者接受,著力點與關注中心基本就是“自然”:熱愛自然,探索自然,自然中的詩意生活,以及自然生態問題。如此言說與接受的是非姑且不論,至少我們不能這樣標簽《文心雕草》:它書寫的植物是自然之物,但更是文化之物。作者寫下的不僅是“大地上的事情”,更是中國文化史的事情。書中有言:草木“生長在大地上,也生長在人類的文化史里”。“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對于中國人來說,不僅是志趣和情懷,更是一種悠久的文化傳統。讀完這本書,引發的不是對自然家園的懷想,而是喚醒屬于中國人的文化記憶。
說是草木人文小史,但這背后的文化世界,是廣闊而浩大的。單看作者列出的參考書目,從詩騷名物、本草書,農書、園藝書、字書,到筆記雜著、民俗歲時、地方志……就能想象一個現代學人如何大海撈針般于浩如煙海的古籍文獻中尋找一草一木的歷史遺跡。沉在故紙堆的深淵里,只為搞清楚“楊柳依依”是怎樣一棵樹?古人眼里的枸杞之“枸”之“杞”究竟為何物?“采芳洲兮杜若”的杜若又是怎樣一棵香草?而這草那樹的背后又有怎樣的人生與故事?……要搞清楚,就得一本本一頁頁地翻閱,那些古老的典籍,因為歷史考古者的走進,熠熠閃光。在現代讀者面前,它們一次次出現,讓我們記得自己的出處和來路,記得流淌在我們身體里的文化血脈,讓我們看到了古人世界里的草和樹,也看到草和樹的背后是祖先的生活,看到他們面對世界的想象和思考,他們的情感與趣味。
他寫草木以及和草木糾纏在一起的文化,也被這些草木和文化改變著,這是知識分子上下求索的態度和精神,也是一個現代文學出身的學人對古典文化的致敬。駁雜的知識體系,學者的嚴謹考察,追求無一字無來處,都讓這本書超越了時下以很多披著文化外衣的草木之文。考辨的過程,也是思想碰撞的過程,其中透露出的思維的錯綜復雜與聯想的漫無邊際,是“小徑分叉的花園”,思想速度之快,意識之密集,讓人目不暇接。讀這樣的草木之文,看到草木人文史,也看到一個人文學者于歷史考辨中對于21世紀中國生活的反思。滿書的知識考古里,有傳統中國學者的學術趣味和文化立場、文化人堅守的“道”——草木之中,不僅“有趣”“有詩意”,也可以“有道”。
是草木史,也是心靈史
撰寫自己民族的植物史,對于一個人文學者來說,無疑是一場精神的壯游。盡管有時候只是一株絲毫不起眼的野草野樹,海金沙或者鼠麴草,構樹或者泡桐,但就像愛德華·威爾遜所說的,“只要我們愿意把視界從眼前垂直下移一臂之遙,一輩子人生都可以投注在圍繞一株樹干的麥哲倫之旅上。”《文心雕草》的草木史之旅不止于一片葉子到另一片葉子的距離,更是心靈地域的擴張和探索。

書的主線是為草木立傳,作者的草木之旅在古籍文獻的歷史之河里,但也并未因此而失去生命的體貼。做歷史考察時,作者是嚴謹的學者,但體貼生命時,作者是深情的詩人。從北方到江南,草木世界遂有了追憶北方的深情,以及煙雨江南新鮮體驗的喜悅。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里說:“土氣是因為不流動而形成的”,個人生活史的流變和精神地理的變動不居才能給生命帶來更多的可能性:白色槐花,曾是北方孩子的美食與歡樂,而初到江南,大雪天盛開的紅色茶花給他震撼……也因此,這些草木之文中,“我”總是在場。從深夜寫到凌晨,從上古寫到現代,從屈原的“芳洲”寫到魯迅的“百草園”,讀者也就跟著作者一同經歷這種柳暗花明的精神歷程,一同感受到心靈史與文化史中那些精微與宏大的場景。
雖然在傳統文化史里尋覓草木變遷的歷史遺跡,向古代先賢致敬,但中國現代文學的專業出身,也難免讓他時時想起民國那些人與事。在青藏高原遇見駱駝刺,會想起《本草綱目》里所記的邊疆舊俗,岑參的邊塞詩,但更想起《駱駝草》這本雜志,以及一群專心致志做書生的文化人,還有寫《中國的西北角》的范長江——一個有學問有好文章的現代報人,那也是傳統;寫木槿花,古代遼遠的事要說,但也忘不了魯迅《朝花夕拾》里的那些朝開暮落的花。作者常說,教育有專業,讀書無壁壘。學人囿于專業就只能做井底之蛙和饾饤之學,而讀書人的本分就是讀書。于是,作者遨游穿梭在古今典籍與雜著,追慕給蓍草寫傳的司馬遷,做史家,為草木寫史立傳,同時,也記錄下自身在閱讀與寫作中的心靈與思想的變遷。
童年讀過的故事,少年時期讀過的詩,集市上遇到的賣花人,北方鄉村的一道木槿花炒雞蛋……都內化成了生命的文化基因。他在露臺上種花養草,在路邊、荒地到處找尋植物。《文心雕草》的草木之文中,大地與古書融合在了一起。顧隨先生曾說:“一種學問,總要和人之生命、生活發生關系。”他將這些年的草木考釋,與自己的生活經驗聯結在一起;他的草木之文,也便扎根在了民族的文化傳統和自己的生命記憶之中。
泡桐,他從《書經》的“嶧陽孤桐”和《詩經》的“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開始寫起,他熱愛古籍古歌里的樹,但他同樣念念不忘自己和一棵樹的遭遇。深夜的街頭,遇見泡桐花,他寫道:“暗夜里,滿眼白色花,像是浮雕在夜的黑石之上。而花,如清澈的星空,鋪天蓋地……”隔著文字,讀者都能感受到花的力量。豐富而細膩的感受力,讓名物考證的草木之文也有了熱情和詩意。因此,文字也是舒緩、質樸,又詩意、熱情的,自有一種典雅的氣質。整本書找不到一句網絡和市井流行語,這種對文字的堅守,對漢語質地的自我要求,也是對心靈質地的捍衛。語言的背后是心靈的腹地,文字的圖景顯示著一個人的心靈圖景。那些在植物中獲得的豐盈感受與撫慰,獲得的文化震驚與體驗,是人與自然的深度交流,也是向古圣先賢的致敬。
致敬是熱愛,但不是迷信。不管是欽定的《廣群芳譜》,還是民間權威的李時珍,他都要繼續探索與考辨,在學術面前,欽定與權威皆非金科玉律。一個不復制的心靈是有自己的殊異性的,一種真知灼見的背后,都是心靈與頭腦糾纏和思辨的結果:采薇采的是什么?卷耳到底是什么菜?杜若究竟是什么草?……考辨這些生長在古籍里的舊物,是一個現代讀書人對一種古老傳統——名物考證的延續,但也更是一種情感——一種對文化和天地萬物的情意:每一種草木的背后,都有著古人的生活與心靈,他熱愛那些生活與心靈。
如果只停留于“格物致知”,或許會喪失一種更深的情感體驗。而與舊籍和草木相伴的生活中,它們也一同構成了作者“心的歲月”。植物在歷史中積淀為文化符號,符號里有古人的信仰,而作者也有自己的信仰。“我的謙卑感只面向永恒的存在、美的原則以及記憶中那些偉大的人類。”濟慈的話幾乎可以照搬過來,用以理解《文心雕草》作者的情感態度。
“余生無所好,唯嗜花與書”,清人陳淏子在《花鏡》序言里寫下的這句話,作者常常提及,這也是他熱愛的生活。于是,讀草,讀書。
為何要對一棵草念念不忘?為什么要追溯一株樹的歷史?答案也簡單:熱愛天地萬物和文化而已。好的寫作者首先是有情有義的人,草木叢中的欣賞與驚嘆,歷史遺跡中的歡欣與悲傷……多種情感的交織,像碎鉆石一樣鑲嵌在字里行間;在可觸摸的植物與消逝的歷史之間來回跳轉,知識考古、紀實與想象相互生發,于是有了《文心雕草》的草木之文與草木人文。
(源自“華文好書”,有刪節)責編: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