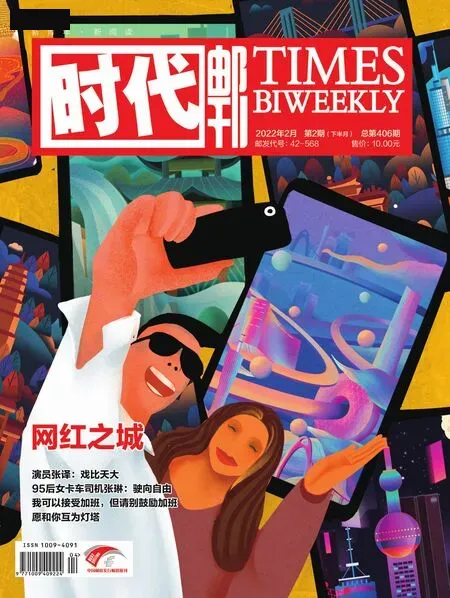當我們談論“社恐”的時候
文 鄒曉菁
“社交恐懼癥患者之所以在面對社交人群時焦慮,是因為擔心自己舉止失當,害怕因此而被人群嘲笑或是得到負面評價。他們也害怕自己內心的緊張不安被別人識破,進而得到負面評價。”

小組討論時不敢與不熟悉的同學交談,更不敢提出反對意見;當眾演講時,不管準備得多充分,上臺后還是緊張到大腦一片空白;路上遇到同事總想回避,不敢大方打招呼;聽到手機鈴響就恐懼,不敢接聽……
生活中,你是否見過這樣的“社恐”青年?又或者,你也是“社恐”人群中的一員?相關調查顯示,自2016年以來,“社交恐懼”一詞的網絡搜索率便持續攀升。在微博上,與“社恐”相關的話題已達數百個,不少話題的討論熱度過億。
當我們談論“社恐”的時候,究竟在談論什么?
“社恐”究竟為何物
如果被一只老虎咬了,你會選擇求救嗎?
“我不會。因為如果沒有人救我,我只是可能會死,可是一旦有人來救,我還得跟他打招呼。”這個曾在網上很火的段子出自一名脫口秀演員,寥寥數語,雖然夸張,但精準戳到了很多“社恐”人的痛點:面對人群就緊張焦慮。
很多年輕人抱著玩梗自嘲的心態談論“社恐”,卻不知道社交恐懼也是一種精神疾病。研究顯示,社交恐懼癥通常始于童年或青春期,大多數人在20多歲之前就已經發病,也有一小部分人會在成年后患上這種疾病。
而現在,社交恐懼從醫學概念演變為網絡上大家互相調侃的梗。在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孫萍看來,“社恐”一詞其實是被泛化了。“社恐”被泛化,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病理性社交恐懼癥的人數也在增多?南京市第一醫院心理門診主任牟曉東說,與其說社交恐懼人群有增多趨勢,不如說更多人了解到自己可能有社交恐懼傾向。“在過去物質生活尚不豐盈的年代,人們很難關注自己是否有心理障礙,而現在人們對心理學科、對自己的認識都在加深。”牟曉東分析道。
“現在的年輕一代獨生子女占多數,從年幼時起他們的社交頻率就比上一代低很多;而且這一代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正逢互聯網和智能手機興起,社交軟件普及,年輕人越來越呈現‘線上狂歡、線下沉默’的狀態。”牟曉東說,現在的年輕人更習慣躲在手機屏后,不習慣把自己暴露在人前,這都可能造成社交恐懼癥多發于年輕人中。“廣義上的社交恐懼癥確實可以說是現代人的通病,有些人的‘社恐’達不到精神疾病的程度,但也會在日常生活中有所體現。”他說,現代社會雖不至于“人人皆社恐”,但“社恐”現象確實值得更多關注。
“我們不能將‘社恐’簡單歸因于內向或害羞,內向的人只是喜歡自己安靜地工作,并不會害怕人,這要加以區分。”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心理科主任醫師李一花提醒道。
“社恐”人心里在想什么
為什么面對人群時就會有焦慮感?劉利(化名)就是一名“社恐”人,他曾做過某心理機構發布的社交焦慮障礙自評表,測試結果是患有中度社交焦慮障礙,“當我面對人群的時候總有焦慮,比如和同學聊天時,如果他沒有對我剛才說的話做出回應,我就會認為,他是不是覺得我說的話很無聊?久而久之,我就很害怕和人打交道。”
從認知心理學角度來看,劉利的心理活動可以被稱為認知偏差。社交恐懼癥往往與認知偏差有關,比如在面對社交人群時會夸大負面結果出現的可能性,或者對模棱兩可的情況作出消極的解釋。
“社交恐懼癥患者之所以在面對社交人群時焦慮,是因為擔心自己舉止失當,害怕因此而被人群嘲笑或是得到負面評價。他們也害怕自己內心的緊張不安被別人識破,進而得到負面評價。”牟曉東總結了社交恐懼癥的表現。
為了提高社交能力,劉利也曾看過社交溝通技巧的相關書籍,但他感覺這對改善他的社交恐懼癥狀幫助不太大。劉利說,很多“社恐”人都像他一樣,內心其實很期待一段愉快的交流,所以會在社交時“討好”對方。但“討好式”社交的感受并不好,于是很多“社恐”便慢慢放棄了社交,越來越不愿意主動和外界接觸。
“哪有人喜歡孤獨,不過是害怕失望罷了。”巴黎第八大學精神分析博士王明睿借用村上春樹這句話總結了“社恐”人的復雜心態。“社交恐懼癥人群的一個重要表現是在社交中無法獲得認同感。”王明睿認為,這和教育方式有關系。“我們傳統的教育方式更傾向于讓孩子在交流中獲得認可,而不是鼓勵孩子在社交中單純地表達自我。”在他看來,這就使得孩子們在長大后對獲得認可的需求非常高,一旦無法在社交活動中獲得期待中的認可,就容易產生回避心態。
“社恐”需要治嗎
“80%的‘社恐’人不必進行相關治療。”這是牟曉東根據接診經驗得出的數據,“這部分患者雖然也有社交恐懼的相關癥狀,但可以通過減少社交活動頻率等方式保持正常生活。”
那么社交恐懼癥狀達到何種程度就應該求助專業人士呢?牟曉東給出一個判斷標準:社交恐懼癥狀持續6個月以上,并且嚴重影響日常的工作、學習和社交活動。
談及嚴重的社交恐懼癥為何需要積極就醫,王明睿解釋道:“每個社交恐懼癥患者的病因都是極具個性化和偶然性的,對病因的深層探尋是一個高度專業的工作,必須由專業人士完成。”
王明睿分享了一個病例:“我曾接觸過一位社交恐懼癥患者,她當時已經嚴重到不敢出門見人,每天只在夜里無人時去公寓的自動販賣機買點必備食品。”最初,這位患者并沒有將童年家暴陰影、工作受挫和自己突然患上的社交恐懼癥聯系在一起,最終,在專業人士的幫助下才找到致病原因,并找到了打開心結的辦法。
“嚴重的社交恐懼癥往往還伴隨著抑郁癥。”牟曉東提醒,社交恐懼癥狀加重時,抑郁程度很可能也加深了,此時患者應該再測一份抑郁程度量表,有問題及時就醫,“嚴重的社交恐懼癥病因往往很復雜,需要由專業人士診斷。”
“有的社交恐懼癥患者不需要長期服藥,但當有重要社交活動比如上臺演講時,可以通過提前服藥穩定情緒,這樣上臺后就不會太緊張焦慮。但要注意,患者不管是長期還是臨時用藥,都必須在醫生的指導下進行。”牟曉東說。
輕度“社恐”可以自愈嗎
如今,在社交網絡平臺給自己貼上“社恐”標簽的年輕人,他們大多癥狀較輕,沒有達到必須就醫的程度,但像劉利一樣,很多“社恐”人雖然外表上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樣,但內心對愉快自如的社交活動仍有很大需求。
“程度較輕的社交恐懼癥患者可以嘗試脫敏治療,就是主動去靠近讓自己感到恐懼的社交情境。”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心理科主任醫師李一花建議,“從行為科學的角度出發,對社交情境的回避意味著患者永遠無法脫離恐懼。如果想消除對社交情境的恐懼,就應該先靠近恐懼。”
在李一花看來,現代社會需要展示自我的場景很多,如果“社恐”人總是用回避的方式躲在安全的“殼”里,很容易錯失自我發展的機會。“一旦社交恐懼癥患者的社交模式改善了,那么他的工作和生活的質量都會有所提升。”李一花鼓勵程度較輕的“社恐”人嘗試自愈。
王明睿鼓勵“社恐”人多參與可以表達自我的社交活動。“相比玩桌游和劇本殺,小龍蝦才是更有效的社交工具。只有嗍著小龍蝦時,大家才會放下手機面對面坐在一起表達自我,這才是有效社交。”他笑著建議,多和朋友嗍幾頓小龍蝦,“社恐”可能就自愈了。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擁有適當而舒適的社交活動是每個人都有的需求,當我們找到更好的與外界溝通交流的方式時,世界也會向我們展示更美好的一面。”王明睿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