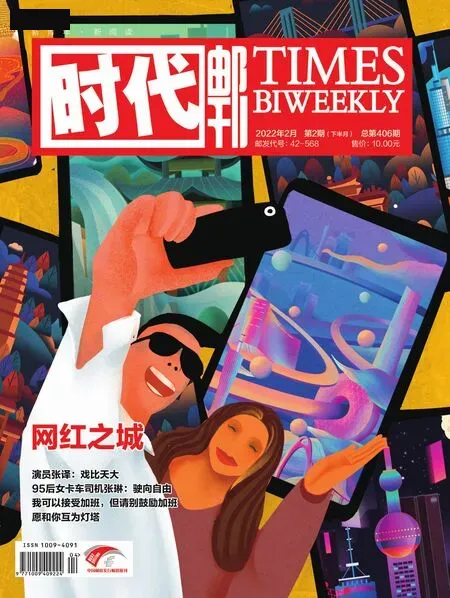汪曾祺認識了施松卿
文 汪明

(節選自汪朗、汪明、汪朝著《老頭兒汪曾祺》,中國青年出版社,2016年8月)
爸爸在昆明一共住了七年,這在他一生中是一個重要時期。在昆明他接受了高等教育,結識了許多師長和朋友,開始走上文學創作之路。在他個人生活歷程中,昆明也是至關重要的。他在中國建設中學時,不但品嘗了不少野菜,寫出了不少文章,還認識了一個與他以后的生活密切相關的人物—— 媽媽。
我們的媽媽施松卿,女,福建長樂人,1918年3月15日生,比爸爸大兩歲。
1939年,媽媽來到昆明考入西南聯大,和爸爸是同一年。在西南聯大,媽媽先是讀物理系,和楊振寧做過同學。但是不久便覺得功課繁重,十分吃力,加之后來又得了肺結核,學業更是時斷時續,難以跟上課程。于是,一年之后她便轉到了生物系,想繼承外公的事業,向醫學方向發展。
生物系的功課也不輕松,而此時媽媽的肺病更為嚴重,只好休學一年,到香港養病,因為昆明的物質條件太差。沒想到,病還沒有全養好,日軍發動了太平洋戰爭,攻陷香港,媽媽只好帶病返回昆明。這一次,她又轉到了西語系,因為學文科相對不那么吃力。
媽媽由于休學一年,學習又是時斷時續,因此畢業時間相應延長到了1945年夏天。畢業之后由于當時新加坡被日本人占領,家中經濟來源中斷,因此媽媽當時的生活也比較窘迫。為了謀生,媽媽也到了中國建設中學,和爸爸成了同事。
媽媽經過的事情比起爸爸要豐富許多。這使爸爸很羨慕。他曾經多次說過:“我要是有你們媽媽的經歷,不知能寫多少小說。”
談到大學的往事時,媽媽常常很得意地說,在西南聯大,人們叫她“林黛玉”,因為她長得挺清秀,淡淡的眉毛,細細的眼睛,又有病,一副慵慵懶懶的樣子。還有叫她“病美人”的。當然,她的本意不是說自己有病,而是有病時尚且如此之美,沒有病就更不用說了。一次,我們問爸爸是否如此。他笑嘻嘻地說:“是聽過有這么個人,有這么個外號,但當時不熟。等到我認識你媽媽時,她的好時候已經過去了。”說得媽媽干瞪眼。
不過,媽媽在外面給人的印象確實不錯。就是晚年和爸爸一起到外地時,也還是頭是頭,臉是臉的,很有風度。有人說像一個人—— 伊麗莎白女王。
也有人不這么看。“文革”后期,一次,郵遞員到家里送包裹單,需要簽字。媽媽開的門,郵遞員上下打量媽媽半天,猶猶豫豫冒出一句話:“老太太,您認字嗎?”那天媽媽上穿一件舊毛衣,下面是一條沒有罩褲的棉褲,顏色還是綠的,活脫一個家庭婦女。她在家里經常是這樣的裝束。
算起來,爸爸和媽媽相識的時候,一個25歲,一個27歲,已經不算談情說愛的最佳時期。他們以前心中是否有過什么人?不詳。他們自己不說,做子女的總不能在這個問題上刨根問底吧?不過,從他們的日常言談中,多少也能察覺出一點蛛絲馬跡。

汪曾祺
(19 2 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祖籍安徽,生于江蘇高郵,中國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
爸爸在文章中說過,他17歲初戀,當時正在江陰上高中。暑假里,在家中寫情書,他的父親還在一旁瞎出主意。此人姓甚名誰,不清楚。好像是他的同學,但是17歲畢竟年齡還是太小了,此事未成也在情理之中。不過,到了晚年,爸爸有時還流露出對那段時光的珍惜。初戀總是難忘的。
到了大學,盡管爸爸生活困頓,沒有余資向女生們獻殷勤,但是他的才華仍然博得了不止一個女同學的好感。
據爸爸最好的朋友朱德熙先生的夫人何孔敬說,爸爸當時的女友后來在清華教書。一次朱德熙在清華門口還悄悄地向她指明此人,長得白白凈凈的。后來爸爸失戀,曾經好幾天臥床不起。朱德熙夫婦不知該如何勸解,只好隔著窗子悄悄觀望,以防不測。還有一個姓王的女生和他的關系也相當密切。這一點,從媽媽談到此人時的醋意可以感覺出來。但是爸爸在聯大學了幾年,連畢業文憑也沒有拿到,前途渺茫,作為女孩子,總要考慮周全一些,聯大出色一點的女生又不乏追求者。因此,在大學時這件事最終還是沒有結果。
至于媽媽,雖然很少和我們談及她的“心路歷程”,但不經意中也透露出在聯大時與一些男同學有所交往,其中和一個福建同鄉關系不錯。此人是歷史系的,畢業之后便出國留學了,走后還從美國給她寄來青霉素(當時叫盤尼西林)治她的肺病。當時這種藥十分稀貴,于是媽媽轉手便到黑市賣掉了,發了一筆小財,借以維持生活。但是,兩個人畢竟遠隔重洋,再想進一步發展什么關系難度太大,最后自然而然斷了線。
人世間的許多事情往往都是這樣。
爸爸和媽媽在建設中學相識之后,很快有了好感,有點相見恨晚的味道。一次爸爸媽媽聊起聯大的事情,媽媽對我們說:“中文系的人土死了,穿著長衫,一點樣子也沒有。外文系的女生誰看得上!”“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媽媽很得意地說:“有才!一眼就能看出來。”爸爸當時大概流露出一種才華橫溢的樣子,盡管背老也挺不直。一次他陪著好朋友朱德熙到鄉下定親,穿著件爛長衫,拄了根破手杖。女方就是朱德熙后來的夫人何孔敬。朱德熙與未來的岳父寒暄,爸爸就一個人隨意閑逛。兩人離去后,何孔敬的父親對她說:“今天一起來的汪先生不一般,有才!一眼就能看出來。”他算不上什么文化人,一個開瓷器店的老板。
爸爸和媽媽認識之后,行動便有了伴。兩個人一道看電影,一道看病—— 爸爸當時老牙疼,媽媽陪他進城找大夫,還一道養馬。朱德熙向我們描述第一次見到媽媽時的情景:“我去看你們爸爸時,在建設中學大門口,看見一個女的牽著一匹大洋馬,走來走去,嘖嘖嘖……”在建設中學,爸爸媽媽已經有了那么一點意思,但是還沒有正式談論婚嫁之事。大家都窮成那個樣子,想要成家也不現實。
爸爸媽媽在建設中學一直呆到1946年7月,然后結伴離開了昆明,走上了回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