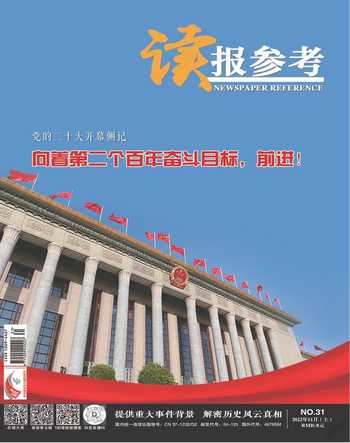即將到來的上海地攤
9月22日,上海發布20年來首次進行全面修改的新版《上海市市容環境衛生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新版《條例》”)。新版《條例》規定,不得擅自占用道路、橋梁等公共場所設攤經營、兜售物品的同時,明確區人民政府、鄉鎮人民政府可以劃定一定的公共區域用于從事設攤經營、銷售自產農副產品等經營活動。新版《條例》將自今年12月1日起正式施行。在以往,上海對設攤經營、占道經營是全面禁止的。
任媛媛是一位“90后”,常住上海,去年10月份開始在小區門口的馬路邊支了一個炸貨鋪攤子,這個位置隸屬郊區,小區周邊的商業配套很少。今年7月,任媛媛與朋友合伙在更靠近市區的地方成功開出了一家門店,雖然只有6平方米,但在這里至少不會再擔憂因雨水的突然造訪而狼狽收攤子了。然而,門店開出后,“和想象得還是不太一樣”,任媛媛一核算,門店掙下來的錢還不及當時擺攤時候掙得多。9月底,她又開著那輛擺攤車來到了小區門口。擺攤第3天,剛準備營業,城管來了。所以,談及接下來上海將會劃定出一部分允許擺攤的區域,她很期待。
老式地攤的沒落
與任媛媛的期待不同,李阿姨很是擔憂。李阿姨看著50多歲的樣子,她平日在上海外環的一家工廠附近的十字路口擺攤賣鞋,這里人流稀少,往來以集裝箱卡車為主,卡車揚起的塵煙彌漫,不時有騎著電動車的快遞小哥停下看幾眼鞋子。在她周圍,還有四五個賣鞋、賣衣服的攤位。
? 她擺攤已經10多年了,以她現在擺攤的這個區域為點位,近些年她呈三角狀打游擊,基本上是從熱鬧的地方搬離到更加偏僻的地方。相應地,從擺攤上獲得的收入也一再銳減,從一晚上能成交30多雙鞋到一晚上能賣出兩三雙都很艱難。近期,她也看到了“擺攤會被放開”的新聞,但她擔憂劃定的區域會在人流更加稀少的偏僻區域,那樣生意就更難做了。
? 這個問題,記者也同時提給了任媛媛,相反,她并不擔心。在她看來,如果是地攤集聚的區域,即使偏僻,也會自帶流量。兩種態度的對比折射出社會變化。
李阿姨指了指對面高聳的小區樓房說,十幾年前這個小區還不存在,她和很多湖南同鄉在這附近擺攤賣鞋,好的時候一天賣出去30多雙,一年能掙到幾十萬。她又指了指對面那條馬路說,以前對面都排滿了地攤。
? 李阿姨售賣的鞋子并非新鞋,而是從回收集散點拉回家以后,由她自己手工清洗干凈,再拿出來售賣的品牌二手運動鞋,價位在幾十元到百元不等。與她攀談的半小時間,隔壁售賣仿版新鞋的大哥攤位上不時有顧客前去詢問,李阿姨的攤子卻鮮有人問津。當隔壁有顧客的時候,她會說:“同樣的價位,他那個新鞋的質量很差的。”這句話,她來來回回說了多次。
? 今夕已經不同往昔。李阿姨說,以前她的很多同鄉都跟她一樣在這附近賣二手鞋,但后來很多人都離開了。記者問她為什么,她又指了指那群高聳入云的樓房說:“這對面的小區一個月房租五六千,誰能租得起?”
年輕人喜歡的市集
? 產業在變化,地攤業態其實也在變化。就像二手鞋已經不再受歡迎一樣,李阿姨所熟悉的地攤形式也已經不是當下的年輕人所喜歡的業態。
? 任媛媛會時常在小紅書上分享自己的擺攤創業經歷,她的擺攤車吸引了很多年輕人的問詢。她的車裝扮得很是漂亮,純白色的主色調,車身圍了一圈燈串,車內貼了一張卡通漫畫的拼接布,她把招牌也作成了卡通樣式,這一輛車子在夜晚很是吸引人。
? 當下,地攤,或者說新型地攤——市集正在成為年輕人心目中帶著浪漫色彩的“詩和遠方”。不難發現,在社交平臺上,越來越多人的年輕人或正在擺攤,或期待擺攤,他們想賣氣球、賣咖啡、賣手作,或者單純只是想逃離“996”。
? 市集也成為了商業地產引流的重要抓手,《2020商業地產志年度報告》中提到,2020年全國多個商場空間,舉辦了超過 1000 場與市集相關的主題活動。但這樣的活力未能照顧到像李阿姨這樣的群體。記者詢問李阿姨會不會考慮到市集上去擺攤,李阿姨看著眼前的鞋子說道:“那樣的地方我們哪里租得起。”
? 目前,上海市集的攤位費從百元到千元不等。任媛媛也未把市集當作自己的全部指望,她解釋說,如果是固定收取200-300元的攤位費,她還能接受;但是有些市集要求采用分成,分成比例高到35%-40%。“原本盈利的空間也只有四成,這樣一抽成,一天等于白忙活。”任媛媛說道。
? “商場的租金越來越高。”上海某文創市集主理人曾這樣向記者解釋攤位費攀升的原因,“商場不僅要收取場地費,還要求你搭建得美觀、布景精致、賣的東西好看,消防安全、設施安全等。”主辦方需要盈利,因此增加的成本繼續轉移至攤主身上。該主理人告訴記者,在上海收費超過1000元/天的市集都有,原先的很多老攤主今年都不租了。
面子和里子
? 任媛媛基本上每天在社交媒體上都能收到來自粉絲的關于擺攤事宜的問詢,比如,車子從哪里定制,哪里比較方便擺攤等。跟記者聊完的那個夜晚,任媛媛發了一條朋友圈說,“我想灌一碗毒雞湯”。她寫道:“工廠、公司裁員,消費低迷,這樣的大環境下,很多人選擇小本創業,當然,我也是其中之一。很多粉絲都在咨詢,想創業,想擺攤兒,想開店,在決定之前可以問自己幾個問題。”
? 是否能扛得住強度巨大的體力勞動?每天反復做同樣的事情,是你想要的生活嗎?擺攤是否能經得起別人的冷言冷語?如果被驅趕或被罰款是否能接受?是任媛媛拋出的一系列問題。
? 當下年輕人喜歡的擺設精美的市集是新衍生出來的地攤業態,但擺攤的底層仍然需要回到任媛媛提出的問題。曾有在上海市集擺攤賣花的“90后”小伙子向記者談到,社交媒體上熱議的擺攤一天收入過萬的情況,他也有過,母親節那天,他的營業額達到8000元,“但那都是極少的情況。很多白領調侃說想要出來擺攤,哪有那么容易,這是服務業,搬花、運花也需要體力,不是誰都能做得來的”。
? 市集的地攤樣本有了面子,但卻照顧不到“里子”的李阿姨這樣低收入人群,而勉強稱得上是“面子”一部分的市集攤主們,面對高昂的攤位費,也有頗多無奈。
? 那么,地攤經濟究竟為誰而提?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研究員、《我國大城市夜間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課題負責人王巖表示,我國提倡開展“地攤經濟”能夠有效緩解就業壓力,讓失業人口獲得收入。同時,它也是社會的一個緩沖地帶,它的低成本性可以給中低收入人群降低生活成本。但也同時需要警惕地攤資源會不會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商業資本介入以后,變成他們新的商業盈利模式。這方面,政府要作好行業規范,加強引導與監管,讓地攤成為老百姓生活必需的“地攤”。
(摘自《經濟觀察報》葉心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