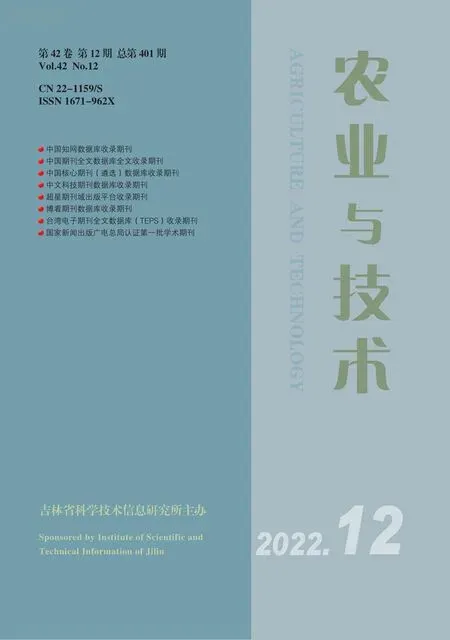種質(zhì)資源對糧食安全的影響簡述
李修平于鑫鑫李維剛
(1.佳木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黑龍江 佳木斯 154007;2.佳木斯大學經(jīng)濟與管理學院,黑龍江 佳木斯 154007)
糧食是保障人民日常安全生存的必要條件,而我國既是當今世界上的最大人口大國,也是糧食需要量最高的大國,所以保證糧食的質(zhì)量與安全的工作必不可少。種質(zhì)是生產(chǎn)糧食的基石,是保證農(nóng)作物可持續(xù)生長的“芯片”。中央一號文件中所提到的“打好種業(yè)翻身仗,制種行業(yè)迎發(fā)展機遇”、“保障糧食安全,穩(wěn)定重要農(nóng)產(chǎn)品供給”、“土地改革穩(wěn)步推進,關(guān)注農(nóng)墾板塊投資機會”等內(nèi)容,保證種質(zhì)資源對保障糧食安全發(fā)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1 種質(zhì)資源的現(xiàn)狀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種質(zhì)資源的保護已經(jīng)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部門規(guī)章和地方法規(guī)的出現(xiàn)也對現(xiàn)代種質(zhì)資源的發(fā)展起到著重要的作用。2015年開展的“第三次全國農(nóng)作物種質(zhì)資源普查與收集行動”提出,在全國范圍內(nèi)建立種質(zhì)資源保護利用研究機構(gòu),并在《種子法》中明確指出,國務院和省、自治區(qū)、直轄市人民政府設(shè)立專項資金,用于扶持良種選育[1]。20世紀90年代,國家分別在北京和青海2個地區(qū)建立國家糧食作物種質(zhì)資源庫和國家作物種質(zhì)復份資源庫,這一舉措對于中國糧食作物改良和生物遺傳研究都有著很大的幫助。2018年,中國已經(jīng)建成世界上唯一完備的種質(zhì)資源保護配套機構(gòu),有效豐富了種質(zhì)資源的戰(zhàn)略儲備體系。從2022年3月1日起,重新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開始啟動實施,并對“重點收集珍稀、瀕危、特有資源、特色地方品種,加強種質(zhì)資源保護,再一次堅定蒙草生態(tài)做好特色種業(yè)的信心”[2]進行了明確。
生物育種科技的發(fā)達也對我國傳統(tǒng)農(nóng)作物育種體系形成了制約的影響,由資本所倡導的商品化種植推動了中國種業(yè)體系走向單一化、壟斷化,并因此造成了種質(zhì)基礎(chǔ)的狹小;在政策方面,由于未能得到足夠的保障,導致農(nóng)民基本放棄了民間育種的實踐;在第四次“生物技術(shù)+信息化”為特點的種業(yè)科技革命中,生物技術(shù)、智能化、數(shù)字化及信息化科學技術(shù)為一體,種業(yè)跨國公司實施了對良種的培育,并且應用生物學修飾技術(shù)也進行了方向的改進,使種質(zhì)資源在育種方面獲得重大的突破[3]。我國在種質(zhì)資源科技上的改進使我國在種質(zhì)育種的道路上前進了一步,同時也為種質(zhì)資源育種技術(shù)在我國今后的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
當今種植業(yè)市場全球化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隨著國外種業(yè)巨頭的強強聯(lián)合,抱團式的成長,已逐步成為了以種質(zhì)公司攜手國際農(nóng)業(yè)化巨頭強強聯(lián)合為特征的一種新型金融導向,也逐步從傳統(tǒng)種業(yè)的合并轉(zhuǎn)變?yōu)閲H種業(yè)的融合;世界種業(yè)走向“一體化”,大型跨國企業(yè)由傳統(tǒng)跨國企業(yè)快速轉(zhuǎn)型成為新型商業(yè)機構(gòu),我國作為一個重視合作互助型的大國,在與各國種質(zhì)資源的合作方面,我國也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和表率。我國不斷從世界各地引入種質(zhì)資源從而帶動世界種植農(nóng)業(yè)的蓬勃發(fā)展,中國基本實現(xiàn)糧食自給自足,同時我國也堅持“走出去”的思想,我國通過地區(qū)和國際合作向其他國家和機構(gòu)提供了大量的植物遺傳資源[4]。
在中國種質(zhì)資源市場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國外種業(yè)巨頭企圖掌控我國的種業(yè)市場,使得中國民族種質(zhì)資源主權(quán)遭到了威脅。如,我國許多糧食作物重要的主產(chǎn)地區(qū)被美國公司玉米品種所覆蓋;在山東省壽光栽培的蔬菜大部分選用的都是從國外引進的種質(zhì),所以出現(xiàn)了本地品種的茄子、辣椒、番茄等被排擠出國內(nèi)市場;在科技方面,由于轉(zhuǎn)基因、基因修飾等先進的技術(shù)核心掌握在發(fā)達國家的手中,這也正是對我國種業(yè)安全構(gòu)成威脅的主要因素[5]。因此在不斷向前發(fā)展,向前進步的同時,更應注重我國自身的本土種質(zhì)產(chǎn)業(yè),加強對我國自身種質(zhì)資源的保護,在不斷引進改進的同時,也做好保護自身種子資源的一道防線。
2 種質(zhì)資源的利用與創(chuàng)新
新形勢下我國種業(yè)科技創(chuàng)新面臨“三個落后”的問題,解決吃飯的問題,根本出路在于科技,因此種質(zhì)資源的利用與創(chuàng)新是必要的問題。全球化、市場化、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化和全球經(jīng)濟一體化的發(fā)展趨勢,使種業(yè)科技到達世界農(nóng)業(yè)競爭與控制的新高度[6]。我國的制度優(yōu)勢對種質(zhì)資源結(jié)構(gòu)進行了合理的調(diào)整,使國家在重大農(nóng)業(yè)技術(shù)創(chuàng)新方面有了成就,對農(nóng)業(yè)基礎(chǔ)性和前沿性也有了深入的研究,并通過對農(nóng)業(yè)種質(zhì)資源的有效整合進行了加強、保護、研究和利用,加快了生物育種產(chǎn)業(yè)化的進步速度,對新品種的審批工作進行了完善,并通過對專利進行維護,以良好地應用技術(shù)創(chuàng)新鏈的構(gòu)建為主要抓手推動了中國種業(yè)經(jīng)濟發(fā)展的高質(zhì)量發(fā)展[7]。
2.1 分子標記輔助選擇技術(shù)
分子標記與輔助選擇理論是把分子生物學研究的方法與技術(shù)相結(jié)合,對目標性狀的基因進行定向操作和聚合,對種質(zhì)資源的育種速度有著大幅度的提高[8]。現(xiàn)階段,分子標記輔助選擇技術(shù)目前在我國給予了廣泛的應用,也因此產(chǎn)生了數(shù)量豐富的具有耐病、抗蟲、耐逆境、高產(chǎn)等基因特征的糧食作物以及新的種質(zhì)資源,同時推動了全世界主要糧食作物選育的高速發(fā)展[9]。
2.2 轉(zhuǎn)基因技術(shù)
運用轉(zhuǎn)基因技術(shù)來開展農(nóng)業(yè)育種已經(jīng)成為全球競爭的核心,從轉(zhuǎn)基因商業(yè)化開始,全球轉(zhuǎn)基因作物品種開始日益豐富[10]。就目前形勢來看,轉(zhuǎn)基因抗蟲棉在我國迅速發(fā)展;雜交抗蟲棉研發(fā)與實驗方面也已經(jīng)取得了重要的技術(shù)突破,并進行了全面的科學評價,抗蟲基因水稻已在全球同類別的研究中居于領(lǐng)先地位,培育出的轉(zhuǎn)基因農(nóng)作物新材料和新品種具有產(chǎn)業(yè)化的前景[11]。
2.3 分子設(shè)計育種
分子設(shè)計育種就是在以對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戰(zhàn)略意義全基因組序列分類為基礎(chǔ),通過對植物分子標記物進行大規(guī)模的深入研究,進而確定重要農(nóng)藝特性基因的功能、效應、網(wǎng)絡(luò)調(diào)控及其基因表達產(chǎn)物作用規(guī)律的前提條件下,首次通過大量的實驗對有利的基因?qū)胛膸旌蛯?yōu)質(zhì)轉(zhuǎn)基因品種進行構(gòu)建;再去根據(jù)選育的目標;通過使用計算機軟件對大數(shù)據(jù)進行分析和模擬,得出最優(yōu)的選育方案,從而讓育種技術(shù)由傳統(tǒng)到定向的高效“精準育種”的技術(shù)轉(zhuǎn)化,在培育的方面也獲得了突破性的進展[12]。隨著人們對分子研究的發(fā)展,通過基因組性狀的定位分離、構(gòu)建染色體組型片段置換體系、對等位基因功能效率的有效分析,利用軟件進行模擬品種的組配,挑出最優(yōu)秀的選擇,讓育種變得更為精準[13]。
3 糧食安全
202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對保障國家糧食安全這條底線給予具體的指示,更有力的表明了保障糧食和重要農(nóng)產(chǎn)品供給的重要性,并且給出了關(guān)鍵性的舉措,在正確認識和把握供給保障問題上給出了明確的方向[14]。
3.1 加強種質(zhì)資源保護,保障糧食安全
種質(zhì)是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基礎(chǔ),同時也是農(nóng)業(yè)的“芯片”。國家要發(fā)展,要壯大離不開人民,而人民的生存離不開糧食,正所謂要首先解決人們吃飽不餓肚子的問題,因此保障糧食的充足供給是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關(guān)鍵,因此保障糧食安全也成為了現(xiàn)代發(fā)展的重要保證,而保障糧食安全的基礎(chǔ)就是保障種質(zhì),保障好種質(zhì)資源的安全才能保證種植多樣性的安全,進而保障糧食的安全。種業(yè)的發(fā)展水平不僅能夠決定糧食供給總量是否達到充足,同時也對農(nóng)業(yè)效益、競爭力和可持續(xù)性發(fā)展有著很深的影響[15]。加強各國之間的交流,用多種方法引進種質(zhì)資源,所謂的保護種質(zhì)資源就是對種質(zhì)多樣性加以保護[16]。
3.2 保障綠色農(nóng)業(yè)開發(fā),保障糧食安全
綠色食品的生產(chǎn)是農(nóng)產(chǎn)品經(jīng)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必要條件,綠色食品發(fā)展的推進不僅是一場關(guān)于農(nóng)產(chǎn)品內(nèi)部結(jié)構(gòu)與生產(chǎn)方式調(diào)整的經(jīng)濟性變革,也是行為和消費方式上的一種綠色革命。共同構(gòu)建出以資源節(jié)約型、環(huán)境保護型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推動農(nóng)業(yè)發(fā)展與資源環(huán)境相互配合、與生產(chǎn)生活生態(tài)相互協(xié)調(diào),在開展建設(shè)綠色農(nóng)業(yè)的道路上我國可以對傳統(tǒng)的措施加以借鑒[17]。如,我國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人們通過發(fā)展“水稻、鴨和魚”、“水稻和泥鰍”、“水稻和田螺”等具有循環(huán)型的農(nóng)業(yè)模式,在減少環(huán)境污染,保障糧食安全方面提供了新思路。也可對國外的“環(huán)保全型農(nóng)業(yè)”、“環(huán)境友好型農(nóng)業(yè)”等進行借鑒和學習[18]。
3.3 堅守糧食安全底線,保障糧食安全
從十八大以來,國家一直把確保中國糧食安全視為治國理政的一號大事,對中國糧食安全這一課題一直給予高度的關(guān)注,實現(xiàn)了從“誰來養(yǎng)活中國”到“中國人的飯碗裝中國糧食”的飛躍[19]。保障糧食安全,是形成國家經(jīng)濟發(fā)展布局的基本安全底線[20]。
就國內(nèi)來講,國內(nèi)人口數(shù)量的持續(xù)上升,造成人們對糧食總量需求的不斷增長[21];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增加,對食物條件的要求也隨之提升,因此更加注重糧食的安全;我國人均資源的占有量少,因此更應對耕地的質(zhì)量加以提升[22];農(nóng)資價格的提高,使農(nóng)民的利潤收窄,對農(nóng)民種糧的積極性產(chǎn)生了影響;近年我國天災的不斷頻發(fā),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穩(wěn)定性產(chǎn)生了制約[23];糧食生產(chǎn)向主產(chǎn)區(qū)集中發(fā)展,使糧食跨區(qū)域的流通量進一步增加,并且增大了運輸?shù)某杀荆兄蠓炔▌拥娘L險[22]。
從國際來看,新冠肺炎疫情的擴散產(chǎn)生了生產(chǎn)力短缺,生產(chǎn)資料不足,運輸受限等多種不穩(wěn)定不確定性的問題[24];國際經(jīng)濟貿(mào)易復雜化,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利益沖突加劇[25];產(chǎn)業(yè)鏈和供應鏈受損導致一些國家或者地區(qū)出現(xiàn)了糧食供給混亂和短缺;極端天氣的出現(xiàn)對糧食作物的產(chǎn)量質(zhì)量以及收成的穩(wěn)定性產(chǎn)生了負面影響[26];貧困和不平等問題的出現(xiàn)導致一部分人口無法獲得充足的食物和營養(yǎng),食物系統(tǒng)面臨著壓力,也導致了全球糧食安全形勢不樂觀[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