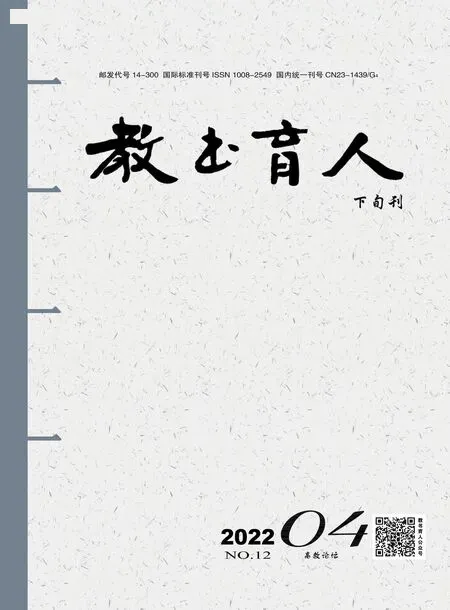中國法制史教學改革探究
——以“馬工程”教材為藍本
劉霓 古強 (宜賓學院法管學部)
當下,在大學的新課程建設語境下,法學所有的核心課都已經正式啟用“馬工程”教材,“馬工程”教材是指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這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對法學教材編寫的指導的進一步深化。中國法制史使用“馬工程”教材意味著中國法制史必須進行重大的教學改革。教學改革是對傳統的中國法制史教學的一種揚棄,它必須建立在對舊有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充分分析的基礎之上。
一、傳統的中國法制史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一)從教學內容分析
中國法制史舊有的教學內容來源于中國法制史的“舊教材”。經過筆者多年的教學總結,舊教材在教學內容上存在諸多誤區:
1.在本學科的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上闡述不詳細
一直以來,我們都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自己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中國法制史教材的編寫也是以這一思想為指導的,學生從事中國法制史研究的時候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應該是以這一思想為指導的。雖然舊教材中會指出中國法制史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但是展開闡述只有三、四百字,沒有充分考慮學生的吸收和運用能力。舊教材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強調不夠和篇幅上的闡述不足,會導致學生對中國法制史的理論指導和研究方法不夠重視,不利于教師在教學中對馬克思主義這一哲學思想的強化。
2.在學術觀點的選擇上更新不及時
從舊教材的目錄架構可以看出,中國法制史教材的內容受舊的學術觀點的影響頗大。舊的學術觀點屬于20世紀70、80年代,認為整個中國的古代法律體系可以用“諸法合體,民刑不分”來概括,這一觀點影響中國法制史教材編寫二三十年。在這一觀點的指導下,中國法制史教材內容對刑罰制度的闡述過分膨脹,其他領域的法律草草帶過,沒有完整客觀地向學生展示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全貌。學生因為對古代除刑法外的其他領域的法律了解不足,導致學生對整個中國古代法律對世界法律文明的貢獻認識不足,這嚴重影響了學生的文化自信。
3.對中國法律制度史的研究時段劃分不準確
舊教材對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時間劃斷,一般都是到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919年—1949年),這使中國法制史的教材內容有所欠缺。雖然在國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后期,解放區人民民主政權的法律制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它和新中國建立之后的法律制度建設成就是無法比擬的。由于舊教材缺少對新中國成立之后的法律制度的那段歷史的論述,因此,對中國法律制度歷史的闡述是不全面的,這不是對歷史真實的客觀反映。
因此,不管從指導思想的進一步明確、學術觀點的持續更新,還是從全面客觀地反映歷史全貌的角度來講,“馬工程”教材的出現都順應了時代的潮流。
(二)從教學方法分析
在舊教材的指導下,過去的教學方法也存在很多失誤:
1.教師教學之初沒有重視對學生已有知識基礎的了解
中國法制史是中國古代各個朝代歷史中的法律制度部分,學生不一定零基礎的。筆者長期的教學經驗中,根據學生的知識儲備,學生可分為三大類:一類是知識儲備偏文史的學生,他們具有中國歷史的基本知識,他們對中國法制史也有大致的了解,但知之不深,有時也存在局部知識記憶上的錯誤。另一類是知識儲備中欠缺文史哲的學生,他們的歷史知識幾乎為零,學習起法制史來相對吃力。還有一類是對文史有著個人愛好的學生,他們是在課堂上聽課時反應最活躍的。不同基礎的學生對教師的教學提出了分層次的要求,這增加了法制史教學的難度。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前就要分別針對不同類型的學生制定對應的教學計劃。
2.教師教學方法側重于講授
傳統的法制史教學方法是側重于教師的單方面講授,這就將導致使法制史的枯燥性“發揮”到極致。很多教師認為法制史也是“史”,將法制史當成歷史來講,對學生來講就是重復上一堂高中歷史課,沒有任何趣味性可言。這也是與新時代下所強調的教學互動背道而馳的。教師以講授為主的教學模式,不僅不能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而且也不能充分發揮法制史這一部門法有著豐富案例的長項。
二、教授具有新時代特色的中國法制史的策略
(一)教學內容上的調整
1.加大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闡發
現行教材用了三頁對學習中國法制史的方法進行闡發。開門見山地指出:“學習中國法制史,首先必須以馬克思主義作為基本的立場、觀點、方法。”緊接著,現行教材用比較長的篇幅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具體的針對性的中國法制史的研究方法予以詳細地闡發。可以看出,教材編寫此部分的目的是為了將馬克思主義在這一部門法中的指導作用落到實處,務必讓學生掌握從而得以靈活運用。然而,筆者在教學中發現,學生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全面把握上是欠缺的。因此,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首先應該對學生進行提問,了解他們在其他學科的學習中已經掌握的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然后,教師再進行補充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介紹。最后,教師應該向學生舉例說明我們在學習中國法律制度史的過程中,如何具體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并且在學習中貫穿馬克思主義的普遍聯系觀、發展觀、矛盾論。比如,馬克思恩格斯語:“野蠻的征服民族必然被被征服民族的先進文明所征服。”這一結論,與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的演變規律可以相互印證。從元和清這些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國家來看,他們都很快地借鑒并吸收了中原王朝的法律制度以發展和壯大他們的國家。只有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我們才能準確地理解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并且得出一個正確的客觀結論。
2.將法律制度史分領域展開講授
“馬工程”教材指出:“中國法制史作為一門學科,統一以近代法律框架為依據,并結合中國法律發展歷史的特點,分別從刑法、民法、行政法、經濟法、訴訟法等領域展開。”因此,“馬工程”教材在目錄的構架上,在秦、漢、唐、宋、明、清各朝代的法律制度下,其章下分節都以立法活動、行政法律制度、刑事法律制度、民事法律制度、經濟法律制度、司法制度的先后順序展開,這種結構的排布方法是一種教材結構及體例的創新。傳統的中國法制史講授過分注重各朝代的刑法典及刑罰制度,這是有失偏頗的。說其偏頗,其原因是:部分教師埋首書本,并不關注宏觀格局,沒有關注到學術觀點在不停往前更新。在中國古代,雖然沒有部門法劃分這一說法,但并不是只有刑法典,比如行政法方面的《唐會典》。而且,很多領域的法律雖然缺少法典,但法律內容依然是豐富的。比如,《大清民律草案》起草時,修訂法律館派遣人員到全國各省去進行民事習慣的調查和收集,說明民事法律制度方面,有大量的習慣法在發揮著作用,這也屬于中國古代法律重要的一部分。教師在教學時,在熟悉新教材的基礎上必須注意到這種學術上的重大變化,以便將新的學術觀點和學術思想準確地傳達給學生。
3.對中國法律制度史的研究時間段劃分及時更新
“馬工程”教材對整個中國法制史的時間劃斷發生重大變化,所以在中國法制史舊教材的基礎上增加了三章。增加的第一章是1949年—197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制的挫折與發展”,增加的第二章是1977年—2010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增加的第三章是“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制”。顯然,新時代下的中國法制史教材的編寫者們,對新中國建立之后的法律制度的撰寫是客觀而全面的,既注重失敗經驗的總結,也注重成功實踐的探討。以香港、澳門的建設為例,香港和澳門的順利回歸和平穩發展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法律制度上的成功實踐。將這段歷史及時地記入中國法律制度史的教材,必定會在學生學習法律制度史的過程中增強學生的文化自信。
4.強調“中華法系”的明確概念
“馬工程”教材在緒論中明確指出:“從公元前21世紀到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古代法律……形成具有獨立民族風格的法律體系:中華法系。”,以《唐律疏議》頒布后為例,當時中國的法律制度是領先于整個東亞的。大量周邊的國家遣使來唐學習,將唐律借鑒到他們自己國家的法律中,實現了母法系對子法系的影響和輻射強度。因此,同大陸法系、英美法系一樣,中華法系也曾經在整個世界文明的發展過程中為法律制度的進步做出過自己的貢獻,這是不可抹殺的。在清末司法改革之后,中華法系已經解體,但中華法系并未消亡,它對整個東亞的法律制度仍有影響。
(二)教學方法上的調整
1.充分利用案例在中國法制史的課堂上進行互動式教學
法律制度史是歷史的一部分,但是又與歷史的教學不一樣。法律制度是立法和司法的結合。由于法律具有其特殊的滯后性,在每一段歷史中,立法是由司法不斷向前推進的,而司法是無數鮮活的古代案例的結合。比如中國法制史中著名的漢朝文帝針對過分殘酷的肉刑所進行的刑制改革,就是因齊太倉令淳于意觸犯刑法,其女緹縈為代父受刑上書而引起的,多數學生對緹縈救父的事跡略有了解,教師可先由他們自行陳述,這樣就很容易誘發學生學習的興趣。以時間離現代較近的明清時期為例,明清的法律形式分為律和例,因為律被封建統治者認為是不變之成法,所以例就是根據司法中的成案對律所做的必要的補充,以應對現實生活不斷變化,這也是對法律具有滯后性的一種必然反應。
同時,案例的使用是靈活多變的,當然,這是建立在教師課前充分準備的基礎上的。比如,西漢法律的指導思想從黃老思想向儒家思想轉變,光從經濟發展這個角度來講,學生不一定能夠完全理解。這個時候就需要教師切入“少年的漢武帝斷防年殺母案”的案例原文,學生通讀之后,在驚嘆漢武帝年僅十二歲就能嫻熟地運用儒家經典斷案之余,也會對成年后的武帝對法律儒家化的巨大推動作用有了一種頓悟。這種案例對教材的輔助理解不是光闡述教材理論能夠實現的。
2.注意兼顧學生不同的知識儲備
作為一名任教多年的中國法制史教師,為了了解學生現有的中國法制史基礎,同時結合學生的知識缺陷進行針對性的教學,筆者在每一次本門課的導論部分上課時,都會請學生起來談一談他們所了解的中國法制史包含什么內容,學生中不乏起來侃侃而談者。文史類的學生在中國法制史的教學中,容易認為自己懂而產生輕視,因此需要教師在以后的中國法制史教學中展現出中國法制史的深度和難度,讓他們引起足夠的重視,同時還需要對他們已有的中法史知識進行不斷地核查和糾錯。對于文史基礎薄弱的學生,他們雖然歷史知識相對薄弱,但是他們往往具備法學所需要的邏輯思維。教師在教學時就要注意歷史背景的展示和鋪陳,以便他們對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產生有一個合理性的推導,從而充分發揮他們的思維優勢,促進他們對法制史知識的快速吸收。
3.將古代法律制度與現代法律制度進行對比式教學
從事中國法制史教學的教師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都會發現,中國古代法律制度與現代法律制度也是有共通性的。以法律制度中的容隱這一制度為例,中國古代法律制度中,法律的儒家化自西漢就開始了,其中著名的“親親相隱不為罪”的法律制度,就是基于儒家“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的思想所產生的。而當今的刑法罪名中的遺棄罪等罪名,因為犯罪人的遺棄行為受害人不親自上訴法院不予處罰的特點,被歸入親告罪這一類別,親告罪從立法原理上講也屬于容隱制度。雖然說古代和現代設計容隱制度的初衷并不相同,古代產生容隱制度的原因是統治階級企圖用儒家綱常統治百姓,而現代的親告罪在立法理念上是因為考慮到了親屬之間的血緣和親情,有可能受害人不愿意法律的介入,再加上親告罪所涉及的罪名社會危害性都不大,在這一前提下,國家對受害人出于親情不愿告訴這種主觀愿望予以充分的尊重,也是為了整個社會的和諧。容隱制度不僅是在中國古代,直至今天在中國,乃至整個東亞的法律制度中都有著生命力。容隱制度這種持久的生命力,正是新教材所強調的中華法系已解體未消亡的實證。通過教師這種古今、中外的對比,學生的視野豁然打開,對中國古代法律制度有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學習興趣更為濃厚,文化自信得以提升,學生產生一種學習的內驅力,對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理解和運用的能力也必然能夠躍上一個新的臺階。
“馬工程”教材是適應時代的產物,作為時代前沿的高校教師群體,肩負著教學改革的神圣使命。“馬工程”教材的廣泛使用,不僅對中國法制史這一部門法的課程建設有著重大意義,同時也能弘揚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在新時代下,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當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文化自信正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里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馬工程”教材正是始終貫穿著文化自信這種價值觀。教師必須在教學中將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內容的豐富性和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對世界文明所做出的的貢獻傳遞出去,這是新時代中國法制史教師的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