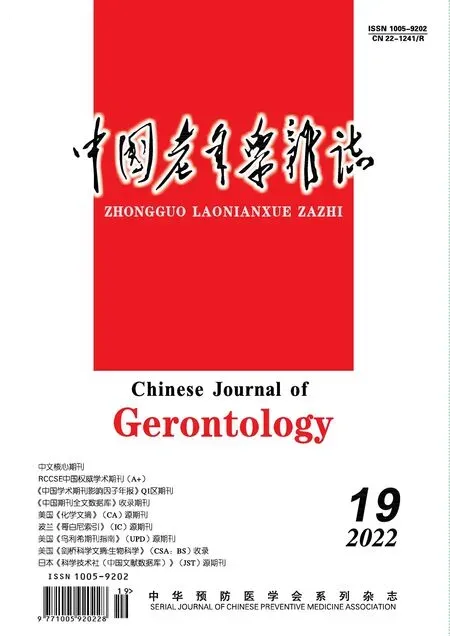從瘀血論治腦出血
崔雅斌 崔成姬
(長春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吉林 長春 130021)
腦出血(ICH)在所有的急性腦血管病中約占30%,而急性ICH(AICH)死亡患者的比率高達30%~40%〔1〕。情緒、精神、勞累,三者過度都可能引發ICH。大多數ICH患者愈后較差,其后遺癥往往導致老年患者喪失勞動及生活自理能力。ICH發病后,腦內血腫隨即形成,后隨著血腫增多,開始出現腦水腫,水腫直接引起顱內壓升高,甚至導致腦疝出現并危及生命。ICH在中醫里屬于出血性腦卒中范疇,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醫學界普遍認為活血化瘀藥用在治療AICH時可能使其出血加重或發生再次出血,因此禁止在ICH時使用活血化瘀藥〔2〕。近些年,通過不斷的臨床實驗研究觀察,認識到活血化瘀藥物治療ICH時對促進腦血腫的吸收有很好的效果〔3〕。清·唐容川在《血證論》中說道:“凡有所瘀,莫不壅塞氣道,沮滯生機……經隧之中,既有瘀血踞住,則新血不能安行無恙,終必妄走而吐溢矣。”指出瘀血阻滯新血生成,影響血病的恢復,指導在治療出血證時驅除瘀血是治療要點,ICH亦是如此。
1 ICH瘀血理論認識
腦卒中早在《內經·風論》中就有記載“風之傷人也……或為偏枯……”《素問·生氣通天論篇》里說“怒急氣上之人,體內陰陽紊亂,氣與血上沖于腦,而生薄厥。”《素問·調經論篇》云:“血之與氣,并走于上,則為大厥。”腦卒中的病機與血有關,氣與血上沖于腦,血液溢出腦絡,導致神機失用,發為此病。唐宋以前醫家認為“外風”是致病的原因,唐宋以后認為是“體內之風”導致此病,《丹溪心法》曰:“中風大率主血虛有痰……次養血行血:半身不遂……在左屬死血瘀血。”指出治療腦卒中要活血養血、祛瘀祛風。李中梓在《醫宗必讀》中說道:“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他建議應以活血化瘀治血來達到治療風證的目的,如果血液運轉正常,則風證自然好轉。清朝的王清任在《醫林改錯》說道:“夫元氣藏于氣管之內,發布周身,左右各得其半。人行坐動轉,全仗元氣”“元氣既虛,必不能達于血管,血管無氣,必停留而瘀。”王清任認為人的行、坐、動、轉需要元氣的維持,當元氣虛時可致腦卒中偏癱,同時也認為瘀血亦是影響腦卒中的一個病理因素。現代醫學經過研究已經證實了AICH患者發病期間血液相對黏稠。有學者研究157例ICH患者的血液流變學指標時發現,血漿黏度、全血黏度和纖維蛋白原均明顯高于正常值,紅細胞變形能力下降,表明ICH患者血液黏度明顯高于正常人,證明ICH患者有明顯的瘀血〔4〕。清唐容川認為“蓋血初離經,清血也,鮮血也,然既是離經之血,雖清血鮮血,亦是瘀血,離經既久,則其血變作紫血。譬如皮膚被杖,血初被傷,其色紅腫,可知血初離經,仍是鮮血,被杖數日,色變青黑,可知離經既久,其血變作紫黑也。此血在經絡之中,雖已紫黑,仍是清血,非血塊也。”“瘀血不去則出血不止新血不生”,他認為瘀血是直接決定血病恢復與否的重要因素,應盡快用藥驅除瘀血,免得留下后遺癥。ICH亦是血證,筆者認為在治療ICH時應及時用活血化瘀藥物驅除瘀血以促進其病的恢復。國醫大師任繼學〔5〕對出血性ICH血瘀的影響進行了表述:“血瘀則痰生、熱結、毒生,瘀塞腦之絡脈,損傷腦之神機……”“若血液稽留而成積,聚而為瘀腫。血瘀水腫,津必外滲,化水,生痰。毒自內生,毒害腦髓,元神受傷,神機受損,神經肌核發生病變,堵塞神明。”可見瘀血本身是致使ICH的主要病因,瘀血亦可衍生其他病理產物損害腦絡。故ICH的治療以驅除瘀為重點。
2 應用化瘀中藥時點分析
現代通過臨床用藥研究活血化瘀藥物來研究證實其有效性,醫學研究指出:活血化瘀藥用于ICH的患者能有效改善出血周圍血液循環,增強吞噬細胞功能,緩解血管痙攣,減輕腦水腫并降低顱內壓,增強神經組織耐缺氧能力〔6〕。
施永德等〔7〕在“離經之血為瘀血”的實驗中觀察到:患者的血液流變學指標有明顯的變化,認為ICH患者血管及血腫處內外均存有瘀血。ICH后腦絡受損,瘀血阻礙血絡運行,在出血的同時形成了血腫,若不及時控制治療,則出現腦水腫,顱內壓升高的首要原因是腦水腫引起,所以治療ICH的關鍵是應及時有效地清除血腫以利于其快速恢復。
近年來,對于各個時期ICH應用祛瘀藥物有不同的爭論,韋志益等〔8〕實驗研究大鼠ICH時結果發現,給AICH大鼠(6 h)注射川芎嗪、黃芪注射液后,可能有繼發性出血和血腫擴大,若在大鼠ICH 12 h及以后用藥,能更好地促進血腫吸收并穩定住血腦屏障,及時減輕腦水腫和顱內壓。沈衛平等〔9〕應用復方丹參注射液治療ICH超早期和亞急性期兩組患者,經過對比發現在超早期應用復方丹參注射液對于患者意識障礙得恢復及促進血腫吸收具有更顯著效果。顧維明〔10〕通過研究ICH發現通過自身調節一般20~30 min停止出血,隨即形成血腫,在6 h內進行血管造影,并未看到造影劑溢出血管外;用同位素標記的紅細胞注射到ICH患者的顱內靜脈血管中,在血腫中也未發現標記紅細胞;根據近些年研究ICH患者的血液狀態,認為在患病期間使用活血化瘀藥物安全有效。楊萬章〔11〕認為雖然常規靜態凝血在3 min內,但腦血管內外壓力差較大,即使止血而因血小板機構松散也容易被解體,這期間使用活血藥容易引起再次出血,所以應該在24 h以后,生命體征平穩,無消化道出血時再著手使用。有研究〔12〕應用破血化瘀藥物治療ICH干預時點的結論表明:在發病6 h內使用破血逐瘀中藥復方,對其3個月隨訪中發現可能增加總不良事件發生。Zeng等〔13〕將365例ICH發病后6 h內的AICH患者隨機分為安慰劑、ICH-1配方(八種草藥,包括水蛭和虻)或ICH-2配方(六種草藥,不含水蛭和虻)。發現AICH患者超早期服用ICH-1配方不會對臨床結果產生顯著的有益影響,但會增加出血風險,這可能是由于ICH-1中包含了核糖體結合位點(RBS)草藥。
隋邦森等〔14〕通過磁共振成像觀察到,血腫一般在2 w內沒有明顯變化。臨床上,ICH患者的神經定位體征在2 w內多無明顯變化,這為使用活血化瘀藥提供了實驗依據〔15〕。筆者認為在ICH發生后6 h內不適宜應用化瘀法治療ICH,確定瘀血無出血傾向后盡早用藥。
3 化瘀法治療ICH用藥分析
活血化瘀的藥種類很多,功效復雜,一般分為活血止血、活血祛瘀、活血行氣、活血利水、破血逐瘀、活血養血等中藥。
活血止血中藥有三七、大黃、茜草、赤芍等,三七、大黃活血止血且不留瘀的作用可以用在ICH最早的急性期,三七含有人參皂苷,能保護腦細胞,很大程度上提高腦細胞耐缺氧能力,且止血效果好;大黃主要含有蒽醌類化合物,能有效減輕腦水腫,增加缺血性半暗區血供,促進血管出血部位凝血,減少出血;腦神經恢復后,患者可以在早期蘇醒恢復意識,后期身體恢復功能加快〔16,17〕。孫大軍等〔18〕研究赤芍總苷對血瘀大鼠的影響,發現其具有抗血栓、降低血液黏度、改善血液流變性等作用。活血祛瘀類中藥有桃仁、紅花、牛膝、丹參等,桃仁活血通便,對于ICH后便秘的患者有很好的療效;丹參主要含有丹參酮、異丹參酮、隱丹參酮等成分〔19〕,研究觀察表明丹參具有雙向調節凝血機制的作用,能夠降低血液的黏度及阻止血小板的相互聚集,調節和改善微循環和纖溶系統,促進血腫吸收〔20〕。
涼血通瘀藥方中含有大黃、水牛角、生地黃、牡丹皮、赤芍和石菖蒲,用于ICH瘀熱阻竅證的患者〔21〕。這部分患者,腦中血分瘀熱積久者邪熱愈熾,血氣蒸騰于上,瘀阻益甚,最終導致患者生風化火成痰。這部分患者使用熄風清火化痰類藥物、平肝潛陽類藥物治療,往往達不到較好的效果。改用涼血通瘀藥,方中水牛角及大黃都是君藥,兩藥并行,清熱涼血,能夠熱清血自涼、血涼熱自清。生地黃為臣藥,滋陰的同時去積聚,化瘀熱。以牡丹皮、赤芍作為輔藥,活血化瘀,阻止血熱成瘀,還能預防生風化痰。石菖蒲起引藥作用,醒神益智,開竅豁痰,諸藥合用,其用最佳。涼血通瘀藥可以將患者風痰火亢源頭切斷,一方面防止瘀郁生熱,將瘀熱、化火、生風、釀痰之病理鏈阻斷;另一方面通下瘀熱,順降氣血,給邪以出路,以釜底抽薪,達到上病下取,以下為清的目的,從而平抑肝風痰火上逆之勢。
活血行氣藥有川芎、延胡索、郁金等,氣與血相互依存影響,氣行則血行,血瘀則氣滯,川芎、延胡索、郁金行氣活血,能加速血腫部位瘀血的吸收。川芎中的川芎嗪與阿魏酸具有抗血栓形成和促進血管舒張的作用〔22〕。
活血利水中藥有益母草、牛膝等,其中牛膝有引血下行作用,配合益母草用于急性期及恢復期。破血逐瘀藥有三棱、莪術、水蛭等,一般用于有癥瘕積聚等證候,因逐瘀力度強,用量宜少,早期一般不用,以免引起再出血。活血養血中藥如當歸,一般用于恢復期肢體偏癱血虛等證。有臨床研究用丹參、紅花、桃仁、雞血藤、地龍、赤芍、川牛膝等藥物治療ICH,對比常規脫水、腦細胞保護劑和自由基清除劑等,前者有效率達91.2%,后者有效率70.6%〔23〕。另外,目前臨床上中醫研制的一些祛瘀中成藥治療ICH有較好的療效。如復方丹參注射液、川芎嗪注射液、銀杏葉注射液,對血小板聚集有抑制作用,并擴張小動脈,使微循環和腦血流量得到改善及調節。腦血康口服液中含有水蛭素,能促進凝血酶和血小板的分離,防止纖維蛋白原轉化為纖維蛋白,抑制凝血因子Ⅴ、Ⅶ和Ⅷ的活化和凝血酶誘導的血小板反應,具有很強的抗凝作用,促進腦水腫的消退以減少腦損傷與炎癥反應,并且能促進血腫吸收〔24〕。筆者認為中醫治療ICH應以整體論治為核心,活血化瘀藥相互配合應用能達到更好的效果。
4 活血化瘀藥治療ICH臨床效果
目前,隨著化瘀療法得到廣泛認可,越來越多的專家教授采用化瘀法治療ICH并取得一定效果。
牟艷春等〔25〕運用活血化瘀法治療高血壓性基底核區ICH患者,較對照組比較,發現運用活血化瘀法在改善病灶周圍水腫方面所用時間更短,能明顯改善神經功能缺損,且用藥安全。顧燕岳等〔26〕以補陽還五湯加減治療ICH患者,發現該方藥有促進血腫吸收,減輕腦水腫的作用,并能改善腦內微循環,預防再出血,對于腦內神經細胞及功能恢復起到積極的作用。劉翔宇〔27〕運用活血化瘀方法(當歸、芒硝、大黃、水蛭、川芎等)治療高血壓ICH(HICH)患者,有效率達95%,可明顯改善腦缺血半暗帶微循環和自由基損害等。劉海艷等〔28〕運用破血化瘀,填精補髓法治療腦出血患者,發現其在出血性腦卒中早期大大減少了患者的內火及痰濕證候要素積分,隨訪觀察時發現應用本法治療的患者在恢復期痰濕證候要素積分仍低于未使用本法治療患者。腦血舒口服液是一種中藥專利藥,包括水蛭、黃芪、川芎、牛膝,是根據中醫理論“氣為血之統領,血為氣之母”的概念設計的。Song等〔29〕在中國相對大規模的人群中評估腦血舒治療急性自發性ICH(SICH)的療效,發現腦血舒口服液是一種有效和安全的治療方法,可減少SICH患者的血腫量和腦水腫。Luo等〔30〕為探討中成藥血塞通注射液(XST)聯合西藥常規治療能否改善HICH患者的血腫吸收,促進神經功能恢復。將224例符合條件的HICH患者隨機分為XST組(血栓通注射液聯合西藥治療)和對照組(單純西藥治療)。發現XST聯合西醫治療能明顯改善腦內血腫吸收,促進神經功能恢復。表明血栓通注射液可能是治療HICH患者的有效佐劑。在陳明海〔31〕研究益氣活血通絡膠囊對HICH小骨窗顯微鏡下血腫清除術患者的影響的試驗中,兩組患者均行小骨窗顯微鏡下血腫清除術,治療組在常規西醫治療的基礎上輔助應用中藥膠囊。結果表明益氣活血通絡膠囊能夠加快術后殘余血腫的吸收、促進損傷后腦功能的恢復、提高患者生活自理能力、縮短住院天數。馬傳鈺〔32〕探討血府逐瘀湯對HICH術后早期高凝狀態的影響作用,發現該方能有效降低HICH術后患者早期的血液黏稠度,顯著改善血液流變學指標,并能促進患者血腫周圍水腫吸收,一定程度上降低顱內新發腦梗死發生率。通過改善血液流變學,促進腦水腫消退,增加腦組織供血供氧,促進神經元修復,改善患者術后神經功能及日常活動能力,為HICH術后的良好恢復創造條件。
5 動物試驗研究進展
活血化瘀療法在動物試驗中也取得了一定進展,證明化瘀藥能有效改善ICH后遺癥。
李妍等〔33〕用活血化瘀藥治療ICH大鼠,觀察大鼠腦水腫與中樞神經系統水通道蛋白(AQP)-4表達的影響,其中活血高劑量組與活血低劑量組均有效果,且活血高劑量組效果明顯優于活血低劑量組,證明活血化瘀藥物可減輕ICH后引起的腦水腫。徐枝芳等〔34〕研究三七總皂苷對早期大鼠ICH神經功能缺損的影響,認為和炎癥介質白細胞介素(IL)-6、基質金屬蛋白酶(MMP)-9可能是導致神經功能缺損的機制之一,通過給藥發現三七總皂苷能有效減輕大鼠ICH后神經功能缺損。陳柏林等〔35〕研究補陽還五湯對大鼠ICH內凝血酶敏感蛋白(TSP)-1及受體CD36的影響,發現該藥通過影響TSP-1和受體CD36對血管新生的抑制作用,來改善血管新生和微循環的重建,且在血管新生結束時上調CD36水平,抑制血管過度增殖,對于ICH后損傷區血管的重建和腦組織恢復發揮了積極作用。王蔚等〔36〕用蛭龍活血通瘀膠囊治療ICH大鼠,發現該藥通過保護血腦屏障,降低血腦屏障通透性,抑制MMP-9、AQP-4表達和PAR-1活化,上調TIMP-1表達,促進缺氧誘導因子(HIF)-1α表達,改善細胞凋亡,減輕腦水腫,從而改善大鼠神經功能缺損癥狀。王學強等〔37〕探討血府逐瘀湯對HICH大鼠神經功能的改善作用及對其p38MAPK信號通路的調控機制,研究表明血府逐瘀湯中、高劑量能減少HICH大鼠的血腫體積,改善行為學和神經功能,減輕病理損傷,推測與上調p38MAPK蛋白的磷酸化水平有關。梁群等〔38〕通過應用活血化瘀中藥制劑腦卒中1號治療AICH大鼠腦卒中1號可使腦組織缺血缺氧改善,B淋巴細胞瘤(Bc1)-2表達增加而Bax表達減少,Bc1-2/Bax值增加。證實腦卒中1號可通過調控ICH大鼠細胞凋亡基因減輕ICH后的神經損傷。
綜上,活血化瘀法治療ICH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經過不斷的實驗研究,總結活血化瘀中藥及制劑對ICH愈后具有安全有效的作用。有實驗〔39〕研究ICH患者血液狀態,發現在急性出血期血液處于濃、黏、凝、聚狀態,說明ICH患者的血液處于瘀血狀態,為使用活血化瘀藥提供了依據。中醫治療疾病整體辨證論治,ICH不僅受到瘀血的干擾,風、火、痰、虛亦是引起ICH的致病原因,應結合患者癥狀,辨證施治。在辨證的基礎上結合活血化瘀,起到促進療效的效果。同時,ICH屬于急癥重癥,也應充分結合西醫檢查療法,如有手術指征時及時進行手術治療。當患者有凝血功能障礙或其他出血性疾病時,或患者血壓:收縮壓>200 mmHg,舒張壓>120 mmHg;有明顯胃腸道潰瘍,長期服用阿司匹林等抗血小板藥物的患者,應禁用或慎用活血化瘀藥〔40〕。在應用活血化瘀藥治療ICH時,應確認無繼續出血風險時在有效的時間窗內及時給予對癥治療。
雖然臨床試驗和動物實驗取得了一定的研究進展,證實化瘀藥在治療ICH有一定療效,但仍有一些療效機制尚不清查,雖有相關可能的推斷來說明其有效性,但仍需要進一步研究來證實并完善治療機制。作為醫者,要充分發揮中醫藥治療特色優勢,結合西醫,發揮最大療效,解決患者的病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