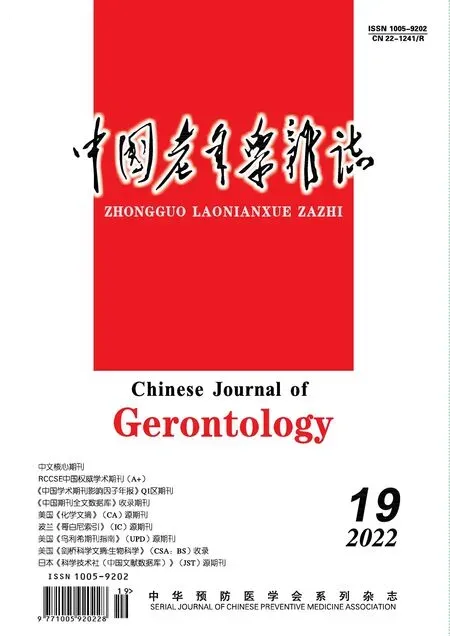神經炎癥介導阿爾茨海默病及運動調控炎癥的機制
閻祉圩 池瑞 彭艷 張日輝
(沈陽體育學院運動人體科學學院,遼寧 沈陽 110102)
早在二十世紀初,Alzheimer醫生就對由于認知功能喪失最終死亡的患者的腦進行組織學分析,在皮層中發現了顆粒性病灶,因為其是首位發現并報道此疾病的學者,因此把這種疾病稱為阿爾茨海默病(AD)〔1〕。對于AD病理的認識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淀粉樣蛋白級聯假說一直是AD病理學的主要觀點〔2〕,它指出AD病理發展順序先是由于淀粉樣β肽(Aβ)產生與清除之間不平衡而導致Aβ積累,繼發微管相關蛋白Tau組成的神經原纖維纏結(NFT)的沉積,并最終引發突觸及神經元功能障礙和凋亡〔3〕。但更多的證據顯示Aβ沉積與疾病臨床表現之間沒有相關性,許多AD患者大腦中沒有Aβ沉積,相反,老年非AD患者大腦顯示出與AD患者一樣多的Aβ斑塊〔4~8〕。這提示淀粉樣蛋白級聯假說并不能完全擬合AD病理,可能存在其他病理機制參與并調控AD進程。來自全基因組關聯研究證實,大部分AD風險基因與神經免疫和炎癥相關,這表明免疫系統介導的神經炎癥在AD病理中起到的作用遠超目前人們的理解〔9,10〕。當前對AD神經炎癥理解是,在AD早期由膠質細胞驅動的免疫反應參與了Aβ清除,但隨著疾病的發展膠質細胞產生過度的炎癥反應又加重了AD的病理進程。
運動已被證明可以通過減少Aβ和tau蛋白沉積來對抗AD病理〔11〕,目前關于運動的抗炎特性也得到了越來越多研究的支持〔12,13〕,但運動能否改善AD神經炎癥及其相關機制仍未解明。本文將綜述AD神經炎癥的機制、神經炎癥對認知及突觸可塑性的影響,并探討運動降低AD神經炎癥潛在的生物學機制,為運動改善AD提供理論依據。
1 AD神經炎癥及其機制
1.1神經炎癥及其標志物 神經炎癥是腦應對感染、腦外傷、自身免疫或中樞神經系統(CNS)中的代謝毒物等刺激而發生的免疫反應,涉及小膠質細胞、星形膠質細胞(AC)、神經元等〔14~17〕。包括AD、帕金森病、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癥、多發性硬化癥等多種神經退行性疾病由神經炎癥所誘導〔18,19〕,膠質細胞活化和炎性因子水平升高被認為是推動上述疾病進程的重要因素。
在靜息或非炎癥條件下,小膠質細胞具有一個微小的且分布神經遞質受體、模式識別受體、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受體的細胞體和許多延伸到微環境的突起〔20〕。這賦予小膠質細胞監測神經元活動和調節突觸可塑性的能力(免疫監控)〔21,22〕。與巨噬細胞類似,被認為是大腦常駐免疫細胞的小膠質細胞按功能差異可分為:分泌炎性因子并伴有吞噬功能受損的促炎型(M1)型,和通過分泌抗炎因子和營養因子改善炎癥,促進組織愈合的抑炎型(M2)型〔23〕。目前認為M1和M2型小膠質細胞轉化是一個動態過程,在疾病過程中小膠質細胞激活可以從M2型變為M1型〔24〕。
研究〔25〕表明,在神經炎癥或局部缺血狀況下AC也可誘導出“A1”和“A2”兩種具有顯著功能差異的表型。當A1型激活時,它會釋放白細胞介素(IL)-1α,IL-6,腫瘤壞死因子(TNF)-α等炎性因子,對神經元產生毒性作用〔26〕。相反當A2型激活時,其可以分泌大量諸如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DNF)、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堿性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bFGF)等促進神經元的存活和生長并參與突觸修復的神經營養因子〔25,27,28〕。AC和周細胞與彼此緊密連接的內皮細胞纏繞形成血腦屏障(BBB)〔29〕。因此當腦內炎癥介導A1型AC活化時,其過度分泌的炎性因子會破壞BBB并使其通透性增加,BBB通透性增強被認為是腦內炎性級聯反應的標志。
1.2神經炎癥誘導神經凋亡 許多促凋亡通路激活是由炎癥誘發的信號分子介導的,這表明神經炎癥可直接介導神經元凋亡〔30〕。凋亡細胞甚至會介導相鄰細胞的免疫反應,例如,凋亡神經元可以釋放含有let-7 miRNA的外泌體,相鄰神經元接受外泌體后,會誘導Toll樣受體(TLR)7激活,并通過進一步激活其下游信號分子,進而導致炎性因子的釋放,最終導致神經退行性病變〔31〕。AD患者的腦脊液(CSF)含有大量的let-7 miRNA,通過鞘內注射將let-7 miRNA胞外引入野生型小鼠的CSF中會導致神經變性〔32〕。據此,神經炎癥在神經凋亡中扮演了雙重作用,其同時是凋亡的誘因和結果,這似乎也提示針對神經炎癥的干預可能改善神經退行性進程。
1.3神經炎癥在基因水平介導AD病理機制 通過結合遺傳連鎖研究、候選基因研究、全基因組關聯研究(GWAS)、全基因組測序和全外顯子組測序研究,已經確定了30多個AD風險位點〔33〕。在這些風險位點中,經過功能基因組學驗證包括排名靠前的兩個風險基因載脂蛋白(APOE)和髓系細胞觸發受體(TREM)2在內的超過50%的基因突變與小膠質細胞和神經免疫密切相關。此外,表觀基因組學分析表明,AD的GWAS基因位點會優先富集與先天免疫過程有關的增強子序列〔34〕。這些研究從基因水平闡釋,神經炎癥對AD病理起到主導的作用。
1.4AD神經炎癥 腦內Aβ沉積和NFTS觸發膠質細胞激活,激活的膠質細胞會改變其分泌特性,以降解和消除Aβ斑塊和NFT為目標,但結果卻收效甚微〔35〕。也有觀點認為膠質細胞活化可能在AD早期,甚至在Aβ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36,37〕。Aβ斑塊被激活的小膠質細胞和AC包圍,小膠質細胞通過分泌含有胰島素降解酶(IDE)的外泌體直接降解Aβ或通過降解Aβ前體蛋白(APP)細胞內結構域(AICD)減少APP的含量,間接減少Aβ的產生〔38,39〕。Aβ斑塊清除的同時伴隨著腦內免疫反應的激活,活化的膠質細胞開始釋放TNF-α、IL-1α、IL-1β、IL-6等炎性因子,炎性因子會誘導鄰近細胞激活,刺激它們分泌更多的炎性因子,并通過減少抗炎因子(IL-4,IL-10)分泌來響應AD活化,最終以前饋的方式維持炎癥〔40、41〕。過量的Aβ會激活小膠質細胞內的NOD樣受體熱蛋白結構域相關蛋白(NLRP)3炎性小體,NLRP3復合物的組裝導致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caspase)-1的裂解和激活,從而觸發下游因子IL-1β和IL-18的加工和釋放,并最終通過細胞焦亡導致細胞死亡,相反NLRP3炎性體缺乏使小膠質細胞偏向M2表型,并導致APP/早老蛋白(PS)1AD模型中Aβ的沉積減少,這說明NLRP3/caspase-1軸在AD發病機理中可能發揮重要作用〔42〕。但Saresella等〔43〕實驗證實至少NLRP3和NLRP1兩種不同的炎癥小體復合物的激活才可以擬合AD相關的神經炎癥。NLRP3炎性小體同樣參與Tau磷酸化的進程,NLRP3炎性體功能的喪失通過調節Tau激酶和磷酸酶降低了Tau過度磷酸化和聚集〔44〕。因此神經炎癥增加可導致高磷酸化Tau啟動,這也與Tau病理在AD中遲發表現相契合。上述慢性活化的小膠質細胞增多并啟動神經元周期性死亡進程,稱為“反應性神經膠質增生癥”〔45〕,此時小膠質細胞多為M1型。目前關于M2型小膠質細胞向M1型極化的具體機制不清,但聚(ADP-核糖基)化(PARylation)可能是小膠質細胞極化為M1型的分子開關之一〔46〕。
遺傳數據表明,AC表達APOE、聚集素、分揀蛋白相關受體(SORL)1等AD風險基因〔47〕。既往研究認為相較于AC,小膠質細胞預先參與AD病理且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但Orre等〔48〕對APP/ PS1小鼠皮層中急性分離的小膠質細胞和AC進行了轉錄分析,發現AC的免疫改變較小膠質細胞更明顯。AC能夠吞噬Aβ肽,這一過程可能取決于其ApoE狀態,這表明ApoE多態性可能通過影響AC的Aβ吞噬而影響發生AD的風險〔49〕。AC參與維持突觸傳導,在AD動物模型的早期,AC的萎縮會對突觸連接產生持久的影響,從而導致認知缺陷〔50〕。AC主要通過提高炎性因子和趨化因子的表達及調節Aβ的產生,內化和降解而在AD的發生和發展中發揮作用〔51〕。AC清除Aβ的機制仍然不清,但有研究證實星形膠質細胞中低密度脂蛋白相關受體蛋白(LRP)-1通過調節基質金屬蛋白酶(MMP)2,MMP9和IDE等降解酶和細胞降解途徑在大腦Aβ清除中起關鍵作用〔52〕。對人類尸檢組織及Tau三轉基因(3xTG)-AD小鼠的腦組織觀察發現,在活化的小膠質細胞旁,堆積的反應性AC聚集在Aβ斑塊周圍〔53~55〕。反應性AC的特征是膠質纖維酸性蛋白(GFAP)的表達增加和功能受損,但結構域沒有改變〔56〕。在大鼠的原代AC和AC-神經元混合細胞培養物中,使用米諾環素可減少AC的炎癥反應,并減少神經元損失、caspase-3激活和caspase-3裂解的Tau產生。米諾環素已顯示抑制大鼠脊髓AC中的核轉錄因子(NF)-κB信號通路〔57〕。這證明NF-κB通路可能參與AC分泌神經炎癥的過程。非編碼RNA(lncRNA)也廣泛參與AD神經炎癥病理過程,許多lncRNA在AD的發展中起重要作用,lncRNAMEG3在AD大鼠中表達下調,上調lncRNA MEG3水平可逆轉大鼠受損的空間學習記憶能力,并通過抑制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蛋白激酶B(AKT)通路來降低海馬神經炎癥水平及AC激活〔58〕。
2 運動參與AD神經炎癥調控
2.1運動介導膠質細胞改善AD神經炎癥 短期或長期運動對腦功能的影響已在各種AD小鼠模型中顯示,包括改善認知能力、下調炎性因子水平,最重要的是改善Aβ沉積和Tau病理〔59〕。運動可通過上調水孔蛋白(AQP)4表達并改變其排列分布,介導Aβ沉積清除的同時下調由Aβ誘發的膠質細胞活化并驅使膠質發生表型極化〔60,61〕。膠質細胞極化既是AD神經炎癥產生的原因又是疾病進程的必然結果。跑臺運動可下調海馬中炎性因子表達,促進抗炎介質分泌并直接介導M1型小膠質細胞極化為M2型達到抑制神經炎癥的目的〔62〕。Leem等〔63〕研究證實跑臺持續3個月可以顯著降低16月轉基因Tau小鼠中Tau磷酸化及小膠質細胞介導的神經炎癥水平。Leem的發現說明即使在疾病晚期,運動對減輕AD病理也可能起到關鍵作用。因此,運動介導膠質細胞改善AD神經炎癥可能是通過清除Aβ、Tau減少對膠質細胞的刺激避免其活化,并通過抑制炎性因子水平、促進膠質細胞表型極化,避免腦內長期處于高度神經炎癥狀態,并抑制由炎癥誘發的神經元凋亡。但也有研究發現運動對AD神經炎癥及相應病理改變的干預效果不佳。Svensson等〔64〕研究表明與久坐組相比,自主運動對五轉基因(5Xfad)小鼠小膠質細胞,細胞因子和Aβ水平均無明顯改善。有研究進一步揭示與久坐APP/PS1小鼠相比,APP/PS1運動組小鼠大腦中可溶性Aβ1~42、β分泌酶、γ分泌酶水平、硝基酪氨酸和過氧化物氧還原蛋白-1水平、膠質纖維酸性蛋白(GFAP)+和離子鈣接頭蛋白-1水平和突觸蛋白和突觸素均無表達差異〔65〕。這證明運動對APP/PS1小鼠Aβ產生及沉積、氧化應激、膠質介導的神經炎癥和突觸喪失均沒有改善效應,甚至是在引入抗氧化劑作為干預手段之后。矛盾的結果可能是由于動物模型的不同及運動方案(運動類型、頻率、強度和持續時間)的差異所導致〔66〕。運動可能通過清除誘導膠質細胞活化的異常蛋白減輕腦內炎癥狀態,并通過抑制炎性因子的激活避免膠質細胞的激活。目前關于運動介導膠質細胞調控AD病理的有效性仍需探討,具體調控機制仍然不明。
2.2運動降低AD神經炎癥促進海馬神經發生 在人類尸檢組織和轉基因小鼠的大腦中都發現海馬神經發生在AD中可能改變〔67~69〕。海馬神經發生可被雙向調控,炎癥被認為會對海馬神經發生產生負向調控,并會導致認知功能障礙〔70〕。海馬中IL-1β的急劇增加導致認知損害并伴隨海馬神經發生下調,Hueston等〔71〕發現IL-1β水平的升高可以選擇性地損害成年雄性SD大鼠模式分離任務。隨后發現,利用慢病毒誘導青春期雄性SD大鼠海馬中IL-1β的慢性過度表達,可觀察到海馬神經發生減少,伴隨著海馬神經突起分支水平的降低,但IL-1β過表達對Y迷宮的模式分離、新穎的物體識別或自發變換行為沒有影響,說明IL-1β不損害神經發生相關的認知功能〔72〕。這種相互矛盾的結果,說明炎癥介導海馬神經減少導致的認知功能障礙的水平可能具有年齡依賴性,考慮到散發性AD患者的年齡,AD患者腦中出現被神經炎癥下調的神經發生也就不足為奇。體外研究表明,在非激活狀態下,小膠質細胞可以釋放因子挽救神經干細胞,誘導神經元分化并可以增強和延長培養細胞的神經發生潛力〔73〕。然而,激活的小膠質細胞會導致腦穩態改變并產生細胞因子,引發廣泛性的腦內炎癥,并通過減少神經干細胞的存活而抑制海馬神經發生〔74,75〕。
相反,運動卻可對海馬神經發生產生正向調控,Tapia-Rojas等〔76〕研究證實自主運動可減少APP/PS1小鼠海馬神經元凋亡,使齒狀回中的神經發生增加1.3倍,并使皮層及海馬區小膠質細胞激活1.5~2倍。Littlefield等〔77〕利用脂多糖(LPS)誘導老年小鼠腦內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活化及由炎癥介導的海馬神經發生的減少,他們證明自主跑輪可上調BDNF共標記的小膠質細胞(M2型)的表達,并通過抑制腦內神經炎癥水平來介導海馬神經發生增加。CD200是一種抗炎糖蛋白,在神經元、T細胞和B細胞中表達,其受體(CD200R)在膠質細胞上表達,AD患者和小鼠模型均顯示出年齡相關或Aβ誘導的CD200減少。將表達CD200的腺相關病毒注射入AD小鼠海馬中,恢復了齒狀回的亞顆粒和顆粒細胞層中神經祖細胞的增殖和分化,體外研究證明,CD200還增強了小膠質細胞對Aβ的吸收〔78〕。運動已被證明通過上調CD200/ CD200R軸的表達,抑制帕金森小鼠小膠質細胞激活,并下調腦內炎癥水平〔79〕。也有研究證實〔80〕,腦卒中后小膠質細胞誘導腦內高表達的炎癥水平可通過跑臺運動介導CD200/ CD200R通路激活來抑制,同時炎癥環境的改善也利于海馬神經發生。據此,推測運動降低AD神經炎癥促進海馬神經發生可能是通過CD200/ CD200R通路。跑臺運動也可通過下調腦內炎性因子水平及AC活化促進腦內整體抗炎環境,通過調控海馬齒狀回區的免疫活性增加了成年小鼠的海馬神經發生,同時跑臺運動還可以通過控制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信號通路調節神經發生和大腦免疫活性〔81〕。上述實驗都表明運動可以下調因炎癥介導的海馬神經發生下降。但也有實驗證明〔82〕,運動雖可有效改善LPS下調的海馬神經發生和學習記憶能力。這種有益效應卻不是由于炎癥反應的改變,而是由于恢復了LPS減少的BDNF信號通路。
2.3運動介導BBB通透性調節神經炎癥 腦中Aβ積累會誘導中樞彌漫性神經炎癥,因此清除Aβ顯然成為改善AD病理的關鍵,參與中樞Aβ清除的結構很多,其中發揮主導作用的是BBB。BBB上分布兩類內皮Aβ轉運蛋白即負責把Aβ從腦內轉運到外周的LRP1和將Aβ從外周轉送到腦內的糖基化終末產物受體(RAGE),RAGE/LRP1的動態平衡是維持腦內Aβ穩態的關鍵。炎癥會誘導BBB處LRP-1水平降低和RAGE水平升高,導致腦中Aβ向周圍轉運失敗。BBB功能障礙同時會觸發神經炎癥和氧化應激,然后增強β-分泌酶和γ-分泌酶的活性,最終促進Aβ的產生。Aβ在腦和BBB功能障礙中的逐步積累可能會成為反饋回路,從而導致認知障礙和AD發生〔83〕。運動可對BBB產生積極效應,長期運動可抑制APP/PS1小鼠AC的激活及CD10和IDE兩類Aβ降解酶的表達,并下調RAGE的表達水平,但LRP1水平卻無顯著改變〔84〕。這說明運動通過減少腦中Aβ水平而使Aβ降解酶及Aβ轉運蛋白活性降低,并通過降低AC激活對BBB起到保護作用。miRNA在BBB功能障礙中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它們在包括炎癥在內的許多病理中起著重要作用。炎性因子TNF-α和干擾素(IFN)-γ已被證明下調幾種特定的miRNA。miR-125a-5p,調節BBB緊密性并防止白細胞外滲,其在炎癥狀態下被下調〔85〕。運動可以介導內皮細胞分泌miR-98-3p和miR-125a-5p,兩種miRNA均可減輕內皮炎癥起到血管保護效應〔86〕。miR-143可調控PUMA(一種促凋亡分子),PUMA與BBB損傷和通透性有關并且會降低緊密連接(TJ)蛋白表達,miR-143/ PUMA軸還參與調控小膠質細胞活化〔87,88〕,而運動可以下調miR-143的水平〔89〕。綜上,運動可以通過調控影響BBB的miRNA而降低由炎癥誘發的BBB功能障礙,降低AD神經炎癥水平。
2.4不同運動對AD炎癥調控的差異性分析 急性運動可引起即時抗炎效應,盡管這些作用是短暫的,但定期運動卻可固化這種抗炎作用〔90〕。運動可在外周器官中誘發整體抗炎作用,這些抗炎作用擴散到大腦,降低了神經退行性疾病發展的風險〔91~93〕。運動也會直接干預中樞免疫反應,對AD神經炎癥起到關鍵調控作用。但應注意不同的運動強度可能導致免疫反應激活類型和程度的差異,由于機體對運動的生物反應與免疫反應之間存在劑量反應效應,例如高強度的體育鍛煉已被證明能夠促進炎癥水平〔94〕,據此運動對機體免疫調控會產生雙重影響。針對AD患者進行實際運動處方設計時考慮到患者年齡風險及體能儲備不足等因素都不應對其進行高強度運動。
綜上,到目前為止AD病理機制仍然未知,神經炎癥雖然近期被認為是驅動AD病理最重要的部分,但仍不清楚它是疾病的原因還是后果。運動是否能改善AD神經炎癥及相應的病理改變也存在爭議。矛盾的結果可能來自動物模型的不同和運動方案(運動類型、頻率、強度和持續時間)的差異。被炎癥負向調控的海馬神經發生也可通過運動誘導正向調控,但其具體機制仍然不清。神經炎癥導致BBB功能障礙可被運動誘導的miRNA所修復,但是否還有其他機制仍待今后探究。本文首次嘗試探討了運動介導miRNA調控炎癥誘發BBB功能障礙的可能機制,為運動改善AD提供理論參考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