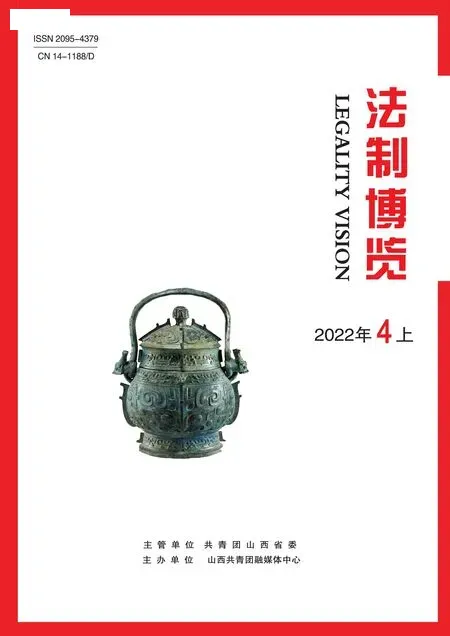從政府法律顧問視角談公平競爭審查
陳換弟
廣東陳梁永鉅律師事務所,廣東 東莞 523000
一、適用依據
(一)直接依據
經公開渠道獲悉,直接就公平競爭審查制度作出規定的規范性文件主要包括如下:
1.國發〔2015〕26號《國務院批轉發展改革委關于2015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意見的通知》;
2.國發〔2016〕34號《國務院關于在市場體系建設中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意見》(以下稱“國發〔2016〕34號文”),就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作出頂層設計;
3.國辦函〔2016〕109號《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同意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的函》,明確提出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
4.發改價監〔2017〕1849號關于印發《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實施細則(暫行)》的通知,其后被國市監反壟規〔2021〕2號關于印發《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實施細則》的通知廢止及替代。自2021年6月29日發布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實施細則》(以下稱“《實施細則》”)對2017年10月23日發布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實施細則(暫行)》作出修訂、增強制度可操作性和可預期性。
(二)間接依據
現行國發〔2016〕34號文所規定之“四個方面18條標準”,以及《實施細則》圍繞國發〔2016〕34號文所規定的剛性標準予以條分縷析后進一步細化而形成的數條二級標準,并非橫空出世,在現行法律法規中基本有對應的上位實體依據,具體主要包括:
1.1998年5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
2.2004年7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
3.2008年8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
4.經修訂并于2014年8月3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及2015年3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
5.經修訂并于2017年12月28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及經修訂并于2019年3月2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實施條例》;
6.經修訂并于2019年4月23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
除國發〔2016〕34號文、《實施細則》以及各省區市印發的實施方案中對進行公平競爭審查這一節點作出規定外,國務院辦公廳及部分部委亦通過各種形式明確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制定應當進行公平競爭審查該項工作,具體主要包括:
1.國辦發〔2018〕37號《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行政規范性文件制定和監督管理工作的通知》①《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行政規范性文件制定和監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一條、第二條。;
2.中國人民銀行令〔2018〕第3號《中國人民銀行規章制定程序與管理規定》②《中國人民銀行規章制定程序與管理規定》第十五條、第十八條、第二十二條。;
3.國家稅務總局令第45號《稅務部門規章制定實施辦法(2019修正)》③《稅務部門規章制定實施辦法(2019修正)》第十四條。;
4.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令第8號《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規章制定程序規定》④《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規章制定程序規定》第十八條、第二十條。。
二、適用范圍與責任主體
(一)適用范圍
1.事項范圍
根據國發〔2016〕34號文,公平競爭審查適用于和市場主體經濟活動有關的規章、規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以及行政法規和國務院制定的其他政策措施、地方性法規的制定與出臺。
相較國發〔2016〕34號文,《實施細則》第二條對適用范圍予以進一步具體化,尤其是對“涉及市場主體經濟活動”的界定,通過列舉方式予以明晰;同時,明確將“一事一議”形式的具體政策措施的制定與出臺一并納入適用范圍。
結合上述規定,筆者理解,行政機關以及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在制定不涉及社會公眾或不涉及在客觀上影響到經營者在市場中競爭的內部工作方案、內部管理規范、工作意見、工作部署等文件,原則上不適用進行公平競爭審查的要求。
2.主體范圍
根據國發〔2016〕34號文以及《實施細則》,所有行政機關、包括國務院在內,涉及上述適用范圍事項的有關舉措制定以及規定的出臺,開展公平競爭審查已然為必經的法定程序要求之一;且,基于法律法規授權而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制定與出臺上述規定及舉措也同樣應當按照規定開展公平競爭審查。
(二)責任主體
1.首要責任主體
根據國發〔2016〕34號文以及《實施細則》,我國現階段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實行自我審查為主的模式,因此,現行規定明確政策措施制定機關為公平競爭審查的首要責任主體。通過自我審查的模式對自身所實施的內容主動進行公平競爭審查,從而在第一線避免或減少對市場競爭的違規干預或不當干預[1]。
2.次位責任主體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稱“《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以下稱“《地方組織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以下稱“《反壟斷法》”),上級行政機關為公平競爭審查的次位責任主體;該等上級行政機關可通過政務報批模式對下級行政機關所實施內容進行公平競爭審查,從而避免或減少對市場競爭的違規干預或不當干預。
3.補充責任主體
根據《憲法》《地方組織法》以及《反壟斷法》,各級權力組織為公平競爭審查的補充責任主體;該等權力組織從整體上可通過立法監督模式(如規范性文件備案審查等)對被監督對象所實施的內容進行公平競爭審查,從而避免或減少對市場競爭的違規干預或不當干預。
4.末位責任主體
根據《反壟斷法》,競爭執法機構為公平競爭審查的末位責任主體;該等競爭執法機構可通過多種模式(如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競爭文化/政策倡導等),針對可能會對市場競爭造成影響、各式各樣的政府干預行為開展公平競爭審查,從而避免或減少對市場競爭的違規干預或不當干預。
三、政府常年法律顧問參與公平競爭審查的方式
(一)以自我審查為主的現狀
無論是早年的國發〔2016〕34號文、《實施細則》,還是市場監管總局公告2019年第6號《公平競爭審查第三方評估實施指南》,無一例外地提倡并鼓勵借助第三方專業優勢、準許委托第三方協助審查責任主體開展公平競爭審查工作以及進行定期評估。
然而,經公開渠道獲悉,自我審查仍然是我國現階段公平競爭審查制度采取的主要模式。官方公開通報的審查案例中公平競爭審查均是由政策措施制定與出臺的主體自行開展,暫無了解到委托第三方單獨開展專項公平競爭審查或者評估個案。
(二)以合法性審查方式參與
由于我國現階段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實行以自我審查為主的模式,故,政策措施制定機關常年法律顧問在開展公平競爭審查時更多為協助審查的角色。政策措施制定機關常年法律顧問在參與公平競爭審查時往往并非以專項審查或評估的方式進行,而是基于常年法律顧問合作,偶發式對制定并擬出臺的政策措施進行合法性審查過程中對照《實施細則》規定的細化標準予以一并審查,在合法性審查中融入或體現進行公平競爭審查的內容,以此協助負責制定及出臺政策措施的責任主體對標審查標準完成自我審查工作。
但是,上述由常年法律顧問以偶發式、嵌入式開展的協助審查,卻并不能稱之為法律意義上的第三方獨立專項審查或評估,同時考慮到參與處理的深度與廣度有所不同,把是否違反公平競爭標準偶發式嵌入合法性審查工作時,常年法律顧問通常無法就嵌入式協助進行公平競爭審查的情況出具單獨審查意見或評估報告。
作為政策措施制定機關的常年法律顧問,盡管目前并非以專項委托的方式開展公平競爭審查,但基于現行法規對政策措施的出臺有要求進行公平競爭審查的指定動作,因此,在對政策措施進行合法性審查時仍需關注是否存在公平競爭審查標準的情形,并結合審查的情況向政策措施制定機關提示潛在風險(如有)。
四、疑惑與建議
(一)以定期發布典型案例方式統一對審查標準的精準理解和把握尺度
相較國發〔2016〕34號文所規定之“四個方面18條標準”,盡管《實施細則》圍繞剛性標準進一步具體化與明晰;但,畢竟公平競爭審查無論是在專業程度還是政策性,相較已成常態化的合法性審查而言更強,難免會導致負責制定政策措施的機關單位、上級行政機關、各級權力組織及競爭執法機構均可能會對公平競爭審查的標準存在不同的認識和理解,從而導致在審查、糾正、執法等層面會出現偏差。
尤其在自我審查是我國現階段公平競爭審查制度采取的模式這一現狀下,對政策措施制定主體的審查能力及理性會有較高的要求;在進行自我審查時,有可能對于審查標準未明確,進而造成對違法性要素認識不到位,致使對開展公平競爭審查的效果造成一定負面影響。
鑒于此,基于盡可能讓所有執行單位統一各自對公平競爭審查各項標準的理解程度,確保公平競爭審查制度能夠精準落地等多方面綜合考慮,可由競爭執法機構定期歸集各省區市查處之違反公平競爭審查標準的典型案例并予以整體梳理與評查后每月或每季度予以定期公開發布。
(二)進一步完善及細化例外規定的適用條件及程序等
國發〔2016〕34號文以及《實施細則》雖然規定了適用例外規定的情形及條件,但現有規定較為原則及抽象,如適用例外規定情形的具體內涵暫未明晰,對于“不可或缺”等諸多適用條件的具體判斷依據、具體情形,以及期限要求等方面暫未作具體細化規定。
此外,現行關于公平競爭審查的配套文件暫未就例外規定的適用情況作出具體細化規定,如批準適用例外規定的機構、批準適用例外規定程序等事項暫不明確,適用例外規定的情形暫未要求向社會予以公開。
在競爭法視域下,例外規定實質屬于《反壟斷法》上的豁免。作為保障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實施功效的關鍵安排,有必要將例外規定放置在優先考慮的地位,以避免由于權力干涉與規則濫用而造成該項制度的執行效果降低,從而對公平競爭審查的權威性造成損傷[2]。鑒于此,為確保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實施效率及公正性,防止例外規定的濫用,有必要進一步對適用例外規定的情形及條件,以及批準適用例外規定的機構與程序等事項予以細化和明晰。
推行并實施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目的在于對政府不當干預市場的行為進行管控,讓市場回歸良性競爭,并對現行反壟斷法對行政性壟斷規制的不足予以彌補;既是讓“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落地的制度安排,也是實現現有經濟體制深化改革的著力點。時至今日,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確立已五年有余,后續如何使政府行為保持合理性與科學性,并在法治框架內規范實施與迭代完善,是一項重要和長期性的課題,值得進一步探討與研究;作為政府常年法律顧問,如何在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落實及推進過程中有效發揮專業優勢與職能作用,值得業內及同行進一步關注與研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