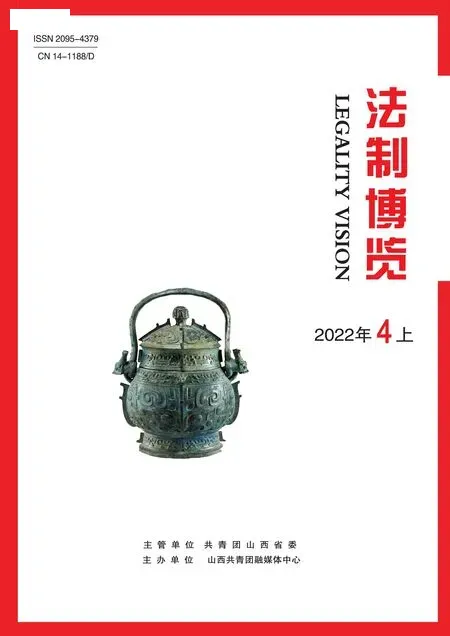刑法中認罪認罰規(guī)則適用研究
章林虎
浙江浙聯(lián)律師事務(wù)所,浙江 杭州 310006
刑事案件審理過程中的認罪認罰規(guī)則適用問題的研究應(yīng)當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一是針對認罪認罰規(guī)則適用階段及案件適用范圍問題進行研究;二是針對認罪認罰訴訟程序構(gòu)造問題進行研究;三是針對認罪認罰規(guī)則適用過程中必須遵守的原則問題開展研究。其中,適用階段和案件范圍的明晰是認罪認罰規(guī)則合法適用的基礎(chǔ),程序則是認罪認罰規(guī)則合法適用的主要依托,原則是對認罪認罰規(guī)則適用得以公開公平公正的重要保證。
一、認罪認罰規(guī)則適用階段及案件適用范圍問題研究
(一)認罪認罰規(guī)則適用階段
如果嫌犯盡早認罪認罰,將更有助于案件進程的開展,因此一般觀點都認為認罪認罰規(guī)則的具體適用階段不應(yīng)當有所限定,從偵查到審理各個階段都應(yīng)當嚴格適用認罪認罰制度。[1]但是,部分知名專家與學(xué)者并不支持在偵查階段實施該制度,這主要是因為擔憂該制度會使偵查部門過于依賴口供,而通過威逼利誘的方法強制嫌疑人認罪,更易于產(chǎn)生冤假錯案。所以,在偵查階段,認罪認罰從寬機制運用的主動權(quán)就應(yīng)當把握在嫌疑人身上,在從寬利益的推動下,可以選擇積極協(xié)助公安機關(guān)負責人開展刑事案件偵查工作,而不應(yīng)當允許公安機關(guān)負責人與其展開供述談判。從有關(guān)法律法規(guī)中也能看出,該制度在偵查階段的運用主要體現(xiàn)為,公安機關(guān)負責人必須知道嫌疑人認罪認罰所可能形成的刑罰后果,對于嫌疑人主動供述認罰的情況應(yīng)當記錄在案并附卷,并且需要在公訴意見書中明確嫌疑人認罪認罰的相關(guān)情形。[2]
(二)認罪認罰案件適用范圍
有關(guān)法律法規(guī)并沒有嚴格限定認罪認罰案件的適用范圍,而是僅僅列出了以下四類除外情況:未徹底損害辨認或限制自身能力的精神病患;未成年人的合法代理人、保護人對未成年人供述認罰存在異議的;行為根本就不構(gòu)成犯罪的;法律兜底條款。[3]其他不能適用的情況。
上述規(guī)定,可以理解為立法人員也主張認罪認罰應(yīng)當運用于一般的犯罪案件中,以至于上面羅列的幾個不適用的情況基本上是因為與精神病患認罪認罰的自愿化程度無法區(qū)分,而未成年人也是特地差異化對待的特殊主體,因此必須更加謹慎地處理。此外,即便精神病患或未成年人不交代案件事實,不認罪認罰,《刑法》對此類主體仍然是相對容忍的,因此仍然可能從輕或減輕刑罰。盡管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所可以適用的犯罪范圍并不是對輕罪重犯的嚴格限制,不過考慮到嚴重暴力行為存在重大的社會危害性,在運用時需要比較慎重,也不能允許以犧牲社會公正換取效果的情況出現(xiàn)。至于不能運用的案件情形,應(yīng)當包括犯罪性質(zhì)惡劣、手法殘酷、存在重大社會危害性的案件,罪犯即便供述認罪也應(yīng)當依法嚴懲,而不能從寬處罰。這也就說明針對那些罪大惡極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使供述認罪,也不應(yīng)該留有從寬余地,而必須嚴懲不貸。
二、認罪認罰訴訟程序構(gòu)造問題研究
(一)偵查階段認罪認罰程序構(gòu)造
在刑事案件偵查工作進行的過程中,偵查部門必須履行告知義務(wù),告訴嫌疑人對其所行使的起訴權(quán)利及其對供述認罰可能會產(chǎn)生的司法結(jié)果,讓嫌疑人自己做出能否自覺供述認罰的抉擇,對供述認罰的情況也要反映到偵查案卷中。在此過程中,嫌疑人可隨意進行供述認罪,由于沒有了時間節(jié)點上的制約,關(guān)押在看守所內(nèi)的嫌疑人也可向看守所內(nèi)的人員、辯護人或值班法官等表達認罪認罰的意向,但有關(guān)人員還需要及時反饋給偵查部門。當刑事案件全部偵破完畢后,對于即將移交起訴的刑事案件,偵查部門還需要在公訴意見書中記載嫌疑人認罪認罰的具體內(nèi)容。
(二)審查起訴階段認罪認罰程序構(gòu)造
認罰表示嫌疑人已經(jīng)接受了相關(guān)司法機關(guān)所主張的實質(zhì)上和程序上的刑罰結(jié)果,而處罰結(jié)果也會隨著刑事訴訟程序的推移而越來越明顯。所以對進行到了審查起訴階段的刑事案件,認罰的主要含義即是與檢察院進行量刑結(jié)果和程序適用狀況的協(xié)調(diào),并簽署具結(jié)書。在這里面包含著控辯協(xié)調(diào)的含義,檢察院可以和嫌疑人雙方進行協(xié)調(diào)互動。在借鑒了其他發(fā)達國家和地方政府在失敗中逐漸成熟起來的成功經(jīng)驗之后,中國選擇將磋商程序規(guī)定在審查起訴階段,既順應(yīng)了國際刑事立法風潮,也符合當前的中國國情,同時避免了在審查階段認罪協(xié)商而引發(fā)的“口供主義”回歸,防止冤假錯案情形的出現(xiàn),解決了“案子多、律師少、法官少”的基本矛盾,既能夠促使嫌疑人及時供述認罰、促進案情分流,也賦予了嫌疑人與檢察院之間很大的磋商空間,在實質(zhì)上也減輕了檢察官的辦案壓力。[4]根據(jù)相關(guān)法律法規(guī),在審查起訴階段,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內(nèi)容程序設(shè)計,主要包括了下列要素:
首先,在中國,犯罪嫌疑人是最主要的協(xié)商主體。按照規(guī)則,必須由檢察機關(guān)領(lǐng)導(dǎo)、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和負責該刑事案件審理的法官一起參加協(xié)商。
其次,在認罪認罰協(xié)議內(nèi)容上,對有關(guān)部門立法也作了相應(yīng)的限制。檢察院可就指控的犯罪及《刑法》適用情形,從寬量刑的意見,以及適當?shù)膶徖沓绦虻仁马椔犎∠右扇思捌滢q護人或值班辯護律師的建議。但認罪的嫌疑人如果是接受了量刑建議和程序適用,則必須在辯護人或值班辯護律師在場的情形下,與檢察院訂立具結(jié)書。“聽取”一詞并不能彰顯嫌疑人身為協(xié)商主體的主觀能動性,乍一看好像排斥了商談的可能性,但是“接受”和“簽字具結(jié)書”則表明了檢察院與嫌疑人之間的確存在著商談的空間,但只是在對商談內(nèi)容上做出了具體的限定,并大致具有如下特征:其一,禁止雙方就犯罪問題及《刑法》的適用展開商談;其二,量刑幅度需要相對明確;其三,確定適用程序。
最后,在認罪認罰協(xié)商程序上,刑事案件移送到檢察機關(guān)后,檢察機關(guān)部門還應(yīng)當向嫌疑人執(zhí)行通知義務(wù),并告訴其享有執(zhí)行的起訴權(quán)利,及其認罪認罰所帶來的法律后果。同時,檢察院還應(yīng)當在就構(gòu)成犯罪、適用法律、判刑意見、運用程序合理等具體事宜聽取嫌疑人的相關(guān)意見的基礎(chǔ)上,在判刑意見和運用程式上與其進行磋商,并提供相對確定的判刑意見和程序合理的意見。嫌疑人如接受了量刑建議和法律程序適用,各方即形成了一致意見,并簽訂具結(jié)書。在整體協(xié)商過程中,辯護人和負責該刑事案件審理的法官也必須全程參加并提出意見,具結(jié)書也必須在他們到場的情況下簽署,以全面保證嫌疑人供述認罰的自愿性。
(三)審判階段認罪認罰程序構(gòu)造
針對由檢察院提起公訴的適用認罪認罰從寬規(guī)定的特殊案例,法庭審判的具體處理程序往往需要區(qū)別于傳統(tǒng)的審判程序,并針對不同的案情類別,在若干環(huán)節(jié)上進行適當?shù)氖÷院途啞7ㄍピ谶@一階段主要的職責是在審查認罪認罰的自愿化,和控辯雙方所簽字的具結(jié)書的真實性和合法性。
首先,對認罪認罰的自覺性審查。認罪認罰從寬規(guī)定適用范圍的前提是嫌疑人必須自覺如實供述罪行,所以,人民法院在審查確定這些案件時,應(yīng)當著重審查確定認罪認罰具結(jié)書中的相關(guān)情形是否是基于嫌疑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作出的,著重審核檢察院和公安機關(guān)是否具有欺騙、威脅和利誘的情形,以確保認罪認罰具結(jié)書是公平公正的,有效保護嫌疑人的合法權(quán)益。
其次,法官們還可通過考察認罪認罰機制在偵查過程或者逮捕階段程序運轉(zhuǎn)上能否符合法律規(guī)定來確認自愿化,比如,偵查部門、檢察院是否認真履行了報告義務(wù),是否聽取了嫌疑人及其辯護律師的建議;嫌疑人有沒有在供述認罰的過程中得到適當?shù)乃痉ㄖС郑约昂炇鹁呓Y(jié)書時辯護律師是否到場等問題。
最后,法院需要對具結(jié)書的真實性和合法性進行相關(guān)的審查。而審查真實性主要是為證明認罪認罰具結(jié)書是嫌疑人的真實意思表達,而不存在威逼利誘和欺騙、威脅等的情況。具結(jié)書的合規(guī)性審查主要分為罪名判刑與程序適用性的審查。法官主要責任在于從實體法上考量罪名與判刑的合規(guī)性,并著重審查經(jīng)法庭確認的犯罪事實與雙方協(xié)商后確認的犯罪事實是否相符,具結(jié)書的具體內(nèi)容有無觸犯《刑法》實體法條款,如是否構(gòu)成了犯罪、罪名的確定和判刑意見是否正確,有無與犯罪情節(jié)和人身危害性相適應(yīng)等。
三、認罪認罰規(guī)則適用必須明晰的原則
(一)堅持“犯罪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
認罪認罰制度的運用,一定要遵循合法證明準則。認罪認罰案件仍應(yīng)當遵循《刑事訴訟法》所明文規(guī)定的證明準則,且不得有例外。遵循犯罪證據(jù)準則是《刑法》規(guī)范的應(yīng)有之義。《刑事訴訟法》明文規(guī)定的犯罪證據(jù)準則應(yīng)當廣泛運用在刑事案件司法領(lǐng)域,例外適用則應(yīng)當由《刑法》明文規(guī)定。認罪認罰的犯罪作為刑事犯罪的組成部分,其犯罪證據(jù)準則在立法上目前并沒有特別規(guī)范,所以,在制度運用的實踐中不能任意改變。另外,認罪認罰從寬規(guī)定的犯罪范圍,能夠拓展至可以被判無期徒刑甚至死刑的重大刑事案件,而這種犯罪的證據(jù)標準的嚴苛程度毫無疑問是要超過了普通刑事案件,且絲毫沒有降低標準的可能性,片面地要求降低證據(jù)標準,顯然是缺乏全面考量問題,有可能會造成顧此失彼,得不償失的重大結(jié)果。值得注意的是,降低證據(jù)準則也面臨著危險。主張減少證據(jù)準則的人往往一味要求辦案效率的提升,但是這些行為并不明智,在當前打擊冤假錯案的司法環(huán)境下,確實不能允許為了體現(xiàn)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司法效率價值,而把傳統(tǒng)司法機關(guān)觀念視為犧牲品的情況出現(xiàn)。而且,減少了供述認罰案例中的證據(jù)準則也意味疑罪從有、疑罪從輕有了合法化、合法性的理由,這也與當前明確疑罪從無原則的目標相悖,也觸犯了當前中國刑事司法體制的底線。
(二)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
認罪認罰從寬規(guī)定的適用范圍的第一個前提,是指嫌疑人應(yīng)當自覺詳細供述自身的犯罪行為,如果交代認罰,就意味著其將在法院作出有罪答辯,即基本放棄了無罪答辯的權(quán)利。該規(guī)定把口供這一證據(jù)的表現(xiàn)形式再次推向了風口浪尖。為了防止公安司法機關(guān)在減少辦案壓力的利益驅(qū)動下,通過刑訊逼供或者其他威逼利誘的方法,促使嫌疑人在違反犯罪事實真相的情況下懺悔認罰,進而促成大量冤假錯案產(chǎn)生的特殊情況,就需要形成一個從偵破到一審、二審全方面保證嫌疑人認罪認罰自愿性的法律制度。
首先,在刑事訴訟各階段,都必須先對嫌犯、被告人作出權(quán)利告訴,讓其完全了解所行使的起訴權(quán)利及其認罪認罰所可能會產(chǎn)生的司法結(jié)果,從而在心理上產(chǎn)生正確的合理期望,并自主地作出抉擇。
其次,確保嫌疑人及時得到合理的司法支持。嫌疑人因為法學(xué)專業(yè)理論知識的不足,往往無法正確地行使自身的法律權(quán)利,無法得到有效的司法保障,所以,為了保護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就必須有具備專門法學(xué)理論知識的人員介入案件。在邀請了專門辯護律師的情況下,辯護律師們當然也會為自身的委托方進行專門的司法幫助。同時針對沒有能力聘請律師的群體,法律法規(guī)中也已經(jīng)制定了司法救助機制,可以為這些群體開展司法救助服務(wù),如法律咨詢、程序選擇、辦理或變更強制措施等。此外,對于適用法律救助制度的案件范圍也是沒有了具體限定的,一般都能夠在嫌疑人供述認罰而缺乏辯護律師的情況下,為其進行司法救助。而辯護律師以及值班律師的加入,能夠幫助嫌疑人更切實地維護正當權(quán)益,從而有效維護了認罪認罰制度的自愿化,也有利于促進嫌疑人認罪認罰案件訴訟進程的順利完成。
(三)把握認罪認罰案件的量刑從寬幅度
犯罪嫌疑人必須主動供述認罪,其主要目的是希望獲得刑罰上的從寬對待。但“從寬處理”目前還只是個概括性的理論管理方針,并沒有實際操作性。
首先,量刑從寬幅度范圍的確定原則。由于實施供述認罰從寬規(guī)定的犯罪限制了刑罰和罪數(shù)之間的協(xié)商,從寬處理主要表現(xiàn)在量刑工作方面,根據(jù)供述認罰的實際情況,按照法律規(guī)定予以從輕、減輕,甚至避免刑罰的辦理。但值得注意的是,對供述認罰規(guī)定所運用的法律表述是人民法院一般應(yīng)當對認罪認罰的嫌疑人的量刑從輕,這也表明了嫌疑人認罪認罰并不能酌情從寬,而是必須從寬,但是從寬處理的量刑幅度必須根據(jù)具體的犯罪實際情況,在《刑法》條文確定的從寬幅度范圍之內(nèi),尤其在共同犯罪案件中,一定要做好認罪認罰從寬處理之后的量刑平衡。
其次,確定從寬幅度的層級性。既然嫌疑人在犯罪案件的不同時期都能夠自愿認罪認罰,并且,考慮到該項制度的本質(zhì)是為了提升刑事案件審理速度以及節(jié)約司法資源,因此,為促使嫌疑人盡快認罪認罰,該項制度的從寬幅度的多少也必須具備層級屬性,從寬幅度在整個辦案進度中應(yīng)該呈現(xiàn)出下降態(tài)勢,在刑事案件偵查階段嫌疑人認罪認罰從寬的量刑幅度應(yīng)該大于審查起訴階段大于案件審理階段。
四、結(jié)語
認罪認罰規(guī)則的合法適用是我國刑事案件審理能夠公平公正、犯罪嫌疑人權(quán)利能夠得到有效保護的一劑強心針,因此從其適用階段、適用案件范圍、在案件審理各個過程中的適用程序以及適用過程中所必須把握的幾項原則問題開展對認罪認罰規(guī)則適用的研究,是對認罪認罰規(guī)則合法合規(guī)適用的最大保障。希望文章可以對相關(guān)學(xué)術(shù)研究人員的后續(xù)研究工作有所啟發(fā),對我國法治社會的建設(shè)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