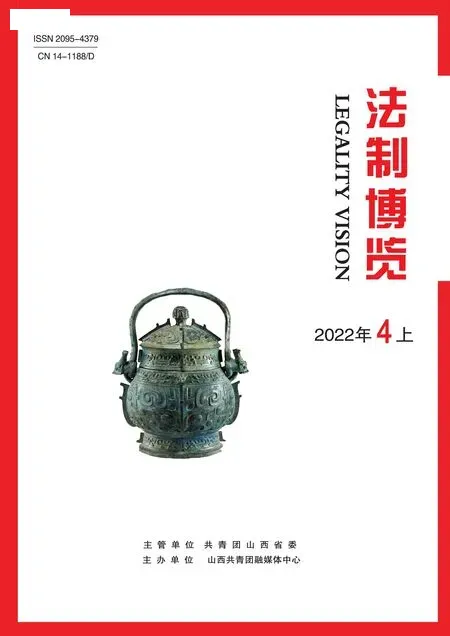電子送達制度在民事訴訟中的具體應用
李幸幸
河南檢察職業學院,河南 鄭州 451191
一、民事訴訟電子送達制度的現行規定
(一)電子送達的概念
民事訴訟送達是指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將有關訴訟文書送交收件人的訴訟行為。電子送達則是指法院利用傳真、電子郵件、移動通信等現代化電子手段進行送達的訴訟行為。相比于直接送達、郵寄送達等傳統送達方式必須以紙質版訴訟文書為載體,離不開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時間投入的特點,電子送達不要求法院與受送達人之間建立面對面的或者其他的直接聯系,也不需要以紙質文書為送達媒介,只需要借助先進的電子技術手段即可實現訴訟文書的虛擬傳送,具有快捷性、高效性的顯著特點。
(二)電子送達的立法規定
1.送達媒介為傳真、電子郵件、移動通信等
2012年《民事訴訟法》以及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規定,只要能夠達到“確認受送達人知悉”目的的“傳真、電子郵件、移動通信”等,都屬于電子送達。而對于“移動通信”,2017年最高院《關于進一步加強民事送達工作的若干意見》將“短信、微信”等方式明確列入其中。
因此,對于電子送達媒介應以發展的眼光作廣義理解,即凡是能夠確認受送達人知悉的現代化電子手段或者特定系統,都屬于電子送達媒介,如傳真、電子郵件、短信、QQ、微信、支付寶平臺、電子送達平臺、訴訟服務平臺等。
2.送達前提為受送達人同意
“受送達人同意”是適用電子送達的前提,主要基于以下考慮:一是,電子送達作為一種新型送達方式,會因為現行立法、司法、技術不夠成熟而存在一定的送達風險,因此為充分保障受送達人的訴訟權利,適用電子送達需要提前征得“受送達人同意”。二是,不同于傳統的送達方式,電子送達以受送達人自覺、主動通過網絡或者借助電子設備接收非紙質版訴訟文書為核心,離不開受送達人本人的積極配合。因此,若未征得受送達人本人同意,電子送達方式要么因欠缺送達地址無法送達,要么因受送達人不知情或者拒絕查看而不被接收,從而無法實現送達目的。
3.判決書、裁定書、調解書不適用電子送達
與傳票、案件受理通知書、起訴書副本等不同,法院的判決書、裁定書、調解書是直接確定當事人訴訟、實體權益的重要訴訟文書,對當事人產生直接的影響,具有權威性和公信力。因此,出于審慎的考慮[1],無論受送達人是否同意,以上三類文書均不適用電子送達。
4.送達日期采用“到達主義”
電子送達由于送達方式的虛擬性,無須送達回證,而以傳真、電子郵件等“到達受送達人特定系統的日期為送達日期”,此即“到達主義”。該送達日期通常與法院送達系統顯示訴訟文書發送成功的日期相一致,但若因有關原因導致上述日期不一致的,則以受送達人證明的到達其特定系統的日期為準。
二、民事訴訟電子送達制度的實踐運行
(一)適用比率總體攀升
2012年以后,隨著電子送達相繼得到《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的明確肯定,全國各地法院紛紛投入到適用電子送達的改革活動中,通過完善送達流程、創新送達方式等一系列舉措,使電子送達在全國的適用比率呈現總體攀升的大好趨勢。例如2019年發布的《法治藍皮書:中國法院信息化發展報告》顯示,電子化送達模式已經在全國鋪開,在接受評估的全國3510家法院中,已經有2951家法院開展了電子化送達,占比高達84.07%。同時,截至2018年,全國82.67%的法院已經開通了訴訟服務網,為當事人提供包括電子送達在內的各類訴訟服務[2]。
(二)送達媒介多種多樣
在具體的送達媒介上,各地法院呈現出多種多樣的態勢[3]。如,全國法院在浙江省杭州鐵路運輸法院等四個試點法院上線統一新型電子送達平臺,支持受送達人通過新浪微博、新浪郵箱、支付寶等三大平臺接收、查詢并下載訴訟文書。廣州市有關法院為受送達人開通訴訟文書送達專用郵箱,由受送達人根據相關密碼登錄郵箱查收并下載文書;深圳市中院上線電子卷宗隨案同步生成系統,借助微信實現法律文書的“一鍵送達”;杭州互聯網法院通過與“天貓”等電商平臺和相關電信運營商合作,建立全國首個大數據深度運用電子送達平臺,從而深度挖掘當事人的寬帶地址、電商平臺賬號等其他常用電子地址。
(三)送達程序高效快捷
相比于直接送達至少需要2~3天的送達時間,郵寄送達歷時3~7日,公告送達需要公告60日才視為送達,電子送達往往在幾分鐘之內即可完成。如浙江省玉環市法院利用“阿里飛狐”人工智能技術的“一鍵送達”功能,僅用時180秒即可完成文書送達的相應操作;江蘇省宿遷市中院與手機三大運營商建立短信送達平臺,最短可在半分鐘內實現送達。
三、民事訴訟電子送達制度的現存問題
(一)送達范圍不統一
在送達范圍的確定上,多數法院嚴格執行《民事訴訟法》的限制性規定,不允許電子送達判決書、裁定書、調解書。但是《杭州互聯網法院訴訟平臺審理規程》卻規定,除裁判文書不得采用電話送達外,訴訟文書(包括判決書、裁定書、調解書)原則上都采用平臺賬戶、手機號、電子郵箱、阿里旺旺的電子送達方式[4]。又如寧波中院制定的《寧波移動微法院訴訟規程(試行)》規定,受送達人同意電子送達的,法院可以向其送達判決書、裁定書、調解書,從而跳出了《民事訴訟法》關于送達范圍的現行立法限制。
(二)送達日期不一致
在送達日期的確定上,盡管現行立法采取“到達主義”,但是各地法院的實際操作卻并不一致。如廣州中院立案一庭庭長徐某表示,該院以電子郵件方式送達訴訟文書時,以文書投遞到送達專用郵箱的日期為送達日期。但是江蘇省高院卻以當事人點擊電子版司法文書的時間為送達時間;上海市某中院則以當事人下載訴訟文書為送達成功的標準并自動生成送達回證。這樣一來,不同法院在送達日期的具體確定上就產生了一定的時間差。
(三)送達人員不明確
實踐中,不同的法院往往安排不同的工作人員負責后續的送達工作。比如浙江省無錫市新吳區法院由承辦法官具體負責其承辦案件的電子送達工作;四川省蘆山縣法院成立法院內部的集中送達工作組,統一、專門負責本院全部訴訟文書的送達工作;北京市房山區法院則采用外包形式聘用外包人員專職從事電子送達工作。
(四)送達技術不成熟
送達技術的成熟度,直接關系到電子送達的送達成功率。就目前而言,電子送達技術正處于發展普及階段,在整體上相對穩定安全,但是同樣也存在著不夠成熟的問題。如短信通知被無故屏蔽,受送達人無法及時收悉;電子郵件無故被系統攔截,無法順利到達對應郵箱;平臺送達程序相對繁瑣,受送達人面臨實際操作困擾;網絡服務器遭受黑客侵擾,導致個人信息泄露、相關文書被篡改等等,這些現實性問題都會成為阻礙受送達人適用電子送達的直接因素。
四、民事訴訟電子送達制度的完善建議
(一)統一送達范圍
現行立法有關“判決書、裁定書、調解書不適用電子送達”的限制性規定主要是出于審慎的考慮。但是筆者認為,實踐中部分法院已經允許上述三類文書適用電子送達,并無有關負面效應;并且2019年12月28日通過的《關于授權在部分地區開展民事訴訟程序繁簡分流改革試點工作的決定》明確提出“經受送達人同意,可以采用電子方式送達判決書、裁定書、調解書”。因此,隨著電子送達方式的普及推廣以及電子送達技術的成熟安全,判決、裁定、調解書適用電子送達也會逐漸從試點變成一種全國趨勢。基于此,筆者相信,在兩年試點工作結束后,《民事訴訟法》應當作出相應調整,明確將判決書、裁定書、調解書納入電子送達的范疇。
(二)確定送達日期
1.對于送達成功的標準,立法和司法上存在“到達主義”和“查閱主義”的爭議。“查閱主義”即以當事人點擊或者下載訴訟文書的時間為送達成功的標準。筆者認為,在電子送達中,由于受送達人已經事先簽署送達地址確認書,其在主觀狀態上已經做好了隨時查閱、下載訴訟文書的心理準備和注意義務,因此訴訟文書到達其特定系統的日期與其查閱、下載訴訟文書的日期通常保持一致,采“到達主義”即可。同時,若采“查閱主義”,則不可避免地出現受送達人以不知情、沒時間或者未查閱為由有意無意地拖延訴訟的情況,從而嚴重地影響訴訟的正常進行和相對方當事人的實際利益。因此,“到達主義”比“查閱主義”更容易維護訴訟的權威性。
此外,實踐中之所以存在以“查閱主義”為送達成功的標準,主要是基于法院送達成功后,受送達人可能不會及時查閱文書而產生的時間差。對此,筆者認為,相關法院可以盡到一定的提醒義務或者采取一定的技術手段,如在送達開始前,法院可以先以短信或者電話的形式提醒受送達人注意查收文書;在短信送達中,與相關運營商合作,設置不可屏蔽、不可攔截、不可忽略的彈屏短信,受送達人只有在進行了相關查閱操作后,才有權繼續使用手機;在送達完成后,若法院后臺在一定期限內未收到“已閱”的回執消息,則可進行再次提醒。
2.確定送達失敗的責任承擔。送達活動涉及送達主體(法院)、送達對象(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和送達第三方(如三大電信運營商、騰訊、支付寶平臺等),因此在送達失敗的責任承擔上,要根據責任主體的不同確定不同的責任承擔方式。如對于因法院工作人員失誤導致的送達失敗,法院應當進行二次送達,并以二次送達成功的日期重新計算送達日期和有關時效期間,由此產生的費用也由法院自行承擔;對于受送達人提供送達地址有誤或者故意拒收文書導致的送達失敗,由受送達人自行承擔相關法律后果和再次送達產生的額外費用,必要時可以對受送達人采取訓誡、罰款等妨礙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對于因第三方合作平臺送達技術不成熟、送達人員不配合導致的送達失敗,對內按照法院與合作平臺簽署的合作協議追究其民事責任,對外仍應由法院向受送達人承擔送達失敗的法律責任。
(三)建立送達隊伍
針對司法實踐中不同法院安排不同送達人員負責電子送達工作的做法,筆者認為,面對當前“案多人少”的矛盾以及“審判中心主義”改革的背景,應當將承辦法官從繁重的輔助性事務中脫離出來,以便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審判工作中;同時,隨著電子送達的專業化要求越來越高,法院內部的集中送達工作組也很難高效完成繁重的送達工作。相比之下,采用外包形式將繁瑣、專業的電子送達工作交由具備一定技術、設備、經驗的外包人員完成,既能保證送達的高效性、專業性,又能極大減輕法院負擔,不失為一種值得推廣的經驗。因此,各地法院應當積極探索購買社會服務,與電信運營商、信息服務公司等外包公司簽署長期的外包合作協議,必要時由外包人員派員駐場,負責全套的送達前聯系、文書送達、回執整理等工作。
(四)完善送達技術
送達技術本身是一個高度精深的專業性問題,一定要充分發揮電信運營商、新浪微博、新浪郵箱、騰訊、支付寶等相關運營商和平臺的專業化技術優勢[5],由法院與其達成深度的戰略合作協議,將現有成熟技術直接應用于電子送達領域,并且不斷開發、優化新的技術手段,為電子送達提供成熟的網絡環境。比如在短信送達中,與三大通信運營商合作,推出彈屏短信,叫醒“裝睡的人”;在微信送達中,與騰訊公司合作,通過電子訴訟文書送達小程序完成人臉識別、訴訟文書推送等工作;在郵箱送達中,與網易等電子郵件運營商合作,建立全封閉的電子郵件系統,保證該郵箱只具有接收、下載法院郵件功能,不具備發送、刪除、修改等其他功能。在平臺送達中,與微博、支付寶等平臺合作,支持受送達人通過登錄平臺網站,查詢和下載WORD、PDF等格式的電子文書。
電子送達作為一種新生事物,在推廣普及的過程中必然面臨各種各樣的現實問題。但是在當前“民事訴訟程序繁簡分流改革試點工作”的廣泛開展下,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借著試點改革的良好契機,伴隨著電子送達立法的完善、司法的統一以及技術的成熟,電子送達制度一定會日益完善,并為健全我國電子訴訟規則發揮應有作用,進而適應我國司法信息化應用和發展進程的總體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