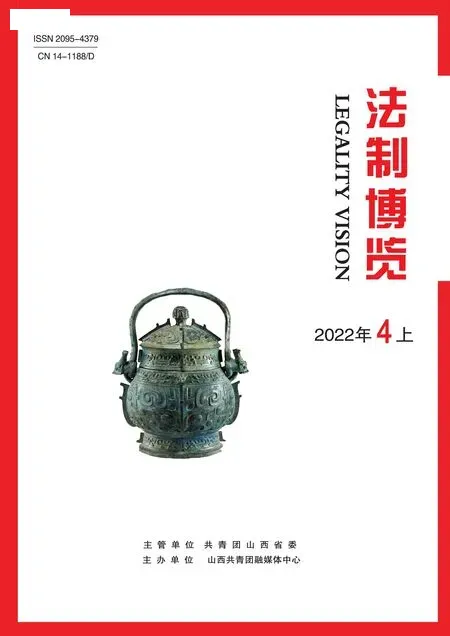大力發(fā)展人民調(diào)解 穩(wěn)步推進社會和諧
羅志紅 陳 靜
1.成都大學,四川 成都 610106;2.四川川達律師事務所,四川 成都 610041
人民調(diào)解源遠流長,中國人民在探索人民調(diào)解之道中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人民調(diào)解制度經(jīng)歷了產(chǎn)生、初步形成、曲折發(fā)展到改革完善幾個階段。現(xiàn)在人民調(diào)解制度還不盡人意,許多專家學者和實務界人士都在探討人民調(diào)解制度,筆者也來談談人民調(diào)解制度。
一、人民調(diào)解的涵義、特征及人民調(diào)解制度的涵義
為了弄清人民調(diào)解的涵義,我們先談論調(diào)解的涵義。“調(diào)解是指在第三方的主持下,當事人自愿妥協(xié),合意解決糾紛的活動。”[1]而人民調(diào)解就是指在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的主持下,依法對民間糾紛當事人進行說服勸解、解決糾紛的一種群眾自治活動。[2]人民調(diào)解具有如下特征:
(一)群眾性。我國規(guī)制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的《組織條例》規(guī)定: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是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下設的調(diào)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我國《人民調(diào)解法》規(guī)定: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的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委員由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居民會議推選產(chǎn)生;企業(yè)事業(yè)單位設立的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委員由職工大會、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工會組織推選產(chǎn)生。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的委員是由人民群眾選舉產(chǎn)生的,他們在基層人民政府和基層人民法院指導下解決人民群眾的民事糾紛。人民調(diào)解解決的是人民自己內(nèi)部矛盾糾紛。人民調(diào)解還吸收社會各界力量、各方面人士廣泛參與。因此,人民調(diào)解具有群眾性。
(二)民主性。由我國《人民調(diào)解法》的相關規(guī)定可知,人民調(diào)解以自愿平等為基本原則,尊重當事人的權利,通過說服教育、耐心疏導、民主討論協(xié)商等方法協(xié)商解決糾紛而不是強行調(diào)解,也不限制當事人通過其他合法途徑維護自己的權利。因此,人民調(diào)解具有民主性。
(三)自治性。我國《憲法》第一百一十一條、《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組織條例》和《人民調(diào)解法》都將人民調(diào)解定位為一種調(diào)解民事糾紛的群眾性自治活動。人民調(diào)解是公民參與糾紛解決的一種重要形式,它排斥了審判程序和行政程序強制解決糾紛的方式,而更側重于糾紛解決的民主自治性。[3]因此,人民調(diào)解具有自治性。
(四)靈活性。人民調(diào)解可采取說服、疏導等多種方法,調(diào)解依據(jù)除了法律、法規(guī)、規(guī)章,還有政策、社會公德等等,調(diào)解程序也沒有嚴格規(guī)定,必要時甚至可以邀請案外人參與調(diào)解以便糾紛的順利解決。人民調(diào)解這種靈活性相比訴訟、仲裁就有其獨特的優(yōu)勢,一定條件下能更快、更有效地解決糾紛。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人民調(diào)解可以不遵守規(guī)范,剛好相反,人民調(diào)解應該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調(diào)解法》等有關規(guī)定進行。
而人民調(diào)解制度是“指我國關于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的組成、調(diào)解委員的權利義務、人民調(diào)解的工作步驟和程序,以及調(diào)解協(xié)議的效力等與人民調(diào)解相關的法律規(guī)范”。[4]
二、人民調(diào)解制度的歷史嬗變
人民調(diào)解的前身是具有悠久歷史的民間調(diào)解。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初心是為人民謀幸福,中國共產(chǎn)黨賦予與政府、公共相關的事務人民性,民間調(diào)解就變成了人民調(diào)解。
人民調(diào)解制度萌芽于20世紀20年代初期中國共產(chǎn)黨人領導的早期農(nóng)民運動中。1923年,中國農(nóng)民運動的先驅彭湃同志組織海豐農(nóng)民成立海豐縣農(nóng)會,調(diào)解農(nóng)民內(nèi)部矛盾,維護農(nóng)民利益。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chǎn)黨在全國建立了十幾個革命根據(jù)地。在根據(jù)地,鄉(xiāng)、村農(nóng)會負有調(diào)解民間糾紛的職能。[5]
抗日戰(zhàn)爭時期,各抗日根據(jù)地民主政府大力倡導和扶植各種形式的人民調(diào)解工作,建立起大批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促進了人民調(diào)解制度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
解放戰(zhàn)爭時期,有些解放區(qū)發(fā)布了有關調(diào)解工作的規(guī)范,標志著人民調(diào)解工作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人民調(diào)解工作進一步發(fā)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人民調(diào)解工作進入新的發(fā)展時期。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了《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暫行組織通則》,標志著人民調(diào)解制度在我國法律地位的確立。之后很長一段時期,停止了人民調(diào)解工作。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人民調(diào)解制度進入恢復和發(fā)展階段。1982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9年通過《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組織條例》,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關于審理涉及人民調(diào)解協(xié)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guī)定》、司法部發(fā)布《人民調(diào)解若干規(guī)定》,為人民調(diào)解進一步完善打下了堅實的基礎。201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調(diào)解法》,對人民調(diào)解工作的法制化、規(guī)范化具有重要意義。
三、我國現(xiàn)階段人民調(diào)解制度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人民調(diào)解制度存續(xù)了很長時間,為解決民間糾紛,保障經(jīng)濟發(fā)展,維護社會秩序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生活的快速變化,人民調(diào)解制度出現(xiàn)了一些不適應新時代的問題,具體表現(xiàn)在:
(一)行政干預過多,損害了人民調(diào)解的本性和應有價值
2002年,司法部出臺《人民調(diào)解工作若干規(guī)定》,規(guī)定可以在鄉(xiāng)鎮(zhèn)、街道設立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這樣的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由鄉(xiāng)鎮(zhèn)有關領導組成,承擔了主要的調(diào)解工作。這么多的行政干預影響了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的功能,損害了人民調(diào)解的群眾性、自治性,妨礙了人民調(diào)解應有價值的發(fā)揮。這么一來,人民調(diào)解就可能被操控,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就可能得不到充分保護。正如有學者所言:“隨著中國調(diào)解的制度化,調(diào)解已經(jīng)越來越相似于審判了。”
(二)人民調(diào)解的“自治型”模式已不適應市場經(jīng)濟規(guī)律
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市場主體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多。為了解決這些矛盾,人們成立了行業(yè)調(diào)解組織和為社會提供有償服務的民間調(diào)解組織。這些調(diào)解組織的出現(xiàn)說明了人民調(diào)解的“自治型”模式已不適應市場經(jīng)濟規(guī)律,必須進行改革和完善。
近年來,人民調(diào)解逐步形成兩種基本模式:一是大調(diào)解模式,二是職業(yè)化模式。大調(diào)解模式主要是以人民調(diào)解為基礎,通過建立鄉(xiāng)鎮(zhèn)一級的調(diào)解中心,實現(xiàn)人民調(diào)解、司法調(diào)解和行政調(diào)解的聯(lián)動,充分發(fā)揮人民調(diào)解、司法調(diào)解和行政調(diào)解的整體效能。職業(yè)化模式,即通過政府投入,建立專業(yè)化的人民調(diào)解機構或逐步推行人民調(diào)解員職業(yè)化,為社會提供更加優(yōu)質(zhì)高效的服務。兩種模式各有自己的優(yōu)勢,也各有自己的問題。我們要促進兩種模式相互融合,相互補充。
(三)人民調(diào)解隨意性較大,適用不大普遍
人民調(diào)解組織的人員素質(zhì)、物質(zhì)條件和工作報酬等等決定了人民調(diào)解工作專業(yè)性不強,隨意性較大,糾紛解決的效果不大理想,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信就不是很高,在實際生活中適用就不大普遍。尤其是政府提出依法辦事,建立法治社會以后,人民更希望通過司法程序獲得確定的,能執(zhí)行的裁判結果,人民調(diào)解的適用就更不普遍。
(四)人民調(diào)解的成效降低
傳統(tǒng)的人民調(diào)解,由于社會經(jīng)濟不發(fā)達,社會關系不復雜,人們生活在熟人社會中,加之法制不健全,人們之間發(fā)生糾紛很大時候選擇人民調(diào)解來解決。現(xiàn)在,由于廣大人民群眾民主權利意識增強,而調(diào)解員的素質(zhì)不高,調(diào)解協(xié)議又沒有強制執(zhí)行力等諸多原因,人民調(diào)解的成效在降低。這就影響了人民調(diào)解優(yōu)勢的發(fā)揮和價值的彰顯。
四、我國現(xiàn)階段大力發(fā)展人民調(diào)解的必要性
進入21世紀后,雖然我國訴訟、仲裁工作取得巨大進步,大量民間糾紛能夠通過法院、仲裁機構有效解決,但是大力發(fā)展人民調(diào)解仍有必要。
首先,中華文明是崇尚“天人合一”的和諧狀態(tài)的,民間糾紛采取調(diào)解方式處理就是情理之中的。千百年來,民間調(diào)解越來越成熟,從理論到技巧都頗有建樹,解決了大量的民間糾紛。新中國成立后,政府高度重視民間調(diào)解,把民間調(diào)解成功轉變?yōu)槿嗣裾{(diào)解。在長期的探索中,人民調(diào)解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既有豐富的理論知識,也有切實可行的操作辦法。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今天,我們應當吸取這些寶貴經(jīng)驗,并在實踐中開拓創(chuàng)新。
其次,人民調(diào)解具有獨特的優(yōu)勢。除了運用法律,人民調(diào)解還用情和理說服當事人,重視當事人之間的友好協(xié)商,盡量減少感情上的對立,這樣解決糾紛當事人更能心服口服,糾紛也就能更徹底地解決,真正做到案結事了。人民調(diào)解還具有程序簡便,耗時短,又不收費的優(yōu)勢,因此可以減少當事人的訟累,減輕當事人的經(jīng)濟負擔,節(jié)約司法資源。
最后,我國當前的社會現(xiàn)實也決定了大力加強人民調(diào)解的必要性。當前,由于社會處于大轉型時期,民事糾紛急劇增加,而法院由于其工作的嚴肅性和專業(yè)性一時不可能大量增加法官,就出現(xiàn)了訴訟爆炸,案多人少的情況。這時,大力發(fā)展人民調(diào)解就能夠有效緩解法院的壓力,讓法院的工作能更順利、更規(guī)范地進行,也讓廣大人民群眾的糾紛能更迅速有效地解決。
五、完善人民調(diào)解制度的路徑
人民調(diào)解制度存在前述問題,可以從以下路徑完善:
(一)規(guī)范行政機關對人民調(diào)解工作的指導
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的法律性質(zhì)決定了人民調(diào)解的本質(zhì)屬性是民間性、群眾性、自治性。司法實踐中,有些地方的行政機關對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的工作介入過多,把指導變成了操控,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就被架空,人民調(diào)解就不能充分保障當事人調(diào)解的自愿性,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就可能得不到充分保護。因此,行政機關應當依法辦事,規(guī)范對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工作的指導,這樣才能維護人民調(diào)解的本性。
(二)探索市場經(jīng)濟下人民調(diào)解的新模式
傳統(tǒng)的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一般是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和企事業(yè)的單位下設的,但是,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產(chǎn)生了行業(yè)調(diào)解組織和向社會提供有償服務的民間調(diào)解組織。這些調(diào)解組織在解決相關民事糾紛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對這些組織也要改革完善,也要加強監(jiān)督管理,逐步探索出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人民調(diào)解更有效的模式。
如前所述,人民調(diào)解近年來逐步形成大調(diào)解和職業(yè)化兩種模式。對大調(diào)解模式,不要輕易改變?nèi)嗣裾{(diào)解的群眾性、自治性,避免國家權力過多地向人民調(diào)解滲透,各調(diào)解組織之間要相互配合,互補優(yōu)勢,做到不缺位、不錯位、不越位,還要建章立制,將各種調(diào)解主體的職責制度化,基本程序制度化。對于職業(yè)化模式,則要加強考核監(jiān)督,確保調(diào)解效果,確保該模式健康發(fā)展。
(三)規(guī)范人民調(diào)解
人民調(diào)解雖然具有民間性、自治性,但是也必須規(guī)范。現(xiàn)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2010年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調(diào)解法》和1989年公布的《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組織條例》分別從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guī)的層面對人民調(diào)解工作作出了規(guī)定,人民調(diào)解的相關法律已形成一個體系,人民調(diào)解就要依照這些法律進行。司法實踐中,有些地方的人民調(diào)解隨意性較大,行政機關對人民調(diào)解的干預過多,造成人民調(diào)解的威信下降,適用不大普遍。這些問題都要盡快解決。
(四)改善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
由于歷史原因,我國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調(diào)解員的素質(zhì)不夠高,調(diào)解工作的成效還不夠好,因此要大力改善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而改善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主要是提升人民調(diào)解員的素質(zhì)。因此可以經(jīng)過一系列培訓提升人民調(diào)解員的素質(zhì),也可以聘請法學研究人員,退休的法官、律師等專業(yè)人才擔任調(diào)解員。調(diào)解員的素質(zhì)上去了,很多問題就迎刃而解。
我國人民調(diào)解既有深厚的歷史基礎,也有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我們要進一步研究人民調(diào)解的發(fā)展空間,探索完善人民調(diào)解的路徑,保證人民調(diào)解更好地發(fā)揮其應有的作用,把社會和諧、國家穩(wěn)定等工作推上新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