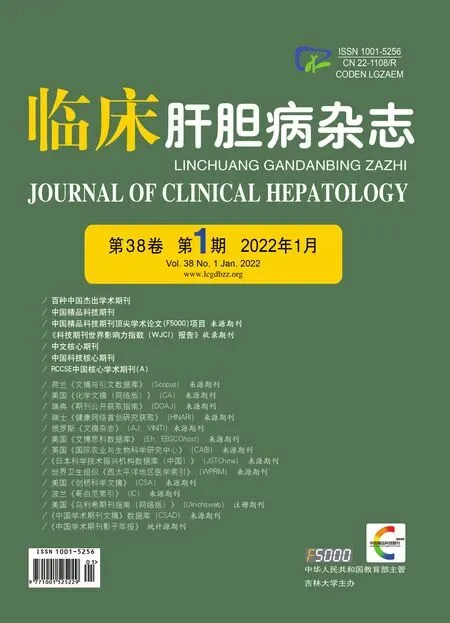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所致肝臟不良反應的研究進展
王 宇, 李釗穎, 李 爽, 劉成海
1 上海市寶山區中西醫結合醫院 消化科, 上海 201999; 2 成都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 神經內科, 成都 610000;3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曙光醫院 a.肝病二科, b.肝病研究所, 上海 201203;
腫瘤的發生與抑癌基因突變及免疫監視失能相關[1]。基因突變重新編輯后的癌細胞抗原性較弱,而且在腫瘤微環境局部存在復雜的免疫抑制或免疫逃逸,這些均是造成難以有效激發免疫反應的原因。腫瘤的免疫療法通過再次激活免疫抑制,恢復免疫系統的免疫監視功能從而達到抗腫瘤作用,但會破壞機體免疫耐受平衡,從而出現免疫相關的不良反應(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 irAE),其中免疫介導的肝炎(immune-mediated hepatitis,IMH)是重要事件之一。本文從腫瘤免疫療法作用機制及類型,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肝損傷的發生率及危險因素、損傷機制、病理模式、治療措施方面進行論述。
1 ICI抗腫瘤作用機制及類型
免疫檢查點是指位于效應T淋巴細胞上的一些激活性和抑制性受體調節開關,激活可以使得T淋巴細胞處于效應狀態,抑制可以使得T淋巴細胞處于沉默狀態。T淋巴細胞要完全激活,需要多個步驟,包括抗原特異性細胞的克隆選擇、淋巴組織中的激活和增殖,然后在靶組織中執行它們的效應功能,這些步驟中的每一個都受免疫檢查點蛋白的調節[2]。腫瘤突變負荷產生腫瘤新生抗原,腫瘤上調程序性死亡受體(programmed death-1 receptor,PD-1)等免疫檢查點的表達,從而發生免疫逃逸[3]。目前臨床上應用的ICI有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相關抗原4(cytotoxic T 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 4, CTLA-4)和PD-1及其配體(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PD-L1)的單克隆抗體。
ICI通過抑制T淋巴細胞沉默抗體,激活T淋巴細胞對腫瘤細胞的免疫應答從而發揮抗腫瘤作用。CTLA-4檢查點抑制劑抗癌作用機制一方面增強對腫瘤細胞具有殺傷效應的T淋巴細胞活性;另一方面抑制調節性T淋巴細胞活性,使輔助性T淋巴細胞(Th)或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重新識別腫瘤新生抗原。PD-1廣泛存在于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和Th上,PD-1的PD-L1和PD-L2兩種配體,除了存在于巨噬細胞、樹突狀細胞的表面,其在腫瘤細胞表面也有分布,腫瘤細胞表面的PD-L1和PD-L2配體會抑制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并上調調節性T淋巴細胞的活性從而使腫瘤細胞發生免疫逃逸。PD-1與PD-L1的抗腫瘤機制在于重啟淋巴細胞增殖以及細胞因子的產生,激活對腫瘤細胞的免疫再識別及殺傷[4]。
2 ICI的發生率及危險因素
目前依據不良事件通用術語標準(CTCAE)對肝臟免疫相關不良事件的嚴重程度分為4級:1級(ALT 或 AST>1×ULN~3×ULN),2級(ALT或AST>3×ULN~<5×ULN),3級(ALT或AST>5×ULN~<20×ULN)和4級(ALT或AST>20×ULN)[5]。ICI肝損傷主要在首次治療后2個月內出現,2%~5%的病例出現AST或ALT升高,而肝損傷中1%~4%的病例中檢出了3~4級的轉氨酶升高[6]。
CTLA-4抑制劑引起肝炎發生率小于10%,PD-1/PD-L1抑制劑發生率約5%,聯合使用2種免疫藥物(CTLA-4和PD-1/PD-L1)的患者更容易發生肝毒性[7]。使用抗PD-1、PD-L1抗體治療后,任何級別的IMH發生率為7.4%~14%,聯合治療為12.2%~37.8%[8]。具體涉及單藥品種而言,接受常規劑量伊匹單抗、納武單抗和派姆單抗單藥治療的患者肝炎發生率為5%~10%(其中3級反應1%~2%)。伊匹單抗 3 mg/kg和納武單抗 1 mg/kg聯合治療的患者肝炎發生率為25%~30%(其中3級反應15%)[9]。
在接受ICI治療的患者中,4%的患者觀察到≥3級irAE肝炎,其中女性和ICI治療史與≥3級irAE肝炎的發生率顯著相關[10]。日本一項研究[11]發現,使用ipilimumab和初始ICI給藥后24 h內出現發熱是免疫相關肝損傷的預測因素。IMH風險可能是劑量依賴型[12],且聯用ICI可增加IMH風險,當抗CTLA-4和抗PD-1藥聯用,肝損傷總體發生率28.8%,3~4級不良反應可達17%[13]。腫瘤本身也會影響其發病率,惡性黑色素瘤患者往往更容易發生IMH[14]。此外既往的自身免疫病史以及肝臟疾病如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亦是IMH的風險因素[15-16],而且人白細胞抗原也在ICI的療效和肝損傷易感性中發揮重要作用[17]。
3 ICI導致肝損傷的機制
在發生irAE的患者中一般抗腫瘤效果較好,這或表明誘導抗腫瘤免疫與自身免疫不良反應之間存在共同機制[18]。ICI導致irAE的機制為活化的T淋巴細胞攻擊正常肝組織、自身抗體的產生、CTLA-4脫靶效應導致的抗體依賴細胞介導的細胞毒性作用以及免疫細胞釋放炎性因子介導組織免疫損傷[19]。
有證據[9]表明,PD-L1/PD-1通路以及CTLA-4對肝臟環境中的免疫調節很重要,通過調節CD8+T淋巴細胞活化和凋亡有助于維持耐受性。其中,CTLA-4基因多態性與肝臟自身免疫疾病之間存在關聯,例如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和AIH。在正常的生理條件下,免疫檢查點通過抑制樹突狀細胞介導的CTLA-4 途徑的活化或通過在炎癥部位誘導T淋巴細胞衰竭PD-L1/PD-1途徑來預防自身免疫事件的發生。ICI通過靶向阻斷腫瘤免疫逃避發揮作用,但會破壞機體免疫耐受平衡,從而引起IMH,ICI所致IMH是間接藥物性肝損傷,為免疫反應增強所致。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在免疫治療相關肝炎的發病機制中起核心作用[20],其機制為細胞毒性CD8+T淋巴細胞導致腫瘤細胞的破壞,并從正常組織中釋放腫瘤抗原、新抗原和自身抗原。這被稱為表位傳播并導致免疫耐受性降低。這種效應與Th1和Th17 T淋巴細胞的激活一起導致促炎細胞因子的產生,包括IFNγ和IL-17[21]。因此,細胞毒性的CD8+T淋巴細胞的錯位攻擊以及炎癥因子的釋放可能是造成肝損傷的機制。
4 ICI導致肝損傷的臨床表現及組織學特征
RUCAM量表與結構性專家診斷程序對于ICI的診斷是支持性診斷而非排除性診斷,因此IMH的診斷更多需要排除其他造成肝損傷的混雜因素。如果患者患有基礎病毒性肝炎或AIH,則IMH的診斷則具有很大復雜性。HBV DNA陽性的患者應在ICI治療之前進行抗病毒治療。肝功能Child-Pugh A級或者B級(≤7分)、HBV DNA小于500 IU/ml并且ECOG PS評分在0~1分的晚期肝惡性腫瘤患者可以一線選擇阿替麗珠單抗聯合貝伐珠單抗進行治療[34],并且治療期間很少出現HBV DNA再激活但ICI對于晚期肝癌的療效仍有待提升[22]。對于未經治療的HCV和其他原因導致肝酶升高,應進行肝活檢進行區分[23]。
累及肝臟的irAE臨床表現相當異質,類似于自身免疫性藥物性肝損傷。肝臟irAE患者與AIH或移植物抗宿主病 (GVHD) 患者在臨床病理特征方面:血清轉氨酶水平無顯著差異,但AIH患者的血清IgG和抗核抗體水平高于GVHD 或肝臟irAE患者。肝臟 irAE患者表現為肝小葉的炎癥,而AIH 患者表現出門靜脈和小葉炎癥。免疫組化分析顯示,在肝臟irAE和GVHD患者的小葉區域中,CD8+T淋巴細胞浸潤占主導地位,并且表達叉頭框蛋白P3(FOXP3)的調節性T淋巴細胞積累有缺陷。相比之下,AIH患者的門靜脈周圍病變的特征在于CD4+T淋巴細胞、CD8+T淋巴細胞、CD20 B淋巴細胞和FOXP3調節性T淋巴細胞的浸潤[24],浸潤細胞主要由CD8+T淋巴細胞組成,并且與肝細胞壞死呈正相關[25]。臨床上,偶爾會出現右上腹部的疼痛和發熱,而影像學檢查無特征性意義[26]。
由于發病機制的復雜性,irAE相關的肝組織學表現是異質性的,包括小葉性肝炎、脂肪變性和脂肪性肝炎以及膽管損傷[27]。但組織學除了在診斷和評估肝損傷的嚴重程度外,也可區分抗PD-1/PD-L1單克隆抗體和抗CTLA-4單克隆抗體的毒性[28]。抗PD-1抗體引起的肝實質損傷主要表現為伴有輕度小葉浸潤的小葉性肝炎[28-29],但在使用抗PD-1抗體治療期間膽管損傷可能導致由淋巴細胞浸潤性膽管炎引起的膽管消失綜合征[30]。派姆單抗和阿替麗珠單抗不僅表現出小葉性肝炎,還表現出硬化性膽管炎、淋巴細胞管損傷和肉芽腫性肝炎,其原因或是PD-1與PD-L1相互作用受阻導致CD8+T淋巴細胞和巨噬細胞紊亂亢進造成[31]。在較嚴重IMH的病例中,較多CD8+的T淋巴細胞聚集在匯管區及肝竇內,且有部分肝竇內皮細胞表達PD-L1[32]。顯著的肝竇內炎癥細胞浸潤和中心靜脈損傷伴血管內皮炎癥可能有助于診斷伊匹單抗造成的肝組織學損傷[33]。CTLA-4抗體肝損傷病理特征顯示活動性全小葉肝炎,伴有肝小葉大量淋巴細胞和巨噬細胞聚集的組成的混合炎性浸潤。巨噬細胞可形成松散的“微肉芽腫”,并見分散的嗜酸性粒細胞和中性粒細胞,還可見融合性壞死灶、多灶性肝細胞凋亡和氣球樣變性[29]。
5 ICI肝損傷的治療
IMH是對肝組織過度免疫反應或免疫耐受突破所致,停止ICI的腫瘤免疫療法是治療IMH的關鍵環節。但除了停用肝損傷藥物外,由于闡述免疫發病機制的免疫基礎研究較少,導致治療選擇的困境及異質性。有經驗表明,輕-中度肝細胞損傷型和混合型藥物性肝損傷,炎癥較重者可試用雙環醇和甘草酸制劑;炎癥較輕者可試用水飛薊素。膽汁淤積型DILI可選用熊去氧膽酸。有報道腺苷蛋氨酸治療膽汁淤積型DILI有效。上述藥物的確切療效有待嚴格的前瞻性隨機對照研究加以證實[34]。目前絕大多數irAE推薦皮質類固醇作為一線用藥選擇,對于二線治療依然推薦的是較為寬泛的靶向T淋巴細胞、B淋巴細胞、細胞因子和自身抗體的藥物,但由于缺乏依據免疫組織病理學進行的分層治療選擇,而臨床應用性不高[35]。
皮質類固醇通過降低T淋巴細胞和巨噬細胞等炎癥細胞的活化、增殖、促進凋亡,來發揮免疫抑制效應。中國臨床腫瘤學會(CSCO)指南根據《常見不良事件評價標準(CTCAE) 4.03版》中AST、ALT或總膽紅素的分級對ICI相關肝臟毒性進行分級, G1指ALT/AST<3×ULN、TBil<1.5×ULN,通常可繼續使用ICI;G2(ALT/AST 3×ULN~5×ULN、TBil 1.5×ULN~3×ULN)需暫停ICI,予口服潑尼松0.5~1 mg·kg-1·d-1,1個月內逐漸減量;G3(ALT/AST 5×ULN~20×ULN、TBil 3×ULN~10×ULN)和G4(ALT/AST>20×ULN、TBil>10×ULN)需永久停藥,使用甲強龍1~2 mg·kg-1·d-1)靜注,若3 d后仍無改善則添加麥考酚酯0.5~1 g (2 次/d)或抗胸腺細胞球蛋白(ATG)等。但長期、較高劑量地使用糖皮質激素可能對治療產生負性影響且目前并沒有大規模的臨床數據證明免疫抑制劑的臨床獲益程度[36]。
通常選擇單克隆抗體英夫利昔單抗作為對皮質類固醇耐藥不良事件的補救治療,但不推薦英夫利昔單抗治療肝炎不良反應,因為英夫利昔單抗有致肝細胞毒性及肝衰竭的潛在風險[37-38]。麥考酚酯通過耗竭T淋巴細胞和B淋巴細胞中的鳥嘌呤核苷酸抑制細胞增殖,因此可以抑制免疫應答和抗體產生。有研究[39]報道,麥考酚酯可作為皮質類固醇耐藥的補救治療措施。亦可以使用能使淋巴細胞、單核細胞、自然殺傷性細胞耗竭的ATG治療皮質類固醇耐藥的肝臟不良反應。研究[40]顯示ATG應用于IMH時,外周循環淋巴細胞CD4+T淋巴細胞被ATG嚴重消耗,而CD8+T淋巴細胞、B淋巴細胞、NK細胞和單核細胞相對較少。
6 展望
ICI通過激活抗腫瘤效應細胞,從而控制腫瘤生長和預防腫瘤復發的作用。但激活ICI往往在靶向調控途徑的同時也會破壞外周免疫的穩態,從而造成一系列免疫相關性疾病。ICI造成的肝損傷是免疫新時代抗腫瘤療法中不可回避的問題。因此,隨著精準醫學的發展, ICI 對大多數癌癥的使用越來越多[42],其免疫相關肝毒性的發生率將繼續上升。但IrAE的臨床表現及影響多樣且復雜,ICI應用患者的管理往往需要在療效、毒性和特定治療之間取得平衡,并積極開展多學科協作。
利益沖突聲明: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王宇負責課題設計,資料分析,撰寫論文;李釗穎參與收集數據,修改論文;王宇負責擬定寫作思路,劉成海、李爽指導撰寫文章并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