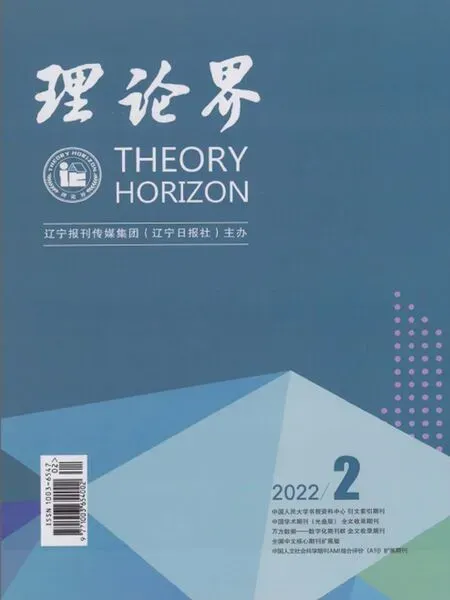從“立志”到“致良知”
——王陽明道德修養的工夫進路
邵友偉
眾所周知,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說是經過“學三變”的思想革新和“教三變”的價值轉向而得出來的。王陽明的“良知”學說,并不是書齋里的參悟,而是經過身臨絕境的軍事斗爭和持之以恒的教學實踐得出的。“良知”在王陽明的思想體系有諸多含義,如其對天理的顯現,對是非善惡的把握,作為思維主體的發用,以及良知的萬物一體之仁。“良知”的內涵非常豐富,但是最重要和流傳最廣的是“良知”的道德修養內涵。在“致良知”的工夫之前,王陽明一直把“立志”作為道德修養的首要條件和根本要領。但是,不管是立志還是致良知都是為成圣成賢的道德修養論服務的。
一、“立志”確立了成圣成賢的方向
在“致良知”的思想提出之前,王陽明一直將立志作為其為學的頭腦和修身的前提。王陽明在教學問答和與友人的書信中,將“立志”作為第一要義有其深層根源。在其求學之初,“嘗問塾師曰:‘何為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而。’先生疑曰:‘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圣賢而。’”〔1〕可見,他將立志成圣成賢作為入學門徑與自己的學問端緒和求學門徑有關。他在開始教學之初,被貶貴州龍場驛之時,就提出“立志”的入門方法。在《教條示龍場諸生》一文中,他將立志、勤學、改過、擇善作為貴州龍岡書院的教學綱領,并把“立志”作為前提和第一要義。在王陽明那里“立志”作為成圣成賢的方向,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為學之頭腦;第二,為善去惡的內容;第三,存理去欲的工夫;第四,養心的工夫。
1.立志作為為學之頭腦
“立志”這一提法最早見于《論語》,《論語》中有“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和“志于道”的提法。心學的代表人物陸九淵也曾提到過“立志”,但他未將“立志”作為為學之頭腦。在孔子那里志于學即志于道,而王陽明將“立志”作為“致良知”的階梯。王陽明之所以提出為學之頭腦,一方面,當時的讀書人將考取功名作為為學的目的,在學問方面表現出空疏支離的普遍現象,“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辨義利”;另一方面,他認為朱子的格物工夫的察之于念慮之微、求之于文字之中、驗之于事為之著、索之于講論之際四條缺乏重點,使初學者對于所要追求的目標沒有明確的概念。“若于此未有得力處,卻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語,平日所見皆非實得,不可以不猛省也!”〔1〕由此可以看出,王陽明與朱子治學路徑的差異,王陽明所說的虛語就是沒有在立志上用力,而是陷于知識的牢籠。他并不是排斥知識,而是相對于知識他更強調道德修養的重要性。“為學須有本源,須從本源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1〕從本源上用力可以明確方向,從而在德性的修養上游刃有余,避免陷入與為學無涉的事情和文字之中。
因此,他認為“為學須有個頭腦工夫,方有著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1〕為學頭腦就是能夠辨明功利之學與圣賢之學的區別。為學頭腦如同為學之路標,能夠使人不忘本心,時時拂拭自己的志向。“立志”之于為學如舵之于舟,如此,人生才會有方向。更進一步,他指出“大抵吾人為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1〕立志是切實的工夫,是做人和做學問未病先藥、未雨綢繆的關鍵。因此,“立志”是通往“良知”之學的緊要大頭腦,如果志向不明確,則容易困頓遺忘和循環往復,因此,應該時時反省所立志是否真切。
2.為善去惡的內容
王陽明認為,立志就是要不斷地在為善去惡上做工夫。“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逾矩’,只是志到熟處。”〔1〕王陽明所說的“立志”雖然是立長志而不是常立志,但是需要經常反省自己所立的志向是否存善去惡,是否剛正不阿,只有達到了“從心所欲不逾矩”,為善去惡的工夫才算完成。為善去惡并不是到外在去尋找,而是到自己的本心中去尋找。“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1〕因此,“立志”不是口頭上的立圣賢之志,而是將心中為善去惡落到實處,方是真正的立志。有了善惡的維度,立志的過程中就能夠避免支離煩瑣和誤入歧途。
“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充與遏者,天聰明也。圣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1〕立志的工夫同時也是引導的工夫,把善念加以擴充,惡念加以遏制,以此來存善去惡。這里的“天聰明”與“此”與后來的良知是一致的,只是此時他尚未提出良知學說。他所強調的善,從更高的意義上來說,是《大學》三綱領中的止于至善。他說:“故止于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1〕這里的大人之學即圣賢之學,大人之學所達到的高度即止于至善。明明德和親民都是達于至善的內容和步驟。“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1〕通過立志,立圣賢之志,與天地萬物合一,從而朝著至善之境的方向去努力。
3.立志作為存理去欲的工夫
與為善去惡相比,存理去欲的工夫更加切己也更加復雜。存理去欲的工夫不是數量的增減,而是內在的體察。當學生問立志應該存善念還是去惡時,他回答:“善念存時,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1〕他認為,為善去惡只是工夫和手段,最終目的是要與天理合一。他認為人心本來是善的,把心中的善念保持住不被沾染就自然能夠與天理合一。
為讓學生理解立志與天理的關系,他用道家“結圣胎”做比喻。“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于美大圣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1〕因此,存天理的工夫是一個長久的工夫,也是一個由量的積累到質的改變的過程。心中常念此天理自然能夠使其充實、有光輝,并且達到至善、至圣、至神之境。當天理的概念在心中生根發芽,人欲則被驅除。“圣人之所以為圣人,惟以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為圣人,亦惟在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1〕立志作為存理去欲的工夫,需要不斷驅除人欲,直至心中純是天理,而無人欲,圣賢之志方確立,存理去欲的工夫才完成。他在《示弟立志說》中對存理去欲的工夫進行了細化和分解。
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燥心生,責此志,即不燥;妒心生,責此志,即不妒;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1〕
諸如此類,這些都屬于人的欲望,從志向上去規范這些行為,則能夠達到存理去欲的目的。存理去欲即是去掉心中不合理的欲望,使心中所存之理能夠與天理合一。
4.立志是養心的工夫
養心是對為善去惡和存理去欲的概括和總結,是更根本和進一步的工夫。立志能夠使人的內心免于浮躁,立志的工夫也是格其心之不正以歸于正的工夫。“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敬坐、息思慮。”〔1〕立志并不是要全然心無旁騖,而應該先有靜心思慮的過程。“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始于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學時去夫外好。”〔1〕養心是德性修養的基礎,也是能否真正立志的關鍵。德性的培養也如同種樹一樣,需要從小培養、澆灌、呵護,避免外在的誘惑。“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葉,葉而后花實。”〔1〕立志的工夫即求得本心的工夫,如同一棵樹從芽—干—葉—果實—生生不息的生命歷程。
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于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譬之根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擁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除之者也,無非有事于根耳矣。〔1〕
立志向學即不斷地尋找本心的過程,與孟子的“求放心”相一致,良知之學即修養身心的學問。事、理、學都在人的心中,所以修“心”的工夫即為學、處事、求理的學問。修心的工夫即培養、灌溉、扶植根本的過程,也是立志的工夫。理在心中是心學一貫的宗旨和原則,與陸九淵的“心即理”的思想是一致的。心外無事就是說道德修養是為學的基礎,心外無理即道德觀念是人心所固有的,不假外求的。
綜上所述,“立志”是為學的頭腦,也是通往“良知”的必由之路。在這一為學頭腦的前提下,通過為善去惡、存理去欲和養心的工夫逐步確立圣賢的志向。立志作為其為學的根本,是學問得以開花結果的基礎,是避免學子在學習過程中消極懈怠和信馬由韁的保證。“立志”要在實事上為善去惡,在體察中回到心之本體,即天理,欲望自然消除。另外,立志成圣賢并不是對圣賢的簡單模仿,而是內心能夠知曉圣人之志。王陽明談到后世著述繁多,恐亂正學“后世著述,是又將圣人所畫,模仿謄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遠矣”。〔1〕因此,立志是自我完善、自我修養、自我體悟的工夫,而不僅是通過讀書得來的。“通過立志而確立價值目標,自我才能真正由迎合于外轉而挺立自我,而為己、克己、成己的過程亦可由此獲得內在的依歸。”〔2〕所以,他認為真正的立志是“正之于先覺,考之于古訓”的。可以說,立志是成德的階梯,是成就圣賢之學的關鍵,也是通往“良知”之學的必由之路。
二、“致良知”與道德修養的完善
在“立志”與“致良知”之間,王陽明一度把“立誠”作為其思想的核心和成圣成賢的不二法門。在正德八年與黃宗賢的書信中,他說:“仆近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吾人為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1〕在此,他是為了說明誠意的重要性以及“立誠”在道德修養中的重要性,〔3〕但是“立誠”的思想體現為“立志”思想的強化。“誠”在王陽明的思想中有很多內涵,其中最重要的價值指向是其道德修養方面。“夫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之功,則明善是也。……故誠身有道,明善也,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1〕王陽明對于“誠”的理解取自《中庸》“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可見,“誠”最重要的作用體現為道德修養內涵的修飾和加強,“誠”的目的是喚醒主體內在的自覺,所以“誠”的道德修養內涵之后被良知之學所取代。
立志與致良知不是孤立存在的,立志是致良知的階梯。因此,王陽明說“志立得時,良知千事萬為只是一事”。〔1〕立志是致良知的前提,立志為致良知提供了道德標準和心理準備。不僅如此,王陽明在晚年居越期間提出致良知后,把致良知說成是“學問大頭腦,是圣人教人第一義”。由此可見,致良知接替立志作為為學頭腦的作用,成為他的心學工夫論的內核。王陽明的良知思想所包含的道德修養內涵大致包含四個方面:第一,良知本義;第二,良知真誠不欺內涵;第三,良知與天地一體之仁;第四,“致良知”與道德實踐。
1.良知本義
良知的思想體系其實在王陽明早期思想中就已見雛形。王陽明被貶貴州龍場驛所提的“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即包含心中有天賦的道德判斷。他真正總結并把“致良知”作為思想的核心是在晚年居越講學期間。良知最早出自《孟子》,孟子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盡心上》)。孟子所說的良知良能是一種天賦的道德判斷和道德選擇,這種良知良能是基于人性善作為基礎的。王陽明在繼承孟子的良知學說的基礎上,將良知思想進行闡發,并且自成體系。他說:
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欲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1〕
在此,王陽明將孟子的天賦的道德觀念意識進一步展開,肯定了孟子所強調的孝悌的倫理道德意識。他繼承了孟子性善論的前提,將善的理念包含在良知之中。除了天賦的道德意識之外,王陽明認為“良知”是可以通過道德修養來完善的。他認為,《大學》中的格物致知的工夫是平常人通過修養,得以充塞流行,沒有私欲障礙的前提。“勝私復理”是程朱理學的修養工夫,王陽明借以解釋對良知的修正,由此也可以看出良知對于常人來說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過道德修養來完善和回歸的。在《大學問》中他對致知與良知的關系進一步闡發:
“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謂充擴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于他人者也。〔1〕
《大學問》作于王陽明晚年,是王陽明出征思田之時對弟子的教導,由弟子錢德洪輯錄。《大學問》是在其解釋“致良知”的思想體系之后,其學問“所操益熟,所得益化”后的提升和總結。他解釋“致知”即“致良知”,在這里“知”即良知良能,不是朱子所說的知識性的“知”。“良知”的道德修養工夫也不是通過格物致知來實現,而是在心之本體上下工夫。因為良知本體有區分善惡的能力,所以,道德的修養的完善是自然而然得以提升的。
2.良知對是非善惡的判斷
為善去惡的工夫是王陽明一直強調的、不同于知識積累的道德修養的方法。由上文立志的工夫可知,立善念、存善去惡還是止于至善,都是首先強調道德意義上的完善。在立志說之后,王陽明多次提到為善去惡的工夫。他說:“為學工夫有深淺,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為善去惡?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1〕雖然其學問頭腦有變化,思想體系不斷完善,但是將為善去惡作為道德修養的內核是不變的。良知作為人天生所具有的稟性,具有判斷是非善惡的能力。“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1〕王陽明認為,良知是一種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而認識是非善惡正是道德修養的關鍵。知善知惡是一種生活智慧,好善惡惡則是一種道德選擇,并且能夠體現人的道德修養。他對良知的發散已經遠遠超出人的天然的應對能力,在他那里體現為強大的認識能力和變通方法。
除了善惡的指向以外,良知還具有對是非的理性判斷能力。
夫良知之于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于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厘千里之謬,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1〕
良知不同于規矩或準則,規矩或準則是有規定性的,但是良知是以不變應萬變的。在王陽明那里知道良知的內涵,則能見微知著、未雨綢繆,也足以看出良知是一種智慧,而不是通過學習知識認識規則。“良知即是易,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圣人。”〔1〕良知的隨機應變體現為易道變動不居的思想,這種變動不居已經不僅拘泥于是非善惡的判斷,而是體現為一種權變和恒常性。熟稔良知之學不僅表現為對是非判斷的準確,而是使人成為一個懂得是非的人。
良知之學與立志的區別在于,良知之學是立志工夫的深入,可以達到“隨心所欲不逾矩”。良知的是非判斷能力不會因人而異,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1〕因此,良知不是理性的技巧,它是個人修養和體悟使然。由良知之學對天下古今的囊括,我們可以看出其學問的超脫和圣賢氣象。
3.良知與天地一體之仁
良知不僅可以作為處理是非善惡的準則,還存在于人與外物的交互作用中。“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為草木瓦石矣。豈為草木瓦石為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為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是一體。故五谷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為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1〕
按照良知是“理”存在于人的心中來看,世間萬事萬物的理都存在于人的心中。凡是與人相關的事物都有良知存在,使自然界萬事萬物能夠成為本來的樣子。正是有了人的靈明,人與萬物交互作用,世界才能繁榮。人包含在宇宙的系統之中,因此人的良知體現為宇宙之理的分殊,良知即人的核心。與朱熹的“格物”思想所不同的是,朱熹認為一草一木乃至日月星辰自然有其存在的道理,與人的存在是無關的,但王陽明認為人的良知即天地的良知,自然萬物的運行以人的良知為轉移。
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個靈明,人只為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它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它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辨它吉兇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卻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1〕
更加深入一點,我們可以看出王陽明的良知所呈現的舍我其誰的博大胸襟。人心的靈明即天地萬物的主宰,能夠主宰超自然和超經驗的事物。由風雨雷電和山川土石再到天地鬼神,良知由自然界的法則變為更恒久的、更神秘的精神力量。
良知思想既是王陽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立身行道和實現治國平天下的精神財富。他認為良知之學不僅是個人道德修養的基礎,同樣是治國平天下的方法。
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1〕
在這里“良知”的內涵相當于孔子的“仁”,把良知的理念推廣到齊家、治國乃至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良知的內涵由個體修身拓展到宇宙的運行法則。王陽明繼承了從先秦諸子之學到宋明道學家的擔當意識與救世情懷。從宇宙的運行法則來看,他把良知看作天道在人心的顯現。從理想的道德人格到理想的道德社會需要人人都能致良知,也需要有天下一家,四海蘊于心中的胸懷。
4.致良知與道德修養的完成
致良知就是將良知的思想進行道德實踐。“天理在人心,亙古亙今,無有始終。天理即是良知,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1〕王陽明認為,良知即是天理在人心的顯現,良知作為道德修養的內容不僅要獲得,最終目的是落實到道德實踐上。“王陽明致良知的致字有推致和擴充至極二義。”〔4〕就良知的推致義而言,就是使良知能夠自然而然地呈現而不受障礙。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上文談到常人與圣人的差別在于,常人的良知被遮蔽,致良知即疏導、推致良知使其充塞流行。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他認為知行不可分離。王陽明認為知與行本來是一回事,“知”是知良知在自己的心中,行是將心中的良知進行推致,致良知是其知行合一思想的最理想狀態。致良知就是將良知本體進行推致,在處世應物中自然而言地體現良知內涵,做到知行合一。
就良知的擴充義來看:
“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謂充擴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故致知必在格物。物者,事也,凡意念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于正者,為善之謂也。〔1〕
致良知并不是擴充知識性的內容,而是擴充良知的內涵。在格物和處事的過程中,良知的含義得到豐富和擴充。把明白是非、為善去惡之心用在做事和與外物的接觸中。良知通過格物和意誠的方式,使本心得到完善。“這樣的致良知,是動機與效果的統一,合目的與合律則的統一。”〔4〕如此,也就避免了“知”與“行”的分離,道德認知與道德實踐的分離。
如此,良知思想由內在到外在,由人心到自然再推致到宇宙。良知雖然是道德性而非知識性的,但是良知需要不斷在事上磨煉,使其逐漸充塞流行,從而與天理合一。致良知思想標志著個體在修身過程中,道德修養的逐步完善,標志著良知的顯現和致思方法的運用。
三、結語
理想的人格背后一定有道德理想主義的方法論做指引,孔子、孟子如此,王陽明亦如是。因其思想將道德較知識放在更高的地位,所以在教學實踐中把德性修養放在優先地位。從知識體系來看,致良知是其思想的核心,立志是學問入手的頭腦;從道德修養來看,立志是道德修養的根基和開始,致良知是道德修養的枝葉和完成。立志作為其為學之頭腦,既可以盈科而后進,又可以時時勉勵,不忘初衷;立志作為為善去惡的內容,在心中除惡存善,不至于誤入歧途;立志作為存理去欲的工夫,需要不斷驅除人欲,使所立志向符合天理;立志作為養心的工夫體則現在驅除人欲,回歸本心。
“立志”作為“致良知”的基礎和開始體現為立志使個體具有了向學、向善、存理、去欲之心。在立志的基礎之上,天賦的道德觀念自然以良知的形式呈現,良知的是非善惡的判斷能力也突破了規定性的限制,良知的內涵也由個體修養上升到宇宙的運行法則。“致良知”對良知的推致和擴充意味著王陽明修身方法的完善,以及個體修養的趨于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