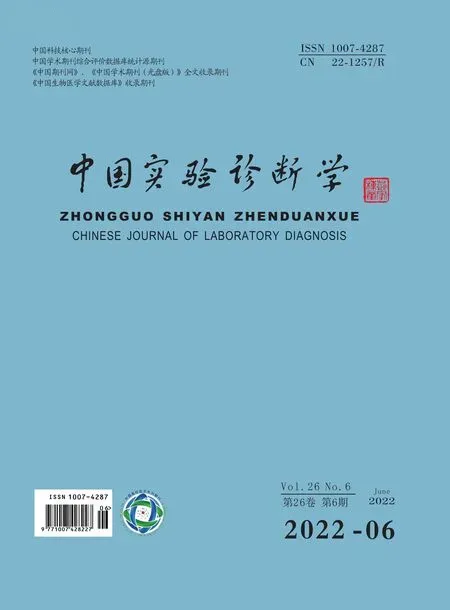慢性腎臟病微炎癥狀態與腸道菌群失調的研究進展
龔麗蘇,劉 鋒,尹 敏,俞元植
(吉林大學中日聯誼醫院 腎病內科,吉林 長春 130033)
慢性腎臟病(CKD)是由于各種原因導致的腎臟結構、功能異常,是威脅人類健康的全球性疾病。2012年我國成年人群中CKD患病率約為10.8%[1]。2019年Lv等[2]調查顯示全球CKD的患病率約為13.4%,且逐年上升。眾多研究表明,CKD患者普遍存在微炎癥狀態。微炎癥狀態與CKD患者心血管事件、貧血、營養不良、感染等并發癥的發生密切相關,是預測預后的可靠指標[3]。2011年Mejiers等[4]人提出了“腸-腎軸”學說,該學說認為腸道菌群失調、全身微炎癥反應及腎小球濾過率(eGFR)下降之間有著密切關系。本文就CKD微炎癥狀態與腸道菌群失調的研究進展作一綜述。
1 慢性腎臟病微炎癥狀態
20世紀90年代末,炎癥在CKD發病和進展中的作用引起了人們的重視,從而形成了“微炎癥狀態”學說。微炎癥狀態是指機體呈現的一種慢性持續性炎癥狀態,主要特征是全身循環中的炎性細胞因子升高,而機體無明顯感染癥狀[4]。微炎癥狀態是一種免疫炎癥反應,在CKD基礎上由多種因素、多種因子共同參與,目前考慮與患者炎性細胞因子清除降低、代謝性酸中毒、容量超負荷、維生素D缺乏、氧化應激、透析器膜的生物不相容性、胰島素抵抗、腸道菌群失調、高鈣、低磷、靜脈補充鐵劑等有關[5]。長期大劑量的靜脈補鐵可促進活性氧(ROS)形成,導致體內白介素6(IL-6)及C反應蛋白(CRP)濃度增高,同時鐵調素的表達增加致使鐵吸收和利用障礙[6]。目前微炎癥狀態的診斷主要依靠檢測血液循環中的炎性標志物,傳統生物標志物包括CRP、超敏C反應蛋白(hs-CRP)、IL-6、白介素1(IL-1)、腫瘤壞死因子α(TNF-a)等[7]。王雅琦等[8]的研究表明血清淀粉樣蛋白A水平與腎功能損害程度有關,且與CRP呈正相關,該指標或許能更早反映體內微炎癥狀態。另有研究認為外周血中性粒淋巴細胞比值、血小板淋巴細胞比值也可能反映CKD患者的微炎癥狀態[9]。
2 慢性腎臟病與腸道菌群失調
健康人腸道中細菌種類繁多,梭菌、疣微菌、厚壁菌、放線菌、擬桿菌、變形菌是人體主要的腸道菌群,其中以擬桿菌和厚壁菌數量最多,占腸道細菌的90%以上[10]。生理情況下,人體腸道細菌的菌屬和數量處于動態平衡,維持著腸黏膜屏障的完整性,此外在營養、藥物代謝及免疫調節等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11]。
CKD患者由于腸道排空時間延長、腸道黏膜屏障受損、腸道pH值上升、抗生素的使用、鐵劑的應用、膳食攝入減少等原因,導致腸道菌群的數量、結構、分布等發生變化[12-13]。Wong等[14]研究發現,終末期腎臟病(ESRD)患者無論是否進行血液透析,腸道中產生吲哚酶、對甲酚形成酶及尿酸酶的細菌濃度均升高,而短鏈脂肪酸(SCFAs)生成細菌,如長雙歧桿菌和嗜酸乳桿菌濃度明顯降低[15]。此外,ERSD患者十二指腸及空腸中厭氧菌和需氧微生物的總數較健康人群明顯增加。腸道細菌可能通過受損的黏膜屏障進入血液循環。Shi等[16-17]在ESRD患者血液樣本中檢測到克雷伯氏菌屬、假單胞菌屬、變形桿菌屬、腸桿菌屬和埃希氏桿菌屬的DNA,其中大部分細菌也分布在ESRD患者的腸道中。
3 慢性腎臟病患者微炎癥狀態與腸道菌群失調
CKD患者無論是否進行血液透析,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微炎癥狀態。多項研究表明,腸道菌群及其代謝產物通過不同的方式共同促進機體微炎癥狀態。
3.1 腸源性尿毒癥毒素生成增多
CKD患者胃腸道功能受損,未消化吸收的蛋白質在腸道遠端停留時間過長,導致蛋白水解類細菌增多,腸源性尿毒癥毒素如氨、酚、胺、吲哚和硫醇的生成增多,直接或間接誘導腎臟微炎癥狀態或全身炎癥反應[18]。目前認為其中5種腸源性尿毒癥毒素與心血管疾病和慢性腎臟病死亡率以及其他終末器官毒性有關:硫酸對甲酚(PCS)、硫酸吲哚酚(IS)、氧化三甲胺(TMAO)、苯乙酰谷氨酰胺和吲哚-3乙酸[19]。PCS和IS進入血液循環后大部分與血漿蛋白結合,故血液透析難以將其清除。研究表明,PCS和IS可誘導腎小管上皮細胞、腎小球系膜細胞產生ROS,ROS激活核因子κB(NK-κB)、p53 等調節因子后上調趨化因子的表達,引起腎間質單核細胞、巨噬細胞浸潤。PCS和IS可促進近端小管細胞發生上皮-間質轉分化、激活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RAAS),同時上調轉化生長因子-β、IL-6等炎性因子表達,導致腎臟纖維化[20]。PCS可抑制近端小管上皮細胞表面腫瘤壞死因子樣弱凋亡誘導因子(TWEAK)受體Fn14的表達,誘導細胞內炎性反應,加劇腎小管上皮細胞凋亡。此外PCS還可促進內皮細胞釋放內皮微粒,介導白細胞黏附,導致血管內皮細胞炎性反應的發生[21]。IS通過激活芳香烴受體(AhR),使促炎蛋白、血栓前蛋白過表達,進而對腎小球及足細胞造成損傷。有研究發現小鼠暴露于IS環境8周后腎臟基底膜出現嚴重病變[22]。AhR途徑的激活也影響著CKD患者鐵調素的功能,這可能是腎性貧血發生的重要原因。Klotho基因為腎臟保護基因,可編碼生成延緩腎臟纖維化進展的跨膜蛋白,IS和PCS均可抑制HK-2細胞該基因的表達[22]。TMAO是一種可通過透析有效清除的毒素,研究發現CKD患者血漿TMAO濃度與機體炎性標志物水平及腎衰竭進程成正比,TMAO可作為評估CKD進展的標志物[23]。在中重度CKD患者中,TMAO水平與IL-6成正比,是心血管事件死亡率的獨立預測因子[24]。Tang等[25]用高TMAO、高膽堿飲食喂養小鼠,發現小鼠腎臟損傷分子-1(KM-1)、NADPH氧化酶-4和促炎細胞因子的表達顯著增加,且小鼠體內TMAO升高與腎間質Smads(腎臟纖維化的關鍵調節劑)的磷酸化、腎小管間質纖維化及膠原沉積成正比。研究表明,腸源性尿毒癥毒素的排出一定程度上可減輕微炎癥狀態。AST-120是一種碳吸附劑,喂養CKD小鼠后發現腸源性尿毒癥毒素濃度降低,腸內環境改變,小鼠體內內毒素水平及炎癥水平明顯降低[26]。
3.2 細菌和細菌成分的移位
血液透析時血液動力學不穩定導致腸道缺血缺氧,腸道黏膜屏障被破壞,此外CKD患者腸道分泌型IgA水平的降低也加劇了這種破壞,兩者共同引起腸道細菌及細菌成分的移位。Shi等[17]對52名ESRD患者血液進行細菌16S rDNA擴增和焦磷酸測序,發現有12名患者的血液中存在細菌,血液細菌DNA濃度與CRP、IL-6以及腸道通透性標志物D-乳酸水平呈正相關。動物實驗發現,CKD大鼠的腸系膜淋巴結、肝臟、脾臟和血液中可檢測到結腸細菌DNA[21]。CKD患者血液循環中內毒素水平與CKD進展相關,在接受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的患者中最高,并在沒有明顯感染的情況下與全身炎癥的嚴重程度相關[27-28]。LPS是一種內毒素,機體細胞識別血液循環中的LPS后,釋放大量IL-6、IL-12、TNF-a 等炎癥因子,炎癥因子又損傷機體腸道粘膜屏障,形成惡性循環。
3.3 短鏈脂肪酸生成減少
CKD患者腸道中菌群改變導致體內短鏈脂肪酸(SCFAs)生成減少。SCFAs是腸道細菌酵解未消化膳食纖維、蛋白及肽的產物,其中乙酸、丙酸和丁酸約占SCFAs的95%。SCFAs為結腸細胞的主要能量物質,可刺激結腸上皮細胞增殖。SCFAs可抑制NF-κB通路及MAPK通路,抑制機體炎癥及氧化應激,延緩CKD的進展[29]。SCFAs可調節腎小管細胞自噬。SCFAs通過增加腎小管上皮細胞自噬相關基因-7(ATG-7)的表達,激活細胞自噬而實現腎臟保護[30]。此外,SCFAs還可通過調控T細胞的分化和功能,影響T細胞對腎臟及機體的作用,CKD患者腸道中產生SCFAs的細菌減少。Jiang[31]等對CKD1期至CKD5期患者腸道菌群進行了研究,發現丁酸鹽產生細菌的豐度逐漸下降,主要包括細菌Roseb uria spp.和F.prausnitzii,而血液循環中CRP濃度逐漸升高。王浦等[32]發現CKD患者腸道中羅氏菌屬、普拉梭菌較健康對照組顯著較少,糞便中的SCFAs明顯下降。服用產生 SCFAs的益生菌一定程度上可改善腸上皮緊密連接,減少腸道黏膜的損傷,改善內毒素血癥,抑制炎癥反應。Marzocco等[33]給予血液透析患者丙酸鈉后,測得血漿中CRP、IL-6、IL-2及TNF-a濃度下降,而抗炎因子IL-10濃度上升。
4 小結
CKD患者微炎癥狀態隨著病情的進展而加重,嚴重影響著患者的預后。目前CKD患者微炎癥狀態與腸道菌群紊亂相互作用機制尚不十分明確,但已有眾多研究表明腸道菌群失調在其中起到一定作用。通過飲食療法、益生菌、益生元、吸附劑、糞便移植等一定程度上可改善腸道菌群失調導致的全身微炎癥狀態,可能延緩CKD的進程[34]。因此研究CKD患者微炎癥狀態與腸道菌群失調的關系,從而尋求可能的治療方法,對于干預炎癥及改善預后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