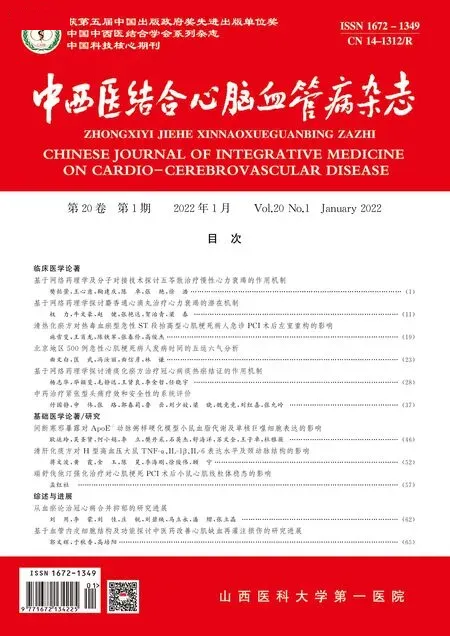缺血性腦卒中側支循環影響因素的研究進展
王燕楠,郭興華
腦卒中是導致全球高死亡率和致殘率的主要原因[1]。缺血性腦卒中病人的腦側支循環與病人最終梗死體積及臨床預后密切相關。已有很多指南將側支循環作為缺血性腦卒中的潛在治療靶點,對側支循環形成與發展的影響因素進行了許多研究。顱內側支循環根據解剖結構可以分為三級:初級側支循環,即Willis環;二級側支循環主要包括大腦前動脈、大腦中動脈(MCA)、大腦后動脈遠端之間及大腦后動脈和小腦上動脈之間的顱內軟腦膜吻合,以及頸外動脈分支和頸內動脈分支之間的吻合;三級側支循環指新生血管,一般在腦組織缺血數天后才能形成。目前用于評估側支循環的影像學方法有多種,包括經顱多普勒超聲(TCD)、CT血管成像(CTA)、磁共振血管成像(MRA)、數字減影血管造影(DSA)等,各種評估方法各有優缺點,DSA仍是評估側支循環的“金標準”,但由于其創傷性操作、注射壓力的影響、設備使用的限制等,目前臨床上更常用的評估方法為CTA。常規單時相CTA(sCTA)及多時相CTA(mCTA)評估側支循環的準確性略差。而4D-CTA,是一種從CT灌注源圖像中導出的能夠顯示軟腦膜動脈充盈的高時間分辨圖像的技術,能同時提供全腦灌注圖像及血管的動態造影信息,可以綜合評價血管狀態及腦血流動力學特點,達到類似DSA的效果[2]。
1 側支循環影響因素
缺血性腦卒中側支循環的形成和發展與遺傳因素、細胞因子、炎癥反應、基礎疾病等多種因素相關。
1.1 遺傳因素 對不同品系小鼠的研究發現,特定品系個體大腦和外周組織中天然側支循環的豐富度差異很大,Zhang等[3]的研究結果表明,MCA阻塞后新側支循環形成僅限于具有不良至中等天然側支的小鼠,缺氧會增加小鼠低氧誘導因子2α(HIF2α)、血管內皮生長因子A(VEGFA)、Rabep2、Tie2和Cxcr4的表達,在缺乏Rabep2的小鼠中,新側支形成被消除,永久性MCA閉塞可誘導Rabep2依賴性新側支形成。Kao等[4]用磁共振成像技術及組織學比較兩種具有不同Dce1等位基因但在其他方面具有相同遺傳背景的同源小鼠品系,結果發現,盡管永久性MCA閉塞1 h后各品系灌注不足的體積相似,但側支豐富小鼠的梗死灶體積減小了三分之一,灌注得到改善,梗死面積更小。
1.2 基因調控 缺血性腦卒中,基因調控異常被認為是側支循環建立的主要分子機制。長鏈非編碼RNA(LncRNAs)在缺血腦卒中中的異常表達與內皮細胞的多種生物學功能相關,在缺血性腦卒中的血管生成中發揮重要作用。趙楊等[5]研究發現,老年急性缺血性卒中(AIS)病人血漿LncRNA X染色體失活特異轉錄本基因表達明顯升高,可能有助于建立腦內側支循環。LncRNA可通過影響mRNA穩定性和表觀遺傳修飾來調控缺血性腦卒中基因表達[6],LncRNA可作為一種競爭性內源性RNA使miRNA與靶mRNA的結合被抑制或減少,從而影響缺氧的血管生成[7]。諸多學者進一步研究了miRNA對于側支循環的影響。Sun等[8]研究表明,miR-15a/16-1通過抑制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2(FGF2)及其受體的表達,通過直接結合其mRNA中3個主要非翻譯區(3′- UTR)的互補序列,抑制腦卒中后腦血管生成,在其缺失后,腦卒中后的腦血管生成增強。miR-384-5p通過Delta樣配體4(DLL4)介導的Notch信號通路促進內皮祖細胞增殖和血管形成[9]。唐蕾等[10]研究結果顯示,血清miR-199a相對表達量與側支循環美國介入和治療神經放射學學會(ASITN)/介入放射學學會(SIR)分級呈負相關,說明miR-199a表達下調可能影響側支循環形成,且miR-199a與VEGF呈正相關,提示miR-199a表達缺失可能通過下調VEGF導致側支循環形成障礙。Hao等[11]研究認為miR-126可能通過增加VEGF和降低Spred-1及PIK3R2表達促進側支循環的形成。
1.3 細胞因子 側支循環血管的形成受多種細胞因子的調控。缺氧誘導因子(HIF)是調節缺氧反應基因的重要轉錄因子,半暗帶中的HIF激活可促進血管生成[12]。血小板生長因子(PGF)是VEGF家族的一員,研究表明,較高的PGF濃度與良好的側支循環狀態相關[13]。基質金屬蛋白酶(MMP)是一種炎癥介質,當機體處于炎癥、缺氧、氧化應激等狀態時,MMP被激活。Mechtouff等[14]研究發現,低MMP-9和高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MCP-1)水平與良好的預處理側支狀態相關。存在于血管系統中且已被證實在幾種癌癥模型中促進血管生成的半乳糖凝集素-1(Gal-1)可改善腦缺血的恢復,Cheng等[15]探討了血管重塑是否有助于這種改善作用,結果表明,Gal-1治療可改善缺血皮質的循環和血管重塑;MMP-9、VEGF和VEGF受體的表達因Gal-1過度表達而上調。有研究分析了大血管閉塞所致急性缺血性腦卒中病人的血漿蛋白質組學特征,并確定與側支循環狀態相關的潛在標志物,發現胰島素樣生長因子2(IGF2)、淋巴管內皮透明質酸受體1(LYVE1)、凝血酶反應蛋白1(THBS1)與側支循環狀態密切相關,IGF2和LYVE1水平升高、THBS1水平降低與側支循環改善相關[16]。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是一類能調節細胞生長、分化的細胞因子,王利軍等[17]研究顯示,急性腦梗死病人側支循環開放組血清TGF-β1水平較側支循環未開放組高,TGF-β1具有促進血管新生的作用。多項研究探討了鞘氨醇-1-磷酸(S1P)及鞘氨醇-1-磷酸受體1(S1P1)與側支循環的關系。研究顯示,與側支循環不良病人相比,側支循環良好病人的血漿S1P相對水平較高[18];S1P1激活促進小鼠軟腦膜側支發育并改善腦卒中預后,S1P1選擇性激動劑通過內皮型一氧化氮合酶磷酸化促進軟腦膜側支循環及缺血后血管生成[19]。
1.4 信號通路 除了上述多種細胞因子外,有多條信號通路對腦側支循環進行調控。Yu等[18]推測SphK1-S1P-S1PR信號軸可能在側支循環中起重要的保護作用,但其具體機制有待進一步研究。Sun等[8]研究證實內皮細胞中miR-15a/16-1簇的基因缺失可通過酪氨酸(Src)信號通路促進缺血性腦卒中后腦血管新生和神經功能恢復。血管生成素1(Ang-1)與急性缺血性腦卒中病人側支循環形成有關的機制可能也是先激活酪氨酸激酶受體,然后激活絲氨酸激酶,最后誘導其下游信號通路來促進血管的重建[20]。15-脂氧合酶1/15-羥基二十碳四烯酸(15-LOX1/15-HETE)軸在缺血性腦卒中后血管生成和神經功能恢復中亦具有重要作用[21]。Huang等[22]研究表明,可通過基質細胞衍生因子-1a/半胱氨酸-X-半胱氨酸趨化因子受體4(SDF-1a/CXCR4)軸增強內源性神經發生和血管生成來解釋血漿SDF-1a水平和循環CD34+CXCR4+細胞與腦卒中嚴重程度和90 d 改良Rankin量表(MRS)評分相關。Zhou等[23]研究表明,抑制缺血半暗帶中的信號素3E及其受體PlexinD1(Sema3E/PlexinD1)信號,增加內皮血管生成能力和周細胞募集,有助于保護老年大鼠功能性新生血管和血腦屏障的完整性。上述部分信號通路之間有所交叉,通路之間是否有相互作用尚不確定,亦需進一步研究。
1.5 后天因素 多項研究表明,年齡、高血壓、糖尿病、高同型半胱氨酸、吸煙史、代謝綜合征等因素會對缺血性腦卒中病人側支循環的形成產生影響[24-27]。血壓升高,會損傷內皮細胞,造成脂質沉積,繼而動脈管壁狹窄,彈性下降,不利于顱內血管側支循環的建立[24]。廖照亮等[25]研究發現,高血壓與側支形成呈正相關,其主要原因可能是血壓升高促進體內內皮素的分泌,從而促進側支循環的開放。Hong等[26]研究結果也得出相似結論。但另一項研究數據顯示,慢性高血壓對急性大血管閉塞的急性軟腦膜側支循環有不利影響[27]。同型半胱氨酸代謝過程中,過氧化物及氧自由基增多,破壞內皮細胞的正常形態及結構功能,因此,高同型半胱氨酸不利于側支循環的代償[24-25]。
1.6 臨床因素 臨床工作及研究中通過藥物或非藥物手段改善病人側支循環以改善臨床預后。靜脈溶栓及機械血栓切除術在改善缺血性腦卒中病人側支循環中應用越來越廣泛,但靜脈溶栓時間窗較窄,再通率較低,且有禁忌證,機械取栓在設備及技術方面要求高,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應用。
藥物治療是改善側支循環的一種重要方法。激肽原酶類的藥物,如丁苯酞是目前得到循證醫學證據支持的藥物,在臨床上得到廣泛應用。Zhou等[28]研究證明了DI-3-N-丁基苯肽(NBP)治療通過上調缺血腦內星形膠質細胞音猥因子(SHH)的表達來改善血管生成。SHH進一步促進血管生長因子VEGF和血管生成素-1的表達。除此之外,他汀類藥物通過促進動脈生成,增強內皮型一氧化氮合酶介導的血管舒張的潛力而改善側支循環[29]。另有研究表明,急性缺血性腦卒中病人腦卒中前口服華法林與軟腦膜側支循環不良呈負相關[30]。還有擴容藥、升壓藥等可增加腦血流量,但具體藥理機制尚未明確。
此外,其他一些非藥物干預措施,如顱內外動脈搭橋術、頭向下傾斜(HDT)、體外反搏、遠程缺血調節、吸入一氧化氮、輸注白蛋白、蝶腭神經節刺激等,部分措施效果不盡如人意,部分尚在動物實驗階段或缺乏可靠的臨床證據。因此,在側支循環的臨床影響因素這一領域仍需更多的研究。
2 總結與展望
隨著影像技術的發展,對于側支循環結構及血流動力學等的準確評估已成為可能,也讓越來越多的臨床醫生意識到側支循環對缺血性腦卒中病人的重要性,因此,對于側支循環的影響因素做了諸多研究,但尚未找到一個具有高度敏感性與特異性的因素來反映側支循環的形成與發展,臨床上也尚無特定的干預手段增強側支循環,未來仍需在這些方面進行更多的實驗研究及臨床實踐。影像評估方面,4D-CTA可以為側支循環影響因素及臨床干預療效的驗證提供幫助,但其仍有一定缺點,目前已有研究將其與人工智能相結合,期待在此方面有所突破,可以為病人及臨床研究提供更為精確的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