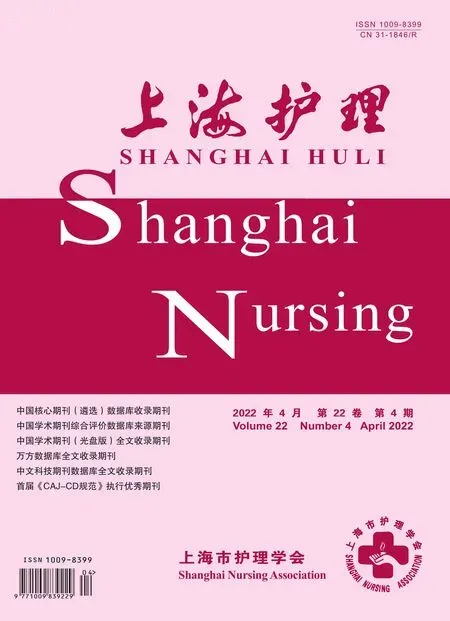撲克牌心愿卡在1例癌癥患者生命末期需求家庭溝通中的應用
石柳清,黃燕華,王惠芬
(湖北省腫瘤醫院,湖北 武漢 430060)
面對嚴重且威脅生命疾病(如無法治愈的惡性腫瘤)的患者,都應該進行生命末期話題的討論[1]。但無論是患者、其家庭成員還是醫療服務提供者,通常很難開啟有關生命末期的話題[1-3]。在中華傳統文化背景下,大多數家庭成員和醫護人員認為避免談論死亡是保護患者的感受,致使患者很少有機會表達自己的生命末期需求[4]。有學者將撲克牌心愿卡應用于肺癌患者生命末期意愿調查,并證實其有助于開啟生命末期相關話題[5-6],但該研究缺少患者家庭成員的參與。在我國,癌癥患者通常會允許其家庭成員作為代理人為其做出醫療決策[7]。但癌癥除了會對患者造成影響外,對其家庭同樣有著不可忽視的困擾[8]。長期的照護負擔可引發腫瘤患者照顧者的生活質量下降、心理壓力增大及哀傷等一系列問題。有學者提出,在實施治療或照護決策過程中,不應將患者和其家庭分割開,而應將其視為一個整體[9]。為探索患者-家庭一體化的生命末期需求溝通方式,踐行安寧療護的全家照護理念,我科將撲克牌心愿卡應用于1 例肺癌患者生命末期需求的家庭溝通中,取得了良好效果,現報道如下。
1 臨床資料
患者,男性,60 歲,已婚,漢族,乙狀結腸癌Ⅳ期,2014年行乙狀結腸癌根治術,2016年腫瘤復發并發生肺部轉移。本次于2021年1月5 日入院,診斷為乙狀結腸癌Ⅳ期伴遠處轉移,嚴重肺部感染、重度營養不良,輕度腹脹、呼吸困難,體力狀態評分為3 分。患者本人對疾病知情,參與疾病決策的主要家庭成員為其配偶及女兒,其中女兒作為醫療決策代理人。根據患者女兒的描述,其家庭內部溝通內容主要集中于檢查指標、藥物不良反應、飲食等,她本人比較關心治療效果和疾病進展等,不想患者及家庭成員留有遺憾,遂向護士求助。為了促進患者及其家庭成員有效溝通,提升其生命末期質量,我們在與患者及其女兒分別協商后決定采用撲克牌心愿卡輔助患者家庭溝通。
2 患者生命末期需求家庭溝通的實施
2.1 撲克牌心愿卡簡介撲克牌心愿卡又稱安心卡,由美華慈心關懷聯盟(Chinese American Coalition for Compassionate Care)開發。該套卡片將愿望表達與撲克牌相結合,是用來識別生命末期患者需求、價值觀和偏好的一種溝通工具[10]。1 副撲克牌心愿卡共54 張,含黑桃、紅桃、梅花、方片4 個花色,每種花色13 張,另有2 張特別心愿卡。不同花色代表不同維度的需求或愿望:黑桃代表軀體需求,紅桃代表心靈需求,梅花代表人際關系需求,方片代表物質/環境需求。每張撲克牌面的中央位置有漢字呈現具體內容。
2.2 實施前準備①征得患者及家屬同意。研究者向患者代理人展示撲克牌心愿卡,介紹家庭溝通實踐的主題、流程和目的,并征得其同意。由代理人召集參與成員并確定溝通時間。最終確定參與者為患者本人、其配偶及女兒。②人員培訓。實施家庭溝通實踐的人員(引導員)均為腫瘤相關科室的臨床護士,經過湖北省護理質控中心安寧療護師資培訓及美華慈心關懷聯盟安心卡引導員培訓并取得相應證書,熟悉安心卡的內容,具備安寧療護基礎知識及引導溝通能力。③環境及物品準備。由于生命末期話題可能涉及個人隱私,溝通地點選擇在科室的醫患溝通室,以避免他人或外界干擾。另,準備3 副撲克牌心愿卡、“待辦事項表”1份、空白紙及筆各3份,以及飲用水、紙巾若干。
2.3 實施步驟①向參與者說明活動原則。實施過程以患者為核心,傾聽時需專注耐心、不隨意打斷和批評他人觀點,患者有權隨時終止討論。②卡片發放與選取。向每名參與者發放1 副撲克牌心愿卡,每種花色分類擺放,指導其閱讀每張卡片的內容。首先由患者從每個花色中選擇3 張認為符合本人意愿的卡片,若某一花色的卡片選擇不足3 張則可再次從其他花色中補充或使用特別心愿卡,合計選出12 張撲克卡;選擇結果暫不公布,并將未選的剩余卡片放在一旁。之后,其他參與者按照相同規則,從自己的卡片中選擇12 張其認為患者會選擇的卡片。最后比對各方選擇的卡,將相同的卡片放在一旁,不同的卡片則留在各自手中。③參與者進行討論。家屬依次解釋為什么會選擇患者未選擇的卡,然后患者解釋為什么沒有選擇家屬手中的卡,并且相互討論,直至所有卡片討論完畢。④患者檢視自己最初挑選的12 張卡片以及家屬的選擇,然后確定12 張卡片作為“待辦事項”,并記錄在表格中。⑤參與各方以問題形式反饋活動感受,包括“最大的收獲是什么?”“有哪些不足和建議?”等。
2.4 溝通結果本案例所有參與者均全程參與溝通活動,其間均未使用特別心愿卡。三方選擇結果比較(見表1),差異頻次最高的是人際關系維度;且患者在重新審視后確定的待辦事項(見表2)中對第一次結果更改最多的也是人際關系維度。這說明人際交往需求是患者及其家庭關注的核心內容。結果中,有2 個條目是患者選擇而家屬均未選擇的。①患者選擇了“如果我已沒救不要靠機器維生”,而2 名家屬均選擇了“我不想有呼吸困難”。原因討論時發現,患者對終末期癥狀的認知存在一定偏差,認為只要吸氧就不會出現呼吸困難的癥狀。其配偶和女兒講述了1 次她們親歷的患者發生嚴重呼吸困難的情境,同時向護士了解可能出現的癥狀。患者認知到呼吸困難可能是終末癥狀之一,且難以忍受,并希望通過一切辦法進行緩解。故重新審視后,將“我不想有呼吸困難”加入待辦事項。②患者選擇了“我希望家人了解死亡對我的意義”,2名家屬均未選該項,且同時選擇了“我不想成為家人的負擔”。溝通中發現,患者的“死亡意義”中包含減輕家人負擔,而家屬在原因討論后表明其立場是“這種負擔是我們希望承受的”。最終,患者認為死亡的意義家人已了解,而“負擔”的意義也被重新定義,故未將其放入“待辦事項”。三方的其他差異性選擇和患者第2 次結果的調整,并非一定受他人影響,也可能同時包含內在因素,如“我希望家人能接受我即將離世的事實”,女兒說“很重要,但不可能完成”,患者認為“時間會讓她們接受,順其自然”。故該項未納入“待辦事項”。
2.5 參與者反饋反饋內容顯示,患者認為最大的收獲是“知道接下來要做什么,能夠坦然談論(死)這件事”;配偶認為最大的收獲是“感覺放松了一些,以前小心翼翼怕說錯話”;女兒認為最大的收獲是“更理解他(爸爸)了,撲克牌把我們想到的和沒想到的(需求)都展現了”。患者和配偶無改進建議,女兒提出卡片中宗教信仰內容普適性不足。
3 討論
3.1 撲克牌心愿卡有助于開啟生命末期需求的家庭溝通有研究認為,在中國癌癥患者中討論生命末期需求或死亡話題被視為禁忌,并歸結于傳統文化觀念的影響[11]。也有學者指出,患者及相關人員可能不愿在沒有提示的情況下公開討論癌癥對其自身及其關系的影響[8]。而撲克牌心愿卡中的文字對溝通起到了提示作用,有助于促進生命末期話題的開啟。既往研究也表明,撲克牌心愿卡對我國安寧療護有一定推動作用,適用于我國的傳統文化背景[6,12]。此外,撲克牌心愿卡的有效性可能還基于其具備以下特征。首先,全球流行的撲克牌形式易于被大眾接受,相較于他人說教,文字呈現可減少侵略性并促進主動思考。其次,以愿望的方式表達需求實現了死亡話題的“軟著陸”。除了疾病本身,更廣泛的計劃和目標可以成為自我披露過程的一種方式,并且可以產生聯結、澄清價值觀,增強應對能力和確定有意義活動的優先級[9]。此外,卡片內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廣泛性。本案例參與者均未使用特別心愿卡,結合患者女兒的反饋,說明4 種花色的內容基本可以滿足其想要表達的需求,特別心愿卡也可作為未涉內容的補充。綜上,撲克牌心愿卡不僅適用于在單一群體中開啟死亡討論話題,同時也可適用于患者與其家庭成員的溝通,是一種值得推廣的生命末期需求溝通工具。
3.2 開展家庭溝通有助于滿足患者生命末期的人際關系需求本案例中,人際關系需求是討論的核心內容,且以家庭關系最為突出。對于患者及其家庭而言,擁有良好、和諧的人際關系是非常重要的,并希望在生命終末階段和親朋好友仍有互動交流,如“我希望有機會和親友道別”“過世時,希望有人在我身旁”等,這與部分學者[5-6]的研究結果一致。從表2可見,經討論后,患者對人際交往需求做出了較多改變。這也表明,溝通過程為個體表達偏好和價值觀提供了機會,差異選項的討論也使參與者得以進一步澄清深層次的原因。在生活中,討論和分享個人目標可以提高人際關系的滿意度[13]。換言之,雙方互動的過程滿足了其部分人際需求。可見,通過安心卡促進患者與其家庭成員有效溝通也是滿足其生命末期需求的重要部分。
3.3 應用撲克牌心愿卡開展生命末期需求家庭溝通的不足及展望本案例最終形成的待辦事項為患者及其家庭明晰了相關計劃目標。參與者的反饋也肯定了該方法對于促進溝通的價值和意義。但本次撲克牌心愿卡溝通實踐尚存在一些不足:如實踐前對患者及其家庭的評估不夠充分,且未使用能夠提供客觀依據的權威評估工具;同時,對案例未進行后期追蹤,對患者需求的完成情況及長期溝通效果缺乏評估。另外,撲克牌心愿卡雖已在國內相關領域被使用,但其內容仍有待進一步開展本土化調試和文化適應性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