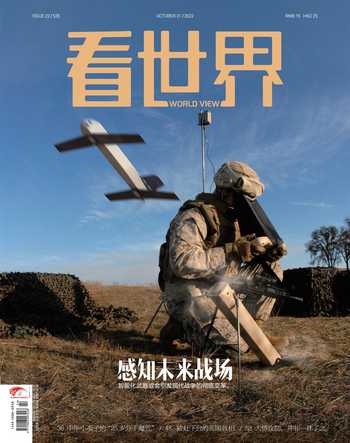元宇宙前夜的老年生活
菲力

2022年8月20日,埃隆·馬斯克首次展示Tesla Bot人工智能人型機器人
有兩個人類歷史的第一次正在當下同時發生:一、全球65歲以上人口數量首次超過5歲以下兒童數量;二、城市人口首次超過了農村人口,到2050年,全球2/3的人口將居住在城市。
這兩個“第一次”意味著,這一屆的年輕人必定負擔更沉重的贍養責任,而這一屆的老年人,則很難指望年輕人實現傳統意義上“父母在,不遠游”的孝順。
其中,日本由于年輕人普遍放棄戀愛、放棄結婚、放棄生育,加上先進的社會醫療條件延長了預期壽命,已成為全球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沒有之一。今年初的統計表明,日本國內達到20歲的“新成人”占總人口數的0.96%,連續12年低于1%。
在全球老齡化的進程中,日本沒有選擇,必須身先士卒,交出第一份答卷。
日本的回答是:機器人養老。
日本從1970年代就開始步入老齡化社會,受此困擾最久,也探索最久。好在,哪里有需求,“看不見的手”就去哪里解決問題。在日本養老院,最突出的矛盾是人的矛盾。照顧人很難,照顧老人更難,專業護工是需要經過培訓考核上崗的。國際標準“失能老人與護工”的配置標準是3比1(日本為2比1),預測到2025年日本介護(即看護)服務業工作人員的短缺將達到38萬。


喂飯機器人和幫助行動不便的老人洗頭的機器人
最早商用于養老產業的康復機器人并不直接幫助老人,而是幫助護理人員。
從20世紀下半葉開始,日本的人工智能技術就開始從醫療、軍事、工業等領域,向養老產業聚焦。最早商用于養老產業的康復機器人并不直接幫助老人,而是幫助護理人員,針對半失能老人收集訓練數據反饋給醫師,提高康復方案的準確性。
日本智能養老設備廠商松下,干脆在2001年自己開設了一家提供護理服務的養老院,充分使用數字技術,通過智能家居設備,結合遠程醫療終端、智能機器人等前沿技術,解決過去養老產業中高昂的人力成本問題。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關于“智慧養老”的探索也逐漸精細化和人性化。比如,有專門幫助行動不便的老人洗頭的機器人—傳感器會先掃描頭部信息,內置計算機根據這些數據,使用16根直徑約2厘米的樹脂手指,模擬合適的力度對頭部進行揉壓捏搓洗等重復動作,整個洗頭過程大約3~8分鐘。
再比如喂飯機器人,手臂前端安裝有叉和勺子,利用類似抓娃娃的原理,將食物自動夾住,送到操作者嘴邊。貼心的是,叉子還會感應縮回,避免誤傷。據說只要30分鐘操作培訓,老人就可以將豆腐、米粒等軟滑微小的食物,平穩送入口腔。
此外,還有陪伴型、醫療護理型、安全監督型、力量型等機器人,被不斷開發出來。
盡管如此,對于日本這個已經在人工智能道路上探索超過半個多世紀的國家來說,看護型機器人的研發速度仍是緩慢的,每年不超過20種,每種機器人僅導入4到5家養老院。不論是產品迭代還是普及實用速度都不樂觀,且不論價格的門檻,現實的困境瑣碎且繁雜。


日本公司研發的“小海獅Paro”
以藤田醫科大學開發的一款名為“toyo醬”的看護機器人為例。由于日本80%的老年人事故都發生在自家住宅內,跌落和摔倒的比例占一半以上,對于骨折臥床的老人來說,幫助他們開關家電和尋找物品,能夠有效減少老人移動—toyo醬為此而生。
toyo醬能夠在“臉部”屏幕上顯示接收到的指令,遙控電器、拿取物品。理論上,這是一個實用的機器人,但硬傷在于,toyo醬的運行需要75平米以上的空間,天花板高度也要高于一般才能安裝軌道。這樣一來,絕大多數日本民居就不予考慮了。
此外,toyo醬的所有指令反饋都需要提前輸入,無法預測的指令或對話toyo醬就無法做到。這就尷尬了,因為老年人群的特殊性之一就在于需求的多樣性。這也是為什么與商務賓館不同,養老機構要向老人提供理想的服務是非常困難的,過去這主要依賴專業的護理人員來實現。
同樣是“腰酸背痛”,誘因不同,需要的護理服務也不同。因此,如果讓toyo醬來處理“腰痛”的情景,多半它還是會建議被看護者:去找“人”吧!而對于人來說,照顧一位老人和操作一臺機器人同樣都要經過培訓,這又在實際運用中增設了一道價格之外的學習門檻。
長大后回想自己小時候暢想未來的作文,誰沒勾勒過“汽車在天上飛”“機器人送來早餐”這樣的圖景呢?甚至有網友考古到1958年上海新華分社知識座談會上,人們曾暢想在2000年時會出現一種“萬能機器”制造一切日用品,初步實現共產生活。這大概是關于“自動化”的終極想象了,但人們顯然輕率地低估了科技創新落到實地的難度。
事實上,現實中真正的自動駕駛仍是個夢,更別提“真正的汽車在天上飛”。目前人工智能領域熱門的深度學習、神經網絡等,本質仍屬于仿生。但回顧歷史,人們之所以能飛行,不是因為長出了翅膀,而是源于空氣動力學和流體力學的發展。只有在厘清本質而非單純模仿的前提下,人工智能才能真正區別于如今為人所詬病的人工智障。而這些基礎理論的發展和突破,以百年計。
如果一臺機器能夠與人類展開對話而不被辨別出其機器身份,那么可以稱這臺機器具有智慧。
但人們等不及了,大衛、瓦力、擎天柱……好萊塢出產的機器人科幻大片比現實中的人工智能,更快地占領了觀眾的心智。
機器人至少要有個人形吧,最好還能懂得愛與被愛。于是,我們等來了日本公司研發的“小海獅Paro”。
這是一臺陪伴型機器人,全身布滿感應器,能夠對觸摸做出靈活反應,能發出仿真格陵蘭小海獅的聲音,雖不能說話,但撒嬌賣萌不在話下。很多養老院中的老人將它抱在懷中,視作自己的孩子,盡管這場景看起來還是很孤獨,但卻真實地增加了老人的腦活動,降低了阿爾茨海默病的發病率。

2022年10月1日,演示視頻展示特斯拉Optimus正在搬運紙箱
當然,與人類大腦的物理性不同,真正意義上發自心靈的愛與同情,被認為具有一種神秘的非物理性,那也是目前建立在模仿基礎上的人工智能技術所不可企及的,生命的奧義。
比較誠實的預測,來自人工智能領域的專家李開復博士。他認為,即便未來人工智能能夠無限接近人類的大腦,但愛與自由意識將始終是人與機器人的分野。一切與人接觸的崗位,都仍需要包裹上真實人類的溫度,而這也詮釋了目前機器人在養老產業中的局限。
另一個大新聞,是前不久埃隆·馬斯克帶來的“擎天柱”。演示視頻展示了這位身高1.72米的“猛男”能在汽車工廠搬紙箱、給植物澆水、移動金屬棒,遠景目標是做飯、修剪草坪、照顧老人等。可惜的是,這些重復性、機械性功能已經并不新鮮,而馬斯克本人期許的另一個賣點“人形”在激起一層浪花之后,也很快無人問津—早在2000年,日本就研發了可雙足行走的機器人,但那又如何?人之所以為人,并非因為有“人形”。
美國人類系統工程學教授Nancy Cooke說得更直指本質:“馬斯克需要展示出機器人具備做出多樣化、非明確指令之行為的能力,才能算成功。如果只讓機器人四處走走、跳跳舞,這并不算什么。”
事實上,早在1950年,英國“計算機科學之父”圖靈就提出了一個劃時代的觀點:如果一臺機器能夠與人類展開對話(透過電傳裝置)而不被辨別出其機器身份,那么可以稱這臺機器具有智慧。這一觀點至今仍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判別標準,但不論“擎天柱”還是Siri,都不曾通過這一測試。
倒也不必因此否認半個多世紀以來,科學家們日以繼夜的努力。從人臉識別、道路導航到內容推薦,今天每個城市人從睜開眼開始,幾乎已被智能應用包圍。
毫無疑問,我們正處于人工智能時代的前夜。一代人正在一邊老去一邊猜測:生命的逝去和技術的突破,究竟哪一個會先來?
特約編輯姜雯 jw@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