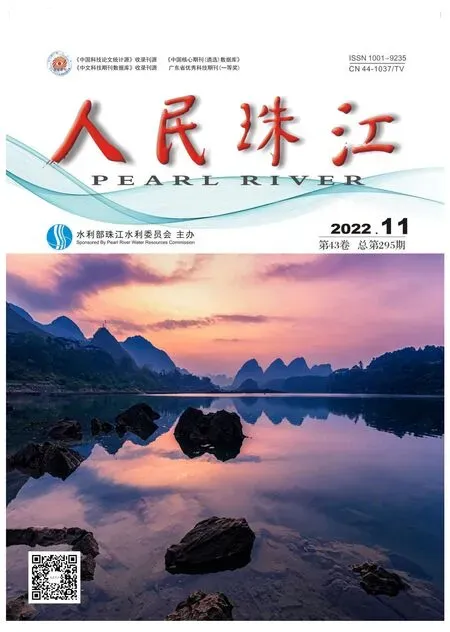基于耦合模型的城市流域洪澇災害治理研究
——以廣州某片區(qū)為例
朱必方,高焱哲,賴成光
(1.廣州市宏濤水務勘測設計有限公司,廣東 廣州 510405;2.華南理工大學土木與交通學院,廣東 廣州 510640)
在全球氣候變化和中國城市化進程持續(xù)快速推進的背景下,城市洪澇災害已成為影響城市正常運行和發(fā)展的最主要的自然災害之一,嚴重威脅到城市居民的生命財產(chǎn)安全[1-3]。據(jù)統(tǒng)計,2007—2017年,全國有超過360座城市遭遇過內澇災害[4]。近年來,發(fā)生在特大城市或省會城市而造成巨大損失的洪澇災害也屢見不鮮,例如2021年鄭州“7·20”暴雨因災死亡失蹤380人,經(jīng)濟損失達到409億元[5];2020年廣州“5·22”暴雨導致全市443處地段出現(xiàn)水浸,地鐵13號線停運,多地停工停課[6];2019深圳“4·11”瞬時強降雨引發(fā)洪水,造成11名正在清理河道的工人溺亡[7]。由此可見,城市洪澇災害已經(jīng)嚴重威脅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城市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如何科學地認識城市洪澇災害的演變規(guī)律并基于此制定有效的防御措施,已成為中國城市防洪排澇工作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
利用城市雨洪模型對城市洪澇開展數(shù)值模擬是一種有效的非工程防御措施,可為制定各種防災減災措施提供參考依據(jù)。眾多學者對城市洪澇數(shù)值模擬技術開展了大量的研究,如曾照洋等[8]利用WCA2D和SWMM模型實現(xiàn)了某城市區(qū)域的暴雨內澇一、二維模擬;黃國如等[9]利用InfoWorks ICM構建了一維-二維耦合城市洪澇仿真模型;梁汝豪等[10]利用SWMM模型對獵德涌進行了模擬,揭示了城市地表徑流規(guī)律。這些雨洪模型的使用有助于揭示城市洪澇的形成機理及其演進規(guī)律,然而這些研究大部分關注研究區(qū)內暴雨所導致的內澇情況,很少從區(qū)域整體流域出發(fā)綜合考慮洪澇特征,存在一定的洪、澇孤立考慮的弊端[11],對于河道影響及其反饋作用的考慮相對欠缺,這對制定科學合理的防災減災措施是極其不利的。
城市洪水一般指城市河道水位上漲導致漫堤造成的水淹,而城市內澇則是指降雨超過管網(wǎng)排水能力導致的水淹,二者成因上存在一定區(qū)別,但對于城市流域往往存在洪澇同源的情況,即洪水和內澇均是由于流域暴雨所導致的。城市河道是城市重要的行洪排澇通道,城市內澇水量的納入可能會影響河道的流量和水位,而城市河道高水位頂托也可能造成城市管網(wǎng)排水不暢,從而進一步加劇城市內澇。可見,城市洪水與內澇的關系不能簡單地割裂研究,在開展內澇數(shù)值模擬時忽略城市河道的影響及其反饋作用,往往會導致模擬結果不準確,而基于此結果所提出的治理方案顯然難言科學合理。因此,從城市流域視角出發(fā)統(tǒng)籌市政排水及河道防洪,理論上有助于更科學地實施城市防洪排澇規(guī)劃,對提出科學合理的城市洪澇災害治理措施具有重要意義。
鑒于此,本文將以廣州某片區(qū)為例,基于流域系統(tǒng)整體視角構建一種考慮河道、管網(wǎng)和地表的耦合水文水動力模型,利用該模型分析遭遇100年一遇暴雨情景下的淹沒情況,并評估采取洪澇防治措施的效果。研究結果以期為城市洪澇災害防御計劃的科學制定提供思路,也為研究區(qū)的防災減災工作的開展提供技術參考。
1 數(shù)據(jù)與方法
1.1 研究區(qū)概況
研究區(qū)位于廣州市白云區(qū),東臨珠江西航道,南、西、北三面與佛山市南海區(qū)接壤,面積7.76 km2。流域地勢西北高東南低,西北部為潯峰山;中部、南部主要以城中居民地為主;地面高程大多為8~20 m。片區(qū)主要河涌有:橫沙涌、沙貝涌、象拔咀涌3條河涌。橫沙涌長約1.55 km;沙貝涌全涌長約6.28 km;象拔咀涌全涌長約2.38 km。象拔咀涌與沙貝涌通過鳳崗北水閘聯(lián)通,3條涌出口均為珠江西航道。根據(jù)GB 51222—2017《城鎮(zhèn)內澇防治技術規(guī)范》,超大城市的內澇防治標準應達到100年一遇,因此研究區(qū)應滿足100年內澇防治重現(xiàn)期。
1.2 數(shù)據(jù)處理
1.2.1河道斷面處理
河道數(shù)據(jù)來源實測資料,根據(jù)河涌現(xiàn)狀走向,從上游到下游依次繪制每條河涌的河道中心線形成河道矢量文件,并將河道矢量文件導入河道水動力模型當中,形成河網(wǎng)文件,從而完成研究區(qū)河網(wǎng)的構建。同時根據(jù)研究區(qū)現(xiàn)狀實測河道資料,依次確定每條河道斷面的河底和堤頂高程、寬度信息,根據(jù)這些信息形成模型斷面文件,斷面布置見圖2。

圖1 研究區(qū)區(qū)位示意

圖2 研究區(qū)河道斷面分布示意
1.2.2地形數(shù)據(jù)
高程數(shù)據(jù)來源實測資料。對高程數(shù)據(jù)中的異常點進行刪除處理后,使用ArcGIS軟件的3D分析生成TIN地形,再將TIN數(shù)據(jù)轉換為5 m×5 m的DEM數(shù)據(jù),形成研究區(qū)初始DEM數(shù)據(jù)。根據(jù)河道寬度、河底高程生成河道DEM,并與研究區(qū)初始DEM進行鑲嵌,形成研究區(qū)最終DEM見圖3。研究區(qū)除西北部山區(qū)外,整體上地勢較為平緩。
1.2.3管網(wǎng)數(shù)據(jù)處理
研究區(qū)內的管線和井點數(shù)量繁多且雜亂,因此需要對數(shù)據(jù)進行概化處理以優(yōu)化排水管網(wǎng)的結構,便于數(shù)據(jù)的處理,提高模型的運行效率。具體概化處理包括刪減多余的、影響較小的細枝末節(jié),保留主干,比如連接檢查井和雨水篦的短管,對于排水管網(wǎng)的貢獻和影響極小。根據(jù)概化后的管網(wǎng)確定雨水管道和管井信息,建立管網(wǎng)拓撲結構,對錯誤連接的管道進行修正。經(jīng)概化處理后的排水管網(wǎng)見圖3,其中排水管線2 248條,雨水井2 242個,出水口79個。

圖3 研究區(qū)DEM及管網(wǎng)分布
1.2.4設計降雨
對于設計降雨,水利與市政設計成果存在一定的差異,導致存在一定的銜接不匹配問題。基于洪澇治理的流域系統(tǒng)整體視角須統(tǒng)一設計雨型,即設計雨型須同時兼顧水利長歷時降雨的量和市政短歷時降雨的峰。對于市政暴雨,一般采用《廣州市中心城區(qū)暴雨強度及計算圖表》發(fā)布的暴雨強度公式進行計算(以下簡稱“暴雨強度公式”);對于水利降雨,一般采用《廣東省暴雨參數(shù)等值線圖》進行計算。為統(tǒng)一二者的降雨過程,本研究綜合分析市政設計暴雨和水利設計暴雨,綜合對比選取相應降雨歷時的大值;對于最大3 h采用芝加哥雨型進行雨量分配,然后利用水利24 h逐時設計雨型分配剩余雨量。研究區(qū)100年一遇24 h降雨量為300.3 mm,暴雨峰值強度為7.93 mm/min,設計100年一遇暴雨過程見圖4。

圖4 研究區(qū)100年一遇設計降雨過程
2 模型構建
2.1 河道模型構建
河道水動力模型采用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研發(fā)的IFMS洪水分析軟件,主要用于河網(wǎng)流量、水位、水質等河道水文參數(shù)的模擬,具有計算穩(wěn)定、精度高、可靠性強等特點,能方便靈活地模擬閘門、水泵等各類水工建筑物,尤其適合應用于水工建筑物眾多、控制調度復雜的情況,因此該軟件在全國重點地區(qū)洪水風險圖項目中得到廣泛應用[12-13]。
研究區(qū)河涌主要包括象拔咀涌、沙貝涌、沙貝支涌、沙貝舊涌東支涌、沙貝理涌西支涌、橫沙涌等,將前述處理完的河道中心線及河道斷面數(shù)據(jù)導入模型,完成研究區(qū)一維河道模型的構建。本次研究區(qū)河道模型共涉及5個泵站及6個水閘,根據(jù)水閘泵站資料,在模型中對其進行概化。研究區(qū)排澇方式以自排為主、泵排為輔。因此在設置閘泵調度規(guī)則時,根據(jù)內外江水位關系設置閘泵的開啟或關閉。主要規(guī)則如下:①外江水位低于內江水位,開閘,河道洪水自排;②外江水位高于內江水位,開泵關閘,河道洪水泵排。
2.2 地表水動力模型構建
二維地表模型采用英國布里斯托爾大學開發(fā)的LISFLOOD-FP水動力模型,最早版本由Paul Bates和Ad De Roo于2001年開發(fā)完成,到2013年8月已經(jīng)更新到5.9版本[14]。LISFLOOD模型能夠對一維河道和二維洪泛區(qū)進行水動力模擬,已有學者已驗證了其良好性能[15]。二維地表模型構建主要包括輸入條件設置、參數(shù)設置、地形文件生成等。其中,二維的輸入包括河道的漫頂流量以及管網(wǎng)的溢流量;地形文件通過ArcGIS軟件插值高程點生成。
2.3 管網(wǎng)模型構建
一維管網(wǎng)模型采用美國環(huán)保署(EPA)開發(fā)的SWMM模型,已被廣泛應用于城市雨水徑流模擬、城市暴雨內澇預警預報、排水規(guī)劃與設計、海綿城市建設、水質模擬等領域之中[16-18]。SWMM模型由于其開源屬性,能夠很方便地調用模型源代碼或者動態(tài)鏈接庫函數(shù)進行二次開發(fā)(比如耦合二維水動力模型),以滿足特定的研究目的,其各模塊既能夠獨立完成特定功能,又能夠互相調用,形成一個獨立而統(tǒng)一的整體。
2.4 模型耦合
在模擬管網(wǎng)匯流上,SWMM模型已十分成熟,但是無法得到城市地表的淹沒范圍、水深以及淹沒過程;LISFLOOD-FP模型的優(yōu)勢在于能夠基于溢流節(jié)點的溢流過程(即流量-時間關系)和城市地形來模擬城市的淹沒范圍、水深及淹沒過程。為發(fā)揮二者優(yōu)勢,本文將SWMM模型與LISFLOOD-FP模型進行單向耦合,即由SWMM 模型提供節(jié)點溢流量,LISFLOOD-FP模型進一步完成淹沒范圍、水深以及淹沒過程的模擬。為了考慮河道水位對管網(wǎng)排水的影響,將IFMS河道模型計算的水位作為SWMM管網(wǎng)模型出水口的邊界條件。河道模型與二維模型的耦合則是將河道模型的水位結果與兩岸堤頂高程進行對比,若有水位高出兩岸堤頂,則統(tǒng)計高出兩岸堤頂?shù)臅r間及水位以計算河道洪水漫溢出地表的體積。
3 結果分析
3.1 模型驗證
利用上述所構建的模型對研究區(qū)的100年一遇暴雨情景進行模擬,模擬結果見圖5a,并與研究區(qū)的《廣州市一流域一手冊洪澇風險圖集》(圖5b)靜態(tài)洪水風險圖進行對比。結果表明,本研究的模擬結果與靜態(tài)風險圖中的風險點分布總體上具有較高的重合度,例如環(huán)洲五路南段、城西花園、潯峰崗地鐵站附近的模擬洪澇風險分布及等級均與洪澇風險圖十分接近;但本研究結果發(fā)現(xiàn)橫沙涌下游處有大片區(qū)域處于中高風險,與圖5b不一致。通過對模型結果進行分析,發(fā)現(xiàn)橫沙涌下游由于河口泵站規(guī)模過小導致河道水位較高,部分洪水漫出河道且排水管網(wǎng)長時間受到河道水位頂托,導致排水不暢。為此,本研究對該中高風險區(qū)開展了實際調查,發(fā)現(xiàn)近年來該區(qū)域遭受的暴雨內澇情況確實比較嚴重,表明本研究的模擬結果更加合理。綜上可知,所構建的耦合模型是合理可靠的,可用于下一步分析。

a)現(xiàn)狀模擬內澇風險
3.2 現(xiàn)狀洪澇情況分析
利用河道水動力模型對研究區(qū)內河道開展數(shù)值模擬,橫沙涌20年一遇設計洪水水位見圖6。由圖可知,象拔咀涌、沙貝涌、沙貝支涌、沙貝理涌西支涌、沙貝舊涌東支涌的河涌水位均低于相應位置的左右岸高程,河道均沒有發(fā)生河道漫流現(xiàn)象,滿足20年一遇防洪要求,而橫沙涌離在河口300~600 m(圖示橫坐標900~1 200 m處)左斷面位置的模擬水位高于左岸高程,表明橫沙涌在現(xiàn)狀排澇設施下無法滿足20年一遇的防洪標準,因此需對橫沙涌采取相應措施,使其能夠滿足20年一遇的要求。

a)象拔咀涌
將100年一遇設計暴雨輸入所構建的耦合水動力數(shù)值模擬模型,得到研究區(qū)100年一遇暴雨情景下淹沒范圍及淹沒水深,見圖7。研究發(fā)現(xiàn),研究區(qū)現(xiàn)狀洪澇災害較為嚴重的區(qū)域主要集中在橫沙涌中下游區(qū)域以及環(huán)洲五路北側,除這2個區(qū)域外片區(qū)整體內澇風險較低。分別對不同淹沒深度下的淹沒面積進行統(tǒng)計,結果見表1,積水深度大于0.15 m的內澇面積達到28.75 hm2,其中積水深度處于0.15~0.30 m、0.3~0.5 m、0.5~1.0 m以及大于1.0 m區(qū)間的內澇面積分別是13.04、6.18、5.17、4.36 hm2。根據(jù)洪澇風險等級劃分標準可知,處于高風險區(qū)域的面積有4.36 hm2,中度風險區(qū)域面積5.17 hm2,低風險區(qū)域面積6.18 hm2。
從淹沒位置空間分布上看,研究區(qū)在現(xiàn)狀排澇設施作用下,環(huán)洲五路北側由于局部低洼,存在較高的內澇風險。橫沙涌中下游片區(qū)由于現(xiàn)狀南圍泵站規(guī)模較小,導致河道洪峰水位較高,造成排水不暢甚至倒灌進排水管網(wǎng),存在較大面積的中高風險區(qū)域,片區(qū)內高風險地區(qū)需要通過實施改造措施降低內澇風險。

圖7 研究區(qū)現(xiàn)狀內澇積水空間分布

表1 研究區(qū)改造前后內澇淹沒面積統(tǒng)計和風險等級
上述模擬結果表明研究區(qū)現(xiàn)狀排水設施不能應對100年一遇內澇險情,橫沙涌不足以應對20年一遇防洪要求,需要根據(jù)不同區(qū)域的洪澇成因,采取相應措施提高整個流域的防洪能力。
3.3 洪澇防治措施效果評估
為更好抵御研究區(qū)洪澇災害并提高整體防洪排澇能力,相關部門綜合兼顧考慮了交通、電力、通訊等設施建設及規(guī)劃后提出了多種治理方案,經(jīng)過綜合對比后擬采用以下方案:①擴大部分市政雨水管道管徑,將部分管徑較小管道的管徑增加至800~1 000 mm;②增設部分雨水管道,增加片區(qū)排澇能力;③將橫沙涌涌口附近卡口處拓寬至8~10 m,橫沙涌涌口泵站流量由2.2 m3/s增加至8.0 m3/s。詳細改造工程建設方案見圖8。

圖8 研究區(qū)改造方案示意
根據(jù)建設方案改造后的情景并結合閘泵調度規(guī)則,將100年一遇設計暴雨數(shù)據(jù)輸入模型進行洪澇數(shù)值模擬,二維淹沒水深模擬結果見圖9,改造前后淹沒面積和風險區(qū)域比對見表1,改造設施使內澇加劇和減緩的情況見圖10。表1可知,建設后的內澇面積大大減少,改造措施使得高風險地區(qū)內澇面積大幅降低,降低幅度達94.84%,高風險地區(qū)基本消除。中風險地區(qū)降低幅度約86.94%。圖11所示,橫沙涌改造后水位降低了約1 m,低于兩岸地表高程,表明橫沙涌達到20年一遇防洪標準。改造方案模擬結果顯示,橫沙涌下游段水位明顯降低,使得附近管網(wǎng)排水通暢,澇水能及時排出,有效消除了橫沙涌下游的高風險點,表明改造方案有效合理。改造之后研究區(qū)僅在環(huán)洲五路口處剩余一個內澇高風險點。通過對模型結果進行分析,發(fā)現(xiàn)該處地形較低導致周邊的澇水容易向那里匯集,因此即使改造方案增設了管道并加大了管徑,該地區(qū)排澇能力仍然較低;但由于該地區(qū)主要為草地,沒有太多人口和財產(chǎn)分布,即使受淹影響不大。剩余2處中風險點分別位于彩濱北路保利西海岸東部以及沙貝大街北部城中村,均因地局部地勢低洼導致澇水匯集且無法自排,可在不影響交通、電力、通訊設施情況下通過加建泵站或設立LID措施消減內澇。

圖9 研究區(qū)改造后淹沒范圍分布

圖10 研究區(qū)改造前后淹沒變化對比

圖11 橫沙涌改造后模擬水位
綜上可知,所提出的改造方案總體上能使研究區(qū)的內澇情況得到極大的改善,特別是橫沙涌河口泵站的改造使得橫沙涌河道水位明顯降低,使得此處澇水能夠順利排走,有效減輕此處的洪澇災害。以上研究表明,基于流域整體觀提出的內澇改造方案能取得很好的內澇減緩效果。
4 結論
以廣州某片區(qū)為例,基于流域系統(tǒng)整體視角構建了河道-管網(wǎng)-地表耦合水動力模型,并利用模型對研究區(qū)改造前后的洪澇風險進行評估,得到結論如下:①耦合模型考慮了河道水位對管網(wǎng)的頂托作用,能體現(xiàn)流域的整體性,所模擬的洪澇風險點與靜態(tài)洪澇風險圖的風險點基本一致,表明所構建的耦合模型是合理可靠的;②現(xiàn)狀條件下,研究區(qū)遭遇100年一遇暴雨時存在較高的洪澇風險,環(huán)洲五路以及橫沙涌下游淹沒水深超過1 m,需采取相應措施減緩該地區(qū)的洪澇風險;③若采用河道治理、雨水管網(wǎng)改造、泵站擴建等改造方案,能大大降低研究區(qū)的洪澇風險,特別是能有效減緩橫沙涌下游段的內澇情況,表明從流域整體觀出發(fā)治理洪澇災害將會顯得更加科學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