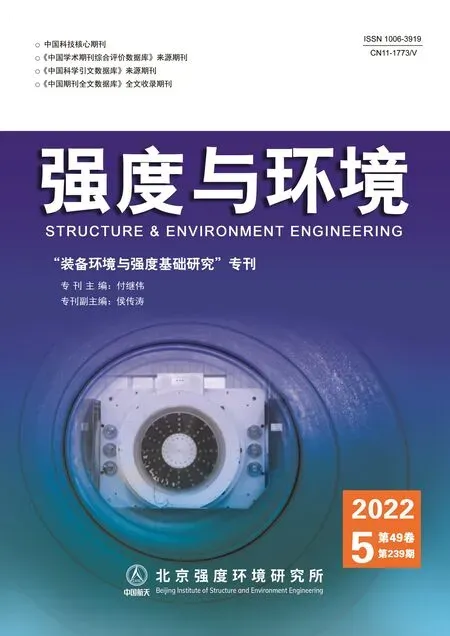熱發射導流器型面仿真計算優化設計
穆洪斌 畢瑩 王暉 寧雷
(北京宇航系統工程研究所,北京100076)
0 引言
垂直熱發射在發射初期產生高溫高壓的燃氣射流,射流導致嚴重的燒蝕、沖擊、反濺,直接影響到發射的安全性[1]。熱發射中導流器設計的合理性,可提高發射的安全穩定可靠性[2]。國內外對于火箭發射的燃氣流場的數值分析研究較多[3-9],但是對于導流器的公開文獻較少。本文主要研究了導流器不同外形對于發射流場的不同規律,對火箭發射的導流器設計具有指導意義。利用數值模擬仿真技術燃氣射流的沖擊和侵蝕,可高效細致地分析流場附近的壓力和溫度,給出導流器與火箭及發射臺兼容的最優模型。本文通過數值模擬仿真計算方法,建立了3種導流器模型,計算了燃氣射流對發射臺和導流面的流場特性,選出了最優的導流器型面。
1 導流器幾何模型
發射臺主要由臺體、導流器組成。臺體用于支承火箭,承受起豎后的火箭質量;導流器用于排導火箭發動機點火之后的射流;發射臺導流形式采用雙面導流形式,臺體與導流器分開,分別與地面通過地腳螺栓連接。導流型面參數如0所示。
在方案1基礎上首先考慮對導流器外形進行優化,優化設計的兩種導流器外形如0所示。兩種導流器導流型面一致,考慮燃氣流場的反向噴濺,設計了兩種高度直線的方案,下部直線高度方案2為1.5a,方案3為a,初步優化完成的導流器形面如0、0、0所示。

圖1 臺體及導流型面主要參數(方案1)Fig.1 Structural parameters of the diverter profile (Scheme 1)

圖2 優化導流器外形示意圖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optimized diverter profile

圖3 優化導流器圖(方案2)Fig.3 The optimized diverter (Scheme 2)

圖4 優化方案2導流器圖(方案3)Fig.4 The diverter of the optimized Scheme 2 (Scheme 3)
2 仿真模型及邊界條件
仿真模型計算域和網格圖如0所示,考慮仿真計算時效性和流場充分性,取發射臺架20倍直徑的計算域。采用完全結構化網格對流場進行離散。


圖5 仿真模型及計算域圖Fig.5 The simulated model and its computational domain

圖6 各方案的網格分布Fig.6 Model meshing of the three schemes
計算中采用的邊界條件設定如0所示。其中,壓力入口邊界條件給定總壓為9.1MPa,總溫3614K;壓力出口邊界條件壓力為環境大氣壓,溫度常溫300K;對稱面邊界條件法向速度和其它參數方向梯度為0;壁面邊界條件中壁面按無滑移絕熱壁面處理。初始條件:噴管內給定一級發動機的燃燒室總溫總壓,流場其它地方給定環境壓力和溫度。

圖7 邊界條件示意圖Fig.7 Boundary condition
3 導流面外形優化研究
從導流器附近的流體溫度場、速度矢量分布,導流面的溫度、壓力分布,發射臺的溫度、壓力分布六個方面對三種方案的仿真結果開展分析。
3.1 導流器附近的流體溫度場分析
給出三種方案下導流器附近的流體溫度場分布,如0所示。
從圖8 a)中可知,燃氣經導流面導向后,主要向導流方向流動,同時燃氣流未出現反濺,但是由于導流器未設側板防護,仍有部分燃氣流向導流器側邊,對發射臺形成沖擊(發射臺表明壓力達到391000Pa)和燒蝕(發射臺表面氣體溫度達到3270K)。


圖8 導流器附近流體溫度分布Fig.8.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the fluid surrounding the diverter
對導流器型面進行優化設計后的方案2和方案3中,仿真計算的導流器型面對應的溫度分布如圖8 b)和圖8 c)所示。如圖所示,導流器加側板后,燃氣流能順暢地沿導流方向流動,沒有向導流器側向流動的現象,燃氣流未出現反濺。噴管出口距離導流面越遠,導流面承受的熱和力載荷越小,相比方案2,方案3導流器下部的直段降低0.5a,導流器附近流體溫度分布如圖8-c所示,如圖所示,方案3的燃氣流沿導流方向順暢流動并且未出現反濺,導流面上壓力比方案2降低。
3.2 導流器附近流體速度矢量分析

圖9 導流器附近流體速度矢量分布Fig.9 Velocity distribution of the fluid surrounding the diverter
如0所示,方案1導流型面下,燃氣流未出現反濺現象,大部分向導流面指向方向流動,但是由于未加側板,從ZY對稱面內的速度矢量可知,燃氣流向導流器側向流出,從而對發射臺形成沖刷和燒蝕。方案2導流型面下,燃氣流未出現反濺現象,導流器導流效果好,燃氣流沿導流面指向方向流動,同時由于側板的添加,沒有出現側向流。方案3導流型面下,燃氣流未出現反濺和有側向流現象,導流器導流效果好,燃氣流沿導流面指向方向流動。
3.3 導流面溫度分析
導流面上的溫度由于導流面與火箭發動機噴管出口距離限制,無論如何設計導流面均將達到燃燒室總溫。

圖10 導流面上氣體溫度云圖Fig.10 Temperature mapping of the air surrounding the diverter
方案1情況下,導流面上最高溫度為3614K,同時導流面側面有溫度升高(約2500K),也說明燃氣流向側向有流動。方案2情況下,導流面上最高溫度為3614K,同時導流面側面無溫度升高,說明燃氣流沒有向側向流動。方案3情況下,導流面上最高溫度為3614K,同時導流面側面無溫度升高,同樣說明燃氣流沒有向側向流動。
3.4 導流面壓力分析
三種方案下,方案3導流面上最高壓力最低。

圖11 導流面壓力云圖Fig.11 Pressure distribution on the diverter profile
方案1情況下,導流面上最高壓力為1.25MPa,平均壓力為0.25MPa,在三種方案中導流面最高壓力值最大。方案2情況下,導流面上最高壓力為0.87MPa,平均壓力為0.38MPa,相對方案1導流面上最高壓力下降0.38MPa。方案3情況下,導流面上最高壓力為0.68MPa,平均壓力為0.36MPa,相對方案1導流面上最高壓力下降0.57MPa。
3.5 發射臺溫度分析
方案1由于無側板防護,發射過程中發射臺表面氣體溫度最高可達3270K,最后選定的導流器型面(方案3)下,發射臺表面氣體最高溫度可下降1000K。方案1情況下,發射臺上最高溫度為3270K,在三種方案中發射臺最高溫度值最大。方案2情況下,發射臺上最高溫度為1820K,相對方案1最高溫度下降1450K。方案3情況下,發射臺上最高溫度為2260K,相對方案1最高溫度下降1010K。

圖12 發射臺溫度云圖 Fig.12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the launch platform
3.6 發射臺壓力分析

圖13 發射臺壓力云圖Fig.13 Pressure distribution of the launch platform
方案1情況下,發射臺上最高壓力為0.39MPa(絕對壓力),在三種方案中發射臺最高壓力值最大。方案2情況下,發射臺上最高壓力為0.14MPa(絕對壓力),相對方案1發射臺最高壓力值下降0.25MPa。方案3情況下,發射臺上最高壓力為0.15MPa(絕對壓力),相對方案1發射臺最高壓力值下降0.24MPa。
取各種方案下導流面上溫度、壓力的最大值和平均值如表1所示。取各種方案下發射臺上溫度、壓力的最大值如表2所示。

表1 導流面上溫度壓力最大值和平均值列表Table 1 Maximum and average value of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of the diverter profile

表2 發射臺上溫度壓力最大值列表Table 2 Maximum of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of the launch platform
從表1中可以看出,方案3下導流面上壓力最大值和平均值在三種方案中均是最小值;從表2中可知,方案2下發射臺上的最大溫度和壓力值在三種方案中最小,方案3次之,而方案1由于沒有側板防護,燃氣射流對發射臺形成較為嚴重的燒蝕和沖刷;從各方案云圖及速度矢量圖可知,方案1由于沒有側板防護,燃氣射流折轉后部分沖擊到發射臺,方案2和3添加側板后,燃氣射流不會直接沖擊發射臺。
4 結論
通過對火箭熱發射的導流器型面進行了優化,對不同導流器型面進行了仿真計算,根據分析,導流器加入側板防護后,燃氣射流不會出現 反濺和側向流動現象,燃氣射流不會影響火箭,對發射臺的影響(溫度、壓力)相對初始設計也更低;噴管出口距離導流面越遠,即導流器下部直段較低時,導流面壓力最大值和平均值最小,分布相對均勻,燃氣射流折轉后不會直接沖擊發射臺。綜上所述,在設計導流器型面時,應采取側板防護,并將下部直線段的高度盡量降低,這樣可防止燃氣射流直接沖擊發射臺,防止嚴重燒蝕和沖刷,有利于保護發射臺。